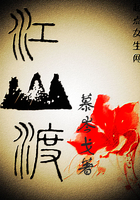这时候,有人上前去抬起那人的脑袋,一看:
“是许世立!”
“真是许兄,难怪我方才去找他找不到。”
“怎么会被人绑在这里,还被打成这样?”
……
许世立,是他,怎么会。
齐嫽不着声色往亭子那方瞥了一眼,本该在这场聚会中对她针对得最厉害,又百般刁难的许世立怎么会……被剥得精光吊挂在这。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不过没了许世立这根搅屎棍,倒是给她省去了一些麻烦。
亭子里,几人已经把还昏迷不醒的许世立抬走,剩下的几人看看站在外边的齐嫽。本来已经说好,由许世立来带头,大家再一起发难,杀她个措手不及。可现在许世立成这样子,出师不利,又去了几个人送许世立回去,剩下的几人,没一个愿意当出头鸟的,就这么你看我,我看你,看了老半天就是没人站出来。
“怎么?人还没来齐吗——”
俏丽的女声闯了进来,众人齐齐抬头,齐嫽也回头。
来的是两名年轻俏丽的姑娘,方才说话的是左边穿翠湖色的女子,模样生得十分俏丽,一双眼睛乌溜溜的地绕了一圈,最后停在了齐嫽身上。
“你……就是齐嫽吧。”
齐嫽有些讶异,萱阳公主怎么来了。
“公主,别过去。”萱阳公主身边的女子提醒了一句。
萱阳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看向齐嫽的目光也多了些谨慎与顾忌,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齐嫽,你好大胆子,身染异病却故意欺瞒。”
那边,正愁着没出头鸟的几个学子们一听这话,眼睛齐刷刷地一亮:
来了,机会来了。
未等齐嫽回答,等在边上的几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抢着开口。
“公主这话是说大姑娘的病有隐情?”
“难道说这病还会传染的?”
“若真是这样,那就是欺君的大罪,得即刻上奏……”
……
望夏都要气炸了,可又不能逾了规矩上前与那群人去理论,再怎么样她也只是个下人,在这种场合不宜出头,一个弄不好还可能害小姐落了个管教不严的话头。
齐嫽看了眼萱阳公主身边的那个艳色裳裙的姑娘,原来是在这里啊,贺婉容。
贺婉容亦在看她,贺婉容三个字在京城的闺秀圈中曾经是数一数二的,也只是曾经。因为自齐嫽出现之后,不管她再怎么努力,那“第一”就好像被烙上了齐嫽的印记,旁人再无法染指。秋闱夺魁,第一个女状元,长孙殿下启蒙先生……这一件接一件的好事,真真是刺得贺婉容耳朵发疼,幸好,还算是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任你齐嫽再怎么能耐,顶着那么张丑脸还能蹦跶到哪里去?
一干人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见齐嫽都没作反应,心里暗喜,没反应就是最好的反应了,肯定是被揭穿而不知如何是好。
“胡说——”一道身影自旁边的小径迅速地走了出来:“简直是一派胡言,以大姑娘的品性岂会做这样的事。若大姑娘的病会传染,那身为与她共事过的人,我与庄序兄怎么就没被传染。”
是谢拾泽,带着一脸的义愤填膺。
谢拾泽并非此届的秋闱生员,他是以崇文馆馆生的身份随行,为“重九宴”而来,记下宴席上的诗作,如有上乘佳作,会纳入官书之中。当一听说这翠湖亭小聚的消息,他与林庄序受馆正之命过来一探,不想却看到这么让人生气的场面。
“公主,”谢拾泽走到萱阳公主面前,拱手行了一礼:“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公主无凭无据,凭空说这番话有损大姑娘声誉。”
萱阳没料到会被人这般当众指责,又是羞愤又是难堪,纤指往旁边一指,嗔怒道:“谁、谁说本公主无凭无据?婉容告诉我的!”
“哦?那本宫也想听听,贺小姐的这一说法是从何而来?”
贺婉容面色唰地一变,看着正徐徐走来的男子。
二皇子,魏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