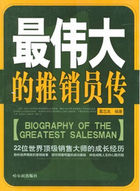吮我的血啊。——我记起了耶稣的故事。
拘留所在报房胡同,离猪市很近。天刚蒙蒙亮,便听到尖锐的叫声了。生存的挣扎啊!那声音落在我们耳中特别凄惨。在我眼前闪着把明晃晃的刀,系着红绸走水的。
早晨,一声吆喊,我们一炕十七条好汉全爬起来。放完了茅,便都盘腿坐在炕上。
如今,我才认出我们这批政治犯中间,原来还有个九岁的娃娃。见到我,他先笑了。我们便凑近了些。(为这个,我还挨了一鞭子。)我们偷偷猜拳玩:石头、剪刀、包袱,多么简单而复杂的游戏啊。
我们玩得很起劲,大人脸上却尽是愁苦。
我不能忘记同狱那个长了络腮胡子的中年人,听说他以前在学术界还颇有点名望。他曾在海外度过八年,专攻经济学,和他的太太(如今关在女牢里,无法见面)怀了对祖国的满腔热诚回来,想有所贡献。岂料一登岸,就被海关人员从箱中翻出一两本过激的书,便马上给押解到这个黑地方来。
这对患难夫妻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也不知道给送到哪儿去了。
这一天,眼看着太阳的影子在窗纸上爬。我们等着审判。我们还想申辩一番,诉说一阵,然后,听凭他们打发到什么地方去。
然而,白天任何动静也没有。
大家胡乱猜测着,有人说大概半夜拉到后院去枪毙,也有人说将用锁链穿起我们,带到警察厅去拷打。
夜间十二点光景,有人来提我了。
“叫什么?”我抬起了头,问话的是一个阎王般满脸黑胡子的家伙。坐在他两旁的是帮腔,冷笑起来令人脊梁发麻。
“我……”
厅堂很大,阴森森的,我忽然发起抖来。
“说吧,毛孩子。说完,就放了你。”那个帮腔的逼着我,一副可憎的面孔。
“……我没有罪,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对吗,”他往前凑凑说,“那么,给我打!”这最后一个字是说得很重的。
然而我没有可说的。我不能胡诌。
便这样又把我了无头绪地拉下堂来。回到炕上,我的两臂疼得爬不上炕了。当我伏在那里,想稍微缓口气时,一道鞭子又拦腰抽来了。
我禁不住哭出声来。
一共过了三堂,每堂都是那三个审官。中间的吹胡子瞪眼睛,不断恫吓着:“枪毙这小子!”另一个坐在那里记录。还有一个伪善者,他总笑眯眯地说:“我家有个小子,跟你一般大。这样年纪就送命,太可惜啦!”他们要我供出领导我的人。
当时在我心目中,那笔账很简单:一个倒霉比三个一道倒霉合算。于、李两位都是我的大哥,我宁死也不能把他们供出来。我一口咬定自己是基督教徒,并且大段大段地给他们背《圣经》,只承认组织过查经班。
第三天,正当我重复着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时,中间那个审官给我看了个油印的簿子,说是从求实中学抄到的,大概是全市或是东城一带学校里C.Y.成员的名单。在我的姓名底下,不但有年龄、籍贯,还有几句鉴定。这下我确实有些发慌,心里怪这个组织不该印这么个东西,更不应该让他们抄到。现在回想起来,谁知道那簿子是真是假!
我仍旧咬定自己是基督教徒,不承认参加过C.Y.,他们带着威胁朝我冷笑,踢了我几脚,就带下来了。
回到炕上,那个小政治犯又要我陪他玩把戏。我没那份心肠了。我在琢磨十人通信团的信会不会也落到他们手里。
夜里照例侧着身子睡,不许翻身。可是我老想心事,毫无睡意。我听两个烤着火的看守在闲聊,好像说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押到鼓楼燕儿胡同。“到了那儿,就给他们尝尝厉害了。”我寻思:这么多人怎么走法?是一长串还是分批?路上会不会碰上同学?
此后两天,我都蹲在炕上嘀咕着,吃什么也不香了。
一个黄昏,忽然把我传了去。还只当是要往燕儿胡同押解呢,原来却是崇实的洋校长把我保了出来,条件是在学校里继续软禁下去。不许出校门,也不许参加任何活动。
后来我才知道,恰好那天上电车的时候,给我的六堂弟瞥见了。他马上去告诉四堂兄和那位美国堂嫂。她赶紧去见洋校长,向他苦苦哀求,说我是个孤儿,又是个独子,这样,他们才把我营救出来。
软禁期间,堂嫂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几位教徒来看望我。一进门先唱一通颂主诗歌,然后就祈祷。在祷词中,他们称我作“迷途的羔羊”,说是上帝开恩救了我。我心里就不服气:拘留所里还有个比我更像羔羊的“政治犯”,才九岁,上帝为什么不把他也救出来呢?还有那对刚从法国回来的夫妇,也依旧关在里面。我所以能保释出来,分明是洋堂嫂托了洋校长。
1928年6月,古城北平发生了巨变。旧军阀张作霖在北伐军节节进逼下,通电议和,逃回东北老家去了。由于他对日本无止境的辱权要求有所抵制,当月4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他乘坐的专列,把他谋杀了。
这时,北平街头上贴满“打倒列强”、“取消不平等条约”和“庆祝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标语。我的软禁自动解除了。校长、教务长见了我又有了笑容,同学也敢接近我了。这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次价值突变。
原先,教会学校的学生组织只有基督教青年会,会务大都由少数教徒把持。不信教的同学一直有意见。北伐军到北平以后,各教会学校都成立了学生会,崇实当然也闹腾起来,并且公推我当学生会主席。我还以这个身份去南口参加了一次庆况大会。是露天会场,台上坐着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四巨头。当时兴奋极了,真以为革命成功了,古老、封建而且分裂的中国,转瞬之间变成统一而民主的新兴国家了。我们的少年团和十人通信团也重新活跃起来了。
提灯庆祝会那晚,我举着盏灯笼,从北海穿过中南海一直跟到天安门,一路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当时洋校长以为中国真的赤化了。为了安全起见,像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那次一样,他和家人又躲到北戴河去了。校务交给教务长(一个中国人)代理。
这时,我依然在教务处干油印活儿。有一天,那位胖胖的代理校长笑眯眯地走进油印间,要我先放下滚子,坐下来同我作了一番恳谈。看来他是要把我这个新选出的学生会主席牢牢掌握住,所以在劝了我一大通之后,就为我描绘了一种前景:
“你四哥不是齐鲁毕业的吗?你要是踏踏实实地干,毕业以后,学校也可以保送你进齐鲁。日后说不定你还可以像我一样,到美国去工读呢。”
当时我刚上高中三,还没考虑毕业以后的事,他倒比我先想到了。我乍一听,倒也动了下心。接着他提出不要解散青年会,要我跟学校合作,“千万别走上邪路。”最后还带点恫吓地小声补上一句:“别以为现在什么都变了。”
学生会成立大会举行了。尽管台下都是很熟的同学,那毕竟是我一生第一次主持的大会。会上,有些同学发言慷慨激昂,认为以前的青年会都是些校方的狗腿子把持,对穷学生一点也不讲公道。提议干脆把青年会解散,该会原来那间办公室由学生会接收。付表决的时候,竟然全体都举了手。
晚上,我在灯下给一位已考进燕大的华侨同学赵澄写了信,叙述完白天的事之后,我写了几句出气的话,并告诉他:“胖子(代理校长的外号)想收买我,我总算挺住了。”
人有时候在重大事情上会疏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我丝毫也没察觉自己在校方眼中早已成为危险人物,一个眼中钉。这回虽然并没软禁,其实我一直在被监视着。我一向不买邮票。发信,总是只把封好的信和二分钱往门房窗台上一放,到时候就走了。这回也是如此办的。
不一会儿,有人通知我到教务处去一趟。一进门,只见代理校长的胖脸气得红胀。桌上放着我头晚写的那封信——已被拆开了。
他劈头就气哼哼地质问我:
“教会给你工读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忘恩负义!”
我也理直气壮地反问他:
“你凭什么拆人家的私信?”
他冷笑了一声:“不但拆你的信,我还要把你开除掉。”接着又说了我“不知好歹”的话。
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我以为国民革命既然成功了,人人都有了公民权,拆私信他就侵犯了人权。我说,我要去控告他。
“好,好,快去告。”然后他指着房门说,“可是你得先给我搬铺盖!”
实际问题来了。今晚我在哪儿安歇呢?堂兄家早已不是我的家了。我咬了咬嘴唇,就走出了校务处。
楼梯上,这会子已经围满了人。几个走读的同学一听说我被开除了,就异口同声地上赶着说:“到我家去住!”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孤单。我对一位住在香饵胡同的张姓同学说:“那么,到你家去吧。”
就这样,我走出崇实的校门,走进了广大的社会。那里的现实,同我在学校里设想的可大不一样。这时,我想起代理校长的一句话:“别以为现在什么都变了。”
五色旗已永远地摘下,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但是中国非但未赤化,而且凡是同赤化沾过边儿的,又成为侦缉队的捉拿对象了。我要去市党部控告,知底细的朋友劝我可别去自投罗网。由于那次被捕,我早已上了黑名单。
这时,赵澄恰好接到一份“母病危”的电报,正要回老家汕头。他慨然表示愿带我南下。
这样,两天后我就离开了这座哺育了我十八年的古城,跟着他茫然地踏上了漂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