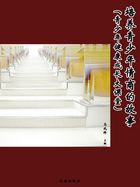检查留言箱的时候,布莱里奥发现父亲已经给他打过两次电话。这时候,他正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刚好位于阿萨斯路和奥古斯特·孔德路的交叉处。背靠着公园的栅栏,他被热得一阵阵发晕。
他甚至感觉自己已经六十岁了。
突然——既无预兆,也无警示——他在最后一条留言里听到了娜拉的声音。随即,大脑内所有关于父亲和母亲的信息全部消失无踪了。
这是耶稣升天节后的第二十一天。
她跟他说的是英语,一字一句说得非常清楚:她将在五六点的时候到达多麦斯路的那家咖啡店——以前他们经常在那里约会。如果他不能到的话,她周二早上一定还会给他打电话——她留言的语气很肯定,而且最后还不忘吻他。
当布莱里奥顺原路穿过公园返回的时候,他走路的姿势突然完全变了,脸上也容光焕发,以至于长凳上的几个人怀疑这还是不是刚才经过的那个人。他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改自己的年龄,走路那么快,以至于疾步向前的时候,竟然超过了两个正在跑步的人。他一路走向离公园最近的地铁站,步行的速度可以赶超专业的竞走运动员了。
但是他一边走,一边还是不停地想问题,尽量让自己不激动,走的速度不要超过音乐的节奏——这样才能冷静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当然很清醒:绝对不能浪费这第二次机会。相反,他要珍惜它,将它舒展开,组织好,归于计划,付诸实践,直到将这个机会拥有一生。但是他不知道,他们将从哪里开始。
一切都取决于她,取决于她对这次见面的期待。
在他看来,此刻,他只是在重新做回自己——在消失了两年的自我之后。
就在他一边冥思遐想,一边尽量控制自己的行走速度时,他有种感觉——似乎他被生命之流、激情之浪所裹挟,就像个孩子迫切地想快乐那样,人行道上每走一步,都有要跳起来的冲动。
就这样一边走,一边狂想,布莱里奥足足提前了一个小时到达了多麦斯路。到达了约会的地点后,他站在一个小卡车的车窗后“侦查“——以便于第一眼就能看见娜拉。
之后,他突然冷静了下来,几乎感到一阵放松——犹如意识被剥离了。他感到自己不是在此刻,而是在回忆此刻——所有他看到的都如同印在了一帧帧的电影胶片上。
巴黎上空各种形态的云在胶片上,死胡同里的那辆黑色轿车在胶片上,那两个刚从宾馆里出来的金发女郎、正在用面包屑喂鸽子的中国人……另一个正在焦躁的乱翻手中的导购报纸的中国人也出现在胶片上,当然他自己也在上面。
五点整,娜拉在迟到了两年之后终于来了。
当她在原地转着身寻找他时,一切声音似乎都消失了,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就连地球似乎都暂停了几纳秒的自转。旁边的两个中国人看到眼前的一幕也禁不住吃惊。布莱里奥明显意识到自己的激情在跳动,犹如一种声波——他正在计算声波传播持续的时间。
实际上,他认出了是她,然而此时的她自己又似乎已经不认识。
在那天的她和今天的她之间,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她。也许是卡车窗玻璃的缘故,他感觉到似乎一层薄薄的胶片挡住了自己的视野,胶片中的娜拉既是她自己,又似乎不像。
她依然是那么青春夺目、光彩鲜艳,依然是那头齐耳短发,还有那几个雀斑——这些都是她最明显的外貌特征了。而且还是那么优雅,黑色套装里面是一件白T恤。但是还有其他东西:她的脸有点变了,瘦了一点,更紧绷——也许是焦虑的缘故。
她在想也许他不会来了。
然而布莱里奥这时还是只在暗处观察,一步也不动——尽管内心已经激情澎湃。他的双眼始终贴在车窗上,想让自己牢牢记住再次见面时刚开始的这种快乐的感觉——趁未来还没有开始,一切都还平静。
当他从隐蔽处站出来,举着双手就像投降那样对着她时,她看着他,做了个滑稽的鬼脸,是惊讶,更是羞涩。然后跑了几大步一下子扑到他身上,抱住了他的脖子,一点儿形象也不顾了。
“哦,路易,我好想你,好想你啊!“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想他,激动得就像一个还没有跟男孩子拥抱过的女孩一样。
两个人都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布莱里奥想试着嘟哝出一些话,表示欢迎她回来,也想表明自己是多么想她。但是他的声音屡次中断,挤出来的几个字只是“内维尔,我知道,我向你发誓我知道。“
她不会明白他到底知道什么,因为——她已经将他带到了咖啡馆内,手拉着手。
他们的手已经两年没有彼此牵过了,都在急着寻找对方的手,都是那么温热潮湿。指尖传过来的电流瞬间使彼此都感到那么幸福。
等眼睛适应了咖啡馆里黯淡的光线后,两人立刻机械地走向了以前经常坐的位置——靠走廊的角落,还点了相同的饮料,就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一样,爱情穿越时空后又完美再现。
然而两个人的感觉还是有所不同:对于她来讲,似乎离开他只不过半个月而已;而他的心却已经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二十五个月三周零五天。
激情过后,双方都冷静了一点儿。当他问起她在巴黎打算怎样生活时,娜拉带着点犹豫的笑容告诉他:她希望赶快找一个迎宾小姐的工作——现在的她一没工作,二没钱,正是最狼狈的时候。
如果不是刚好有个机会可以住一套郊区的房子——她的表姐芭芭拉借给她的,她跟布莱里奥解释说情况还会变得更复杂。
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布莱里奥还是不大喜欢谈这些涉及物质的东西。他更想谈一谈他们之间的事,谈一谈她自离开巴黎之后的生活。但是凡事都是该来的时候必然会来。
尽管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但同时也是个做事畏首畏尾的人,所以当然也不敢建议她立刻带他去参观下那套郊区的房子。而她却一点都不着急,又点了一杯啤酒,似乎两人的共同生活就在眼前,需要的只是漫长的等待而已。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很明显面临着相同的焦虑。
不管怎样,他该建议她打车离开了——她看起来就是在等这个建议。然后,她将啤酒一饮而尽,嘴唇上沾满了啤酒泡沫。
之后他们一起走向多雷门,去找附近的地铁。他们一直手拉着手,腿也好像失去了重力影响一样——似乎是在滑行,是舞蹈家在跳双人舞,而不是在走路。
尽管他们都走得很快,然而调整了几下步伐后,两人很快就再次找到了默契,也找到了在大街上并排走路的快乐,还有在出租车中的热烈拥吻的激情。
出租车进入环城大道后,他们就一直拥吻在一起——这个长吻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布莱里奥甚至一直感到有点窒息。终于在几公里后,车停在了里拉镇一个前方没有出口的小巷中。而他们也结束了长吻,走出了出租车。眼前是仍然有点灼人的傍晚的阳光,还有阳光下的一座白砖小房子。“就是这儿。“娜拉推了下花园的大门。
“你知道出什么事了吗?“娜拉突然给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袋。“不知道。“他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找不到房子的钥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