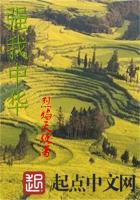那天,她刚满二八,正是妙龄芳华的时候。本来她已私心暗属,喜欢上了一名英武的将军,却突然被父王许为王镕家的公子。虽然她有几分不乐,也曾暗自哭了几次,但父命难违,只得从命。
金秋十月,选定的良辰吉日,父王为了置办了奢华的嫁妆,金玉珠宝多得数不过来,装了十大车。她却没有丝毫做新娘的欢喜。
花轿来到,她才惊醒青春年华就此结束。而那位心爱的将军就在送行的队伍之中,却不敢向父王禀明真情。她好恨,任仆媪扶入花轿,与王昭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还曾暗暗伤心。
揭了盖头,借着红烛看见昭祚郎君好样貌,心里才算稍有满意。
昭祚偷眼看普宁的丰姿,不说美若天仙,也有九分的姿色,也很合心意。到了夜间,仆媪们铺好了床。玉钩帘下两床被褥已经展开。
按照旧时俗例,新郞用红被,新娘用绿被,床上两色被子,他家自然也是如此。
当仆媪们退出,谁知他王昭祚竟不理不顾公主羞答答地不敢抬头,也不给公主脱衣,竟自己钻进账内,早已钻入绿被之中。
公主等待许久,不见郎君为自己脱衣,悄然四顾,恍然看见床帐间露出一副胆怯的面孔,卧在那里竟如一位柳眉杏眼的女人一般。
公主吃了一惊,以为是哪家的女人不怀好意,占了人家的被窝。正想发怒,我是明媒正娶的公主,哪来的骚蹄子敢爬上我的床?低头细看,原来是他,正偷眼看她。
公主平素也是决断之人,又气又恼。罢了,今天你既然甘心做我的老婆,我也无妨做你的丈夫。今宵就算我是新郎,你是新娘。
她恼了一会儿,只得钻入红被之中。两人竟一夜无事。
次日,二人起床,梳洗已毕,昭祚竟自己跑了出去。到得中午,二人同案吃饭,例行男左女右,他竟又坐在了右边,不由得又把自己的位置占了。也罢,公主只得坐在左位。暗自笑他:活该他是给我做定了媳妇。
这样过了好多天。公主暗藏心事,永远这样过着才好。直到一夜,王昭祚酒醉得心旗激荡,不顾公主反抗,成就了夫妻之实。
从此以后,二人除了那件事不能假借,此外的举动,一齐颠倒。公主好像是家里的主子一样。从这件事看,王昭祚的相貌亦是不俗,却又有几分女态。是个怕老婆的种。
这样也不能怪他,史上有多少驸马不是如此。
王昭祚果真在殿上痛哭流涕,痛说自己多么的不想离去,老丈人对自己是如何地开恩,自己又是实在不得已,老父思念成病才要回去尽孝的,之类的话讲得连自己都深觉可信。朱温看着下面跪着的懦弱样子,开怀大笑。
谅下面的这个小子也没胆子与我对抗。
既使要送女儿,当然要有皇家的体面。赏赐了许多金银珠宝、珍玩美玉、绫罗绸缎、摆器用具及路上吃的点心果品,权当是嫁妆。直把唐王的天下当成了自己的,任取任用。
反正早晚是朱家的天下,尽快放诏天下,登基为好。
出行之日,朝中的大臣,朱温的儿子和养子们,前来送行的队伍排到了城门外。一千禁卫军是护卫主队,正是卢益。
那日容少卿离宫,谢崴虽然怀疑另有蹊跷,却也没有查到他的头上。
王镕派来迎接的队伍有三百人,带队之人是左牙将皇甫鹤,另有公主身边的亲信队伍二百人。共十辆大车拉着货物,普宁坐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锦围华盖,其它女眷几人共坐一辆,也凑了三大车。王昭祚则是一骑肥壮的高头大马,模样也很是风流潇洒。
正在与众亲友话别,镜儿单骑飞驰而来,荡起一片尘土。
到得近前,她以极美俏的姿势旋落,大喊:“姐姐别走,我也要去!”
普宁气得笑了起来,“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怎么还要胡闹,父王答应你了?”
“那是自然。我求父王,他老人家已经同意了。”镜儿嘟着小嘴,“姐姐为什么不等等我?”
“反正我不管,你不同意我也要去,你不要我,我就自己走!”她决心已定,策马江湖的日子早就是她的梦想。
无奈,只得带上这位半大的孩子,比烈马还野的野丫头。
一千五百名军士分做三批,前批探路,头哨在十里之外,每隔二里放一哨兵,后哨在一里之外,随时汇报前方情况。皇甫鹤在香车左右,近身护卫。后队负责众家眷的安全。
路上还算平安,一路遇山翻山,遇河过河,所经之处除了少量的大镇还有热闹的气象之外,大多村庄少有人迹。甚至在偏僻一些的村落,竟然是破败的空村,无一人居住。饿死被杀的尸体堆积如丘,显然不久前才发生过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