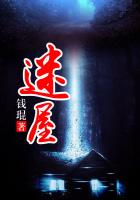在乔雅·赫葛咽气前,赫葛先生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上门讨伐塞弗洛一家了。
然而,满屋蔓延的如同蛇皮般的树皮将赫葛先生阻挡在了门外。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带头对着自己太太挥舞拳头的男人像一头脱水的啮齿动物般扑向自己的场景。屋里一群已经不是人类的生物翻着瓷白的眼眸,裸露尖锐的门牙,相互依附着啃噬对方的脊背。最后一眼,他看见只剩一张死不瞑目的脸能被辨认的老塞弗洛倒挂在过廊梁顶,“它”眼睑一扬,倒看着仿佛狞笑一般——是的,最后一眼。
三天之后,送货的小厮将三张散发奇怪气味的床板放在赫葛家门口,怎么喊都没人来应门。
“他们一家移民了。赫葛先生已经委托把东西交给我了,拿过来吧。”
小厮不情愿地又把货物推到隔壁这家人门口,抬眼瞧了瞧眼前这个老眼昏花的瘸子,“我只负责送货到赫葛家,既然委托你了,东西你就自个儿抬进去!”
“如果我加钱呢?”老瘸子扬了扬眼睑。
小厮向前挪步,向这幢两边种满胡桃树的宅子里张望,里面阴沉沉的,什么都辨不清。估摸着确实是个穷鬼家,他反而觉得值得一讹了,立刻比出一个巴掌。
没想到,对方却塞给了自己高出预期10倍的金额,并慢吞吞地说:“那么,以后诺珸家有什么需要,还请小哥多费心。”
小厮顺从地把滑腻坚实的3张床板放进耳房储藏室,一脸赔笑说:“我们伊鲁索里人是最好客的!放心做好你们的外省人吧!”
送货小厮洋洋得意地带走一身异香和厚实的钞票。
他只负责送货,哪里明白,纸钞也是木头做的……
老瘸子关上大门,隔绝了阳光的屋子渐渐显露出装潢细节:苍翠的印花布纹墙纸被橡木软包紧紧包裹,燃烧树脂来照明的灯烛头凝结成一簇簇琥珀,宛若昆虫的卵囊。大件的家具、小件的装饰物,目所能及之处极尽木料物事,肃穆而阴翳。
“他们家是独子,偏偏是3张床……”
少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储藏室门口,黯淡的光线下,瞳孔透出微微的萤火绿光。
“问问厨子不就明白了么。”管家模样的老瘸子语气轻蔑。
一个身形肥硕的人听见有人唤“厨子”,便一摇一摆从楼下窜上来——俨然就是赫葛先生。
伊寥萨白了瘸子一眼,“那我问你,你的儿子是怎么死的,你又记得么?”
老塞弗洛的脸色顿时沉下来,被问得哑口无言。他只得对着已经变成诺珸家厨子的赫葛先生大呼小叫道:“没事了!回去备膳,少爷马上就回来了!”
赫葛厨子灰溜溜离开的蠢态让塞弗洛管家稍感安慰,重新安抚主子说:“今晚一定会是三人晚餐,少爷会找到那个女人的。”
伊寥萨并没买账,只淡淡地指了指对面曾是赫葛府的宅子吩咐道:“我们不需要两栋庄园,把那边的改成灌木园。记得,必须是花期长的灌木,总得留一部分光明让诺珸家显得亲切友善。懂么?”
老塞弗洛从左胸掏出绢巾,流畅地抛起用左手一接,左臂立刻变作硕大的园艺剪。他欠欠身,恭敬地应答:“小姐放心。”
伊寥萨哪里能放心。她不过是自欺欺人地想证明,那日听到的女声是一时幻听。
********************************************************************************************
伦理,其实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一片充满魔法和怪异法则的郡土里,如果没有足够开放的脑洞,还真容易着了一些怪异路数的道。
在赫葛先生举办那场断送自己性命的茶话会前,其实并没有人知道伊鲁索里来了诺珸一家。但在那天以后,茶客们各自回到家,异样终究会被传播开。因为那片作为赠礼的貂脊葛可以让他们忘却乔雅?赫葛被群殴,可以让他们忘记真正的老塞弗洛已死,却无法改变“老塞弗洛不是什么老佣人,而是塞弗洛府主人”这一公认的事实。
海特缇一家正为自己老爷过早出现“老年痴呆”症状而焦头烂额。
这日,西晒的海特缇书房又一次爆发激烈的争执。
“我说过不下一万遍了!没有什么塞弗洛的瘸子主子!赫葛家也早就移民了!”
“亲爱的,怎么又改说辞了?赫葛家什么时候移民了?你和赫葛走得那么近,不是才去他家参加茶话会回来么?还有,你忘记了么?塞弗洛家前阵子小儿子刚出了事……”海特缇夫人无奈地纠正着。
海特缇先生一怒之下掀起厚脊书就向自己妻子砸去,险些砸中人的书本被摔得四分五裂,“你这足不出户没见识的妇人!你要是有点智商,你就自己走出家门去和外人交际啊!我都说过了——赫葛家对面住的是诺珸家,诺珸!”
头一次被丈夫骂得这么毫不留情,还动了手,温驯的布岚内斯·海特缇哭着跑出了书房,躲回卧室抽泣。丈夫原本性情温和,看中的便是自己知书达理,所以从不介意自己惧怕社交,宁可被别人说三道四,也要维护自己。可自从上次去了赫葛家茶会回来,关于赫葛和塞弗洛一家,丈夫变得开始胡言乱语起来,并且笃信自己所说的一切。日子久了,更是添油加醋地给自己的胡话追加了各种奇怪的解释,今天又提出了“移民”一说。
“对了,他说塞弗洛家住的是什么人家来着?诺,诺什么……”布岚内斯冷静过后喃喃道。
“母亲,父亲又骂您了么?”
这时,一个梳着精致卷辫、模样秀气的少年走进主卧。他见着满脸泪痕的母亲,心痛地将眉头蹙成一个结,眉尾的痣都挪了位置。
“没事,没事的,彻里,是我太心急了……”布岚内斯勉强笑笑。
费彻里·海特缇自然不信,他走过来坐到母亲身旁,手里举着一个透明小袋,里面装着一片丑陋的树皮,“我觉得父亲的异常和这块树皮有关。”
“这个是……”布岚内斯伸手就想接过去,但被儿子迅速制止了。
“这是父亲从茶会话上带回来的。这东西气味刺鼻,我已经用玉面胶封存了,估计嗅到这味道就会像父亲那样说胡话的。”费彻里收回袋子继续道,“我问过那天和父亲一起去赫葛茶会的莱克家,他家主事也说莱克先生回来后也拒不承认塞弗洛家的存在,并且提到了一个姓氏:诺珸。”
“对对,刚才你父亲也提到这个名字了!”布岚内斯激动得像是找出丈夫病灶一样握住了儿子的手,但仅仅两秒后,对视着儿子笃定的眼神她连忙摇头,“彻里,别做傻事。你父亲只是混淆了两个与我们无关的姓氏,其实对我们生活也没造成多大影响,不再计较就过去了……”
“没有影响?他已经开始伤害你了!”费彻里腾地站起身,坚定而不失温柔地安慰母亲,“相信您儿子,他不傻。”
没等布岚内斯继续劝阻,楼下传来女仆的尖叫。
二人跑到1楼门厅口时,女仆正倒在地上瑟瑟发抖,她指着门外,气声嘟嘟哝哝:“赫,赫,赫……”
费彻里把母亲护在身后,只见屋外侧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脸肿得像一颗刚被手术切除的肿瘤,青紫斑斑还敷着脓。
“赫葛太太?”费彻里吃惊地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