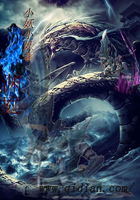一条无人的林间小道上,两旁光秃秃的的杨槐树木向前开始变成长青的松柏林,枝叶多了起来,光线就少了起来,世界就暗了下来。
一道背影地上拉着一柄大锤在缓缓地朝远方缓缓走着,从光明走向黑暗,步子飘忽不定身体左摇右摆,好像一阵风就可将他吹跑,吹到天涯海角。
他是个路痴,若真是那样,就肯定再也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的人,就叫死亡。
一直走着,仿佛要走到世界的尽头。
一阵寒风吹过,身体打了个寒颤,脑子恢复了一点意识,无神的瞳孔终于有了点焦距,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他是林邈。
缓缓走在树林间,神色茫然浑身是血,大片的血迹黏在衣服上板结成块,散发着一股血肉烧焦的气味。
已筋疲力尽,视线会时不时模糊不清,眼前有时会间歇性的黑暗,紧接着就是一阵天旋地转,好像死神在向他招手接引他走进死亡之门。
很累,手里却依然攥着一柄开石头的长柄大锤。随着不断前行,大锤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印记。
脑袋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怎么从那个别墅离开的,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只是凭着惯性茫然地向前走着,可浑身的骨头仿佛全部碎裂,好似只有一层皮包和着身体。
想停下来休息一下,可感觉自己只要停下来就会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不能倒,因为父母正在家里等着他过新年。
他们会像木偶似的可笑地杵在大门口,看到林邈一身脏乱开口就是一通义正言辞的训斥,然后便会忙手忙脚地扶他进屋躺下,再给他倒茶倒水焦急照顾,放下心来又是一通训斥。没有文化,话的内容就还是那干巴巴几句,就从他不记事说到上大学,从青春说到苍老,不知说了多少遍。
这时候他应该大声地回两句,表示讨厌他们的啰嗦,表示自己对他们言辞如此匮乏的嘲讽。
可他已没有力气张口。
拉着大锤,感觉就像在拉那曾经在杉龙大学琴海分校参观过的184吨重的韶山4号改进型火车头,于是父母突然消失了,他变成了一匹马,但不是那精力充沛尽情奔跑的小马王,而是匹快要死掉的干瘦跛**隶马。
套着缰绳的头颅顶着自由的天空,刺入脚掌的蹄铁踩着翻滚的岩流。
天生任人驱使,职责就是去受罪。
他的任务是拉着火车头走到世界的尽头。
于是在脑子里咒骂起来,为什么要造那么重的火车头,关键是为什么要让他去拉火车头?
林邈不想吃草,草很难吃,小时候吃的满嘴里又苦又涩,他吃三毛钱馒头,一顿饭只吃两个,连菜都很少舍得买,不买菜就要多吃一个馒头,不然晚上会饿醒。
那就会光着大半屁股蹲在铁床架上,凌冽的冬风会像热情的少女不经男主人同意就及时从窗户溜进来,然后悄悄站在他撅起的屁股后,缓缓伸出如玉的小手,却攥着一把缝衣针去猛烈地戳眼前的两半大肉蛋。
她会阴谋得逞地哈哈大笑,他则躬身背对着,五官扭曲努力地忍耐着,嘴里啃着根辣条心里不停默念‘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然后辣条两口下肚急忙钻进被窝感受着火热在胃里翻滚、热量在身体里释放才被肚子允许进入睡眠。
社会上到处需要虚假的关系,林邈想在学校里过一段单纯的日子,所以他不想对一些不可靠的人树立不可靠的人缘,更不会搞些虚假做作的东西去拉拢人。
结果他们最后也就不把贫困助学金的名额之票投给他。
选的是人缘,不是贫困。
想要钱,还不想吃草。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林邈就是个沙比。
但他们是白痴。
道不同不相为谋。
沙比不可与白痴为伍。
沙比不想吃草,想把手里沉重的火车头扔掉,可手攥得太紧,右臂从肩到手掌的肌肉已僵化,长长的锤柄好似嵌进了他手心的肉里,再难分开。
他清楚地记得,之前把那个男人的身体完全撕碎生生吃光了,打破了无形的禁锢,所以他没死。
就在要扭头继续吃身旁那个老头的时候,世界降下了大雾,什么都看不清,老头突然不见了,所以他异常愤怒。
天上突然适时降下来一个大锤,好似神明的礼物,他伸手握住了它,只要将这片雾砸碎,就能将藏在雾里的那个老头砸成肉泥。
哦,于是想起来,自己不是一匹马,手里拉着的也不是火车头。
那就感觉不是那么沉了。
锤头是好的,可以让他不被一阵风吹跑,可身体已没了力气,为什么不让他早点想起来呢。
握着锤子的僵硬手臂突然颤抖起来,身体左摇右摆,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怎么会想杀人呢,怎么会去吃人呢?
他是个好孩子,从小不去和人打架,别人打他他会告诉老师,尽管这样就不能找理由打回来了,但从来不会想要去杀一个人,还是撕扯身体虐杀,还要吃人肉,这是魔鬼要做的事!
跛脚瘦马的任务是拉火车头,他的任务是上大学,魔鬼的任务是让人类恐惧。
他不会这么做的,那是魔鬼的工作,那是罪孽,那是一场梦。
于是,牙缝里那残留的人肉味道开始模糊然后变淡最终消失。
林邈的后背已然被冷汗浸湿,内心却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那个小女孩呢?他刚从水底出现要凶狠地举着锤子轰碎一切时,却突然发现眼前坐着一个身穿黑色绒袄蜷缩成一团的小女孩,孩子的表情好可怜像是受到了惊吓。
女孩的五官太精致,所以他也看得很清楚。
他的锤头堪堪停在她的额前,他差点就把小家伙的脑袋砸成了肉泥。
是假的,都是假的。
不然,自己怎么能站在水面上呢。
眼前又是一阵黑暗,天旋地晕。
林邈摇摇头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他已清醒了过来,知道不能再继续走了,那样说不定真的再也找不到路。却不敢停,只能尽可能放慢步子。
想歪头找个自己撞不断的树,脑袋却沉得要命,只能是眼睛四处瞟了一圈,看到身前路边一颗碗口粗的松树,感觉很满意。
于是拉着大锤挪动过去,就一步的距离,使使劲努力迈开步子,感觉身体的筋就像被抽掉了一样,软塌塌的快要没有知觉了却又异常的沉。
人的筋听说有五十多米,要是接在一起摆在大街上应该很壮观,他这样乱想道。
慢下来之后再想加快步子却是异常的难,身子已有多处部位失去了知觉,感觉变成了木头,就他就想起在梦里审的那两块迎风摆动的腐朽木头。
艰难挪动了半天才要到达,这才发现自己走的确实不如蜗牛快,那迷路的问题应该好解决,自己肯定没走多远,至少肯定还在这座城市,江家别墅他还是认得的。
林邈不知道自己身体损伤什么样子了,但追梦之人自然满怀期望。
他觉得自己会活下去。
突然吱地尖锐一声响。
耳朵本来像变成了木耳,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或许是声音太过尖锐的缘故,他听到了,那说明耳朵还能用,真是个令人高兴发现。
声音在左前方至少十几米的林子里,脖子扭不动,眼珠子想瞟到那里就需要摆脱眼眶的束缚跑到外界来,他还没有那种360度环视的超能力。
该死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束缚呢?
那就不看了,他依然朝着前方走,确保自己会准确地撞在树上。
又是一声尖锐的响。
他昏昏欲睡却仍然有心情烦躁,想那是谁家的孩子在吹破哨子,吹得这么难听,好像要死人似的。
真晦气,林大官人可是要长命百岁的。
林邈终于一头撞到了树上,身子直接软塌塌贴了上去,两手臂顺势夹在松树上两个发育不良的突起,然后像块软泥巴似的缓缓滑落。
因为脚底没动和右手边那柄锤子拖在地上扯着的缘故,下滑的过程中上身围着松树左转了几乎270度,可以坐在树林里看到来路,才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他感觉做得很成功,有了松树的借力,休息之后应该可以再站起来。
眼皮使劲撑着看了一眼来路,一道长长的印记从远处路的拐角出现然后连接到身旁的锤子,他可以跟着这道印记找到回去的路。
现在要做的,就是睡觉。
眼皮像挂了铅块沉重无比,睡觉是一件美好的事,或许还可以醒来,或许再也醒不了,那又如何,累了就要睡觉,他要任性一次。
他太累了,累了二十年,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次了。
闭上了眼,身子慢慢歪倒了下去,在倒地的最后一瞬间,又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有哨子就有人,尽管声音很讨厌,但这么近的距离发现自己的可能性很大,自己被救的可能性就很大。
他又想到了那些在马路中间勇敢倒地的老爷爷老奶奶,感觉自己被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那没关系,只要自己醒了,就会走回去。
今天小年,却是回不了家了。
闭眼的最后一瞬间,他还是斜眼朝哨子响的方向看了一眼,以他现在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
或许是身体变糟的缘故,感觉自己开始产生幻觉,快要闭合的视野里,一个快两层楼高的血红色大蜘蛛在跳舞,八条巨大的肢节飞快舞动舞成了一朵朵巨大的罂粟花,残影娆动异常艳丽像是世间最美的圆舞曲。
肢节下有个光头的小蚂蚁穿着僧服在不断躲避大蜘蛛的舞步,蜘蛛一声尖锐的愤怒鸣叫吐出漫天的白色蛛丝,蚂蚁便上下翻飞、身形灵动,像是个演杂耍的猴子。
大冬天的还演杂耍,看来人过的都很辛苦。
他闭上了眼,世界便成为了一片黑暗。最后默念着蜘蛛到别处跳舞吧,小猴子不要太累,至少不要去拉火车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