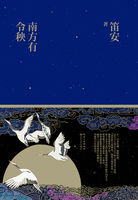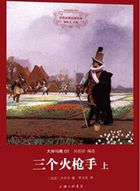从那一天往后数了很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怎么见过我爸,陵城有官员落马,他总要这么忙碌一阵。
这次是个大鱼,分管城建的张副市长,此人也算是年轻有为,省长秘书出身,四十出头被下到陵城出任市委领导,已有三年之久。
零二年春天就有匿名信寄到省纪委,后者刚开始调查,他们书记就被张的老领导请到办公室。年近花甲的省长拍了桌子--这算什么,我身边的人,刚下去做出一点点业绩,就有人开始不安分了?举报材料我看过,都是些捕风捉影莫须有的东西,小张身居要职,得罪人在所难免,你们这样配合,搞得人心惶惶,以后还有没有人敢做事?老百姓再抱怨政府效率低下,你们纪委的,都给我站出去承担!
纪委书记从省长办公室退出来,连夜找到省委一把手。
一把手沉吟良久,查,一定要查,但老同志的意见我们也要尊重,有些事进行,但不要放到台面上。
于是,案件转入地下,一查就是一年多。期间省领导班子换届,省长退居二线。
线索千丝万缕,收网却收的非常突然,被监管起来之前,张副市长前一天还在本年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时间,陵城中层以上干部,人人自危,张副市长被双规的第二个月,沈伯伯被纪委传去谈话,接受调查。
我那段时间,正是考研复习到了第二轮,每天泡在图书馆和自习教室,对这个事一无所知,等我知道,它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没有查出什么大问题,据说张副市长在位三年,沈伯伯逢年过节时送的礼金,统共大概在五万上下,这在被调查的干部中绝算不上头一份,党内处分可能跑不掉,但还不至于丢官。
我妈这么告诉我的时候,也明显是宽慰的语气,是啊,毕竟是这么多年的邻里,谁栽在谁手里,大家都不好过。
她又问:“你最近在学校见过思博没有?”
“没有,我见他干什么。”
“听说他要出国了?”
我心里就好像有一个慢下来的陀螺,猛然间有人抽它一鞭:
“您问我我问谁去啊,是吧?”
“别给我阴阳怪气的。”
“我怎么啦,我还看书呢。”我捧着经济法真题:“齐享晚上过来吃饭,您烧什么菜?”
院学生会换届选举以后,一群人到佳缘小栈聚餐,我逗那帮学弟学妹:“挺好,我马上都退休的人了,吃饭还带上我呢,以后我经常得回来找你们蹭。”
“庄学姐,你是太上皇啊。”他们七嘴八舌,开酒瓶:“太上皇满上。”
“我事先说好,就一瓶,多了不行。”
当年被热水瓶烫伤的那位小陈说:“庄凝一向不是不爽快的人哪。”
“廉颇老矣。”我拍拍他肩:“这以后,你我退出江湖,就看他们年轻人的了。”
年轻人们纷纷做昏倒状,小陈笑:“他们给你面子叫一声学姐,看把你喘的。”
话是这样,确实也没有人硬是来劝我酒。
看他们一杯接着一杯,我有心劝一劝:“不是我扫你们的兴……”再一想,算了,真把自己当过来人了?不提远的,就大半年前,要有人跟你说,庄凝,不要犯糊涂,你听么?
这些小孩子都看着我。
“没事,喝吧,我忘了我刚要讲什么了。”我说:“人年纪大了记性就是不行。”
他们哄笑起来。
等差不多我下去把账给结了,老板娘还是以前的那一个,对我笑:“好长时间没来了。”
“忙啊。”
“快毕业了?”
“可不是吗。”
我曾在这个地方,享受我大学生活的第一顿午餐,似乎只一个转念,就到了现在,伏在柜台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有那么多的改变前赴后继,有些东西却一成不变。
这一天我去图书馆还书,又借了两本新的政治习题集,下楼原本该直接往借阅处走的,可是我站在回廊上,看见天井里盛得满满的秋阳光,乳白雕花的长椅安放于散尾葵旁,我立刻就不能动了,还有什么,比坐在这里翻一本游记或者画册,更可以引诱一个连背两天“新民主主义”背到精神衰弱的可怜人?
我在文艺借阅室的书架间穿行,饥渴极了,看见什么都想拿。我的亢奋终结于角落里的一本书。
它有着金色,暖洋洋的封皮,封面上这个端庄娴静的姑娘,芳名《阿米莉亚》。
这本菲尔丁的作品,当时我从谢端手里借过来,看了一小半就扔还给她,她很诧异地,不好看?
说不上来,反正我不喜欢。
我那时喜欢乖张的,戏剧化的,生于迷恋死于激情的玩意儿,而不是这种波澜不兴繁琐平淡的小儿女情长,我也不喜欢这个故事里,道德观固若金汤,善良从来无懈可击的女偶像。
她忍,忍,忍个头啊,我当时对谢端说,要我我就一巴掌上去。
但是谢端喜欢,她总是轻声细语地对我讲述布思和阿米莉亚的爱情--他带她离开她母亲,他们抵御诱惑,战胜困难,终得幸福绵长。
现实里有这样的事吗?我把抱在手上的都轻轻放到一边,从书架抽下那本书。
却有人在这本《阿米莉亚》和这排书架后面,开头我们并没有注意彼此,直到我听见手机震动,然后是熟悉的声音:“妈?……我还在学校……是的,快了……”
一边说,脚步声一边往外去了。
我跟过去,试图在书丛高高低低的间隙中看清楚,却总是晚一步,实在无奈:“沈思博!”
偌大的一间阅览室,我看不见他在哪,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我想,这就算了吧。
这时有人在身后叫我一声:“喂。”
我回头,他还是那个样子,清秀温和的,站在风卷起来的白窗帘前面,对我笑一笑。
“听说你要出国了?”回廊里安排了课桌椅,方便学生看书,我和沈思博面对面坐着,我问。
“嗯。”他说:“来办手续,退证件。”
“沈伯伯,他没事吧?”
“心情不大好,不过没事。”他回答:“你现在怎么样,工作找在哪?”
“没找。”我给他看我手里书的封面:“准备考研。”
“挺好的。”
“最近回家也没怎么见你。”
“出去了一阵。”
“哦,什么时候走?”
“明年春天吧,也许。”
这之后,我们沉默片刻。我想,他如果在等着我提到她,恐怕要失望了,不是我不愿意,实在是,无话可说。
“前两天,我还去佳缘小栈来着。”沈思博开口道,他可能也不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所以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最近也去的。”过了几秒我笑起来:“多快啊。”
他也弯一弯唇角,隔了一会儿:“要是她……”
我等着。他却垂下眼睛对自己笑笑,那是个黯淡的表情,意思是,何必呢。
然后他重新看着我说:“那,我先走了?”
“好好--哎!”
沈思博已经走出去两步,又回过头来。
“我可能没时间去送你。”我起身:“就在这祝你一路顺风。”
“谢谢,再见。”
我把书都收拾到臂弯里,对他点点头,然后沿反方向离开。
又过了两个月,有一天半夜我被苏玛晃醒了。
我火死了:“干吗?”
她瞪着两只大眼睛,遍布血丝:“你还问我?你刚一共喊了五遍‘综上所述’,我不管你述啥,赶紧述完,不然我还睡不睡?”
“……”
这就是我那一阵的状态,冲刺阶段,白天晚上都在不停做题,有时候到了梦里,思维还刹不住车,又疲倦又焦虑,每天洗洗脸就睡,长了一脸的痘,也不爱打扮了,所以当齐享元旦时说接我回去吃饭,我还怪不乐意的。
三十一号中午我给他拨了个电话:“喂,你在哪呢?”
“在房子这。”
“哪个房子?”我旋即想起来:“交付了,这么快?”
“昨天刚拿到钥匙。”
“怎么样?”
“地方不大。”他说:“不过,我现在站阳台上,能看得见陵河。”
“真的啊?”我有点心驰了:“可以在那放把躺椅。”
“包墙全弄成玻璃的。”
“再放个冰柜。”
“再在墙上弄个书架。”
“再弄两盆绿植。”
我们俩在两边同时满足地轻叹一声。
正在此时“砰”得一下,像有什么翻倒在地,我这里听都不小的动静:
“怎么啦,怎么啦?”
他隔了两秒:“楼道里的。”
“哦,没事吧?”
“我去看一看。”他说:“回见。”
我化个了淡妆,然后我把橱门打开,发现所有能穿出去的衣服,全都穿给齐享看过,有的还穿了好多遍,我默默蹲在衣橱前纠结了很长时间,曾小白问:“庄凝你蹲那儿干嘛?你是不是肚子疼?”
“你才肚子疼。”我说:“我郁闷呢。”
“怎么啦?”
“没衣服穿。”
“哈。”她笑了:“谁让你几个月不逛街。”
“我哪有空。”我怒了:“我要看书,上课,要吃饭,睡觉,我还要谈恋爱,妈妈的。”
“你跟谁发脾气呢?”
我说:“我跟我自己。”
“放心,他不会嫌弃你的。而且,”她趴在床栏跟前,看着我:“你什么时候这么小女人了?”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从放下电话,一直折腾到现在。”她看看手机:“一个半小时,你中午一般不午睡的吗?”
“来不及了。”我叹口气:“哪有人两点钟开始睡的。”
“我啊。”她重新仰躺下来,默了一会儿,说:“庄凝,你还记得那次么?”
“嗯?”
“零一年,我们一个寝室人仰马翻,为你赴约打扮。”她轻描淡写地说,抬了抬上身,似乎试图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时间真快,我他妈都要毕业了啊。”
我去自习前喝了一大杯浓咖啡,坐教室里坚持做完了一份英语模拟题,齐享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倒下了,胳膊下面垫着一本小字典,睡得正酣。
他把我叫起来,我惺忪地收拾东西,跟着他走出去,这会儿已是黄昏,沿着楼梯往下走,我抬头看看远方,不见光,灰云由疏向密地朝地平线堆过去。
我这边还在望呆,突然脑袋里嗡的一响,眼前就蒙了,如果不是齐享眼明手快地一把扶住我,我这一下摔得会非常惨烈。
他声音很紧:“怎么了?”
“别讲话。”我扶着他手臂:“我头晕。”
齐享打开车门坐进来,递一盒冰淇淋给我:“没事了?”
“就是太累,没事。”我接过它,另一只手把遮阳板掰下来,照一照,又转头对他瞪瞪:“看我的眼睛。”
他看了一眼:“何必呢。”
“我连简历都没做,什么工作都没找,这个再不上点心,真是彻底不想好了。”
他没有再劝我,只是问:“很有把握?”
“哼哼,基本上,志在必得。”我打开盒盖舀了一勺:“对了,中午那声响怎么回事?”
“隔壁邻居,老两口搬些杂物过来,摔了一跤。”
“这么吓人?怎么没让子女过来?”
“不在了。”
“……怎么的?”
“生病吧。”
“哦。”
我和齐享有一个共识,对于他人发生的灾厄,能缄默尽量保持缄默,过分的好奇和谈论难免有娱乐化的倾向,不厚道。
我就转了话题:“去了一趟是不是庆幸,你妈没听你的意见,坚持要买?”
“有一点。”
“你啊,不要老觉得自己一贯正确。”
他微笑:“我有吗?”
“还没有?”我说:“从认识你,你不一直这样么?”
“你能比我强到哪里去,小姑娘?”他转头看着我,说:“是谁,第一次见面就让我下不来台?”
“嘿嘿。”我说:“我知道了,就跟偶像剧里演的,你肯定觉得我特别不一样,就喜欢上我了,是不是?”
“我欠啊?当然挺生气的。”
“哦?那后来呢?”
“后来。”他顿一顿:“后来多了,你具体指哪一段?”
你看,你要是想听听这个人正经讲甜言蜜语,讲讲他是怎么被你吸引,你哪里与众不同之类的,总是要等的傻眼。
我没有办法:“小气。”
他笑一笑,没搭理我,我歪在副驾驶座上,迷迷瞪瞪地睡了过去。直到被车窗外滴滴答答的声音吵醒。
“下雨了,又下雨了。”
考试地点在市三中,第一门政治结束,中场休息的时候,旁边永和豆浆里满满当当坐的都是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