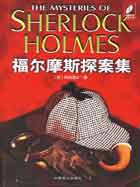那天傍晚,吃过晚饭,我就早早地赶到了舞厅。但走近舞厅那漂亮的玻璃大门时,我却踌躇起来。我紧握拳头,周身发热,血管膨胀。我忽然想起在学校时,一遇到与女同学一起的娱乐活动,我就躲,以致同学们都喊我“绝缘体”的事,心里一阵发笑。但想想,还是硬着头皮闯进去了。一进门,我立即感觉到一阵寒意,发觉许多的眼睛似乎都朝我射来。我习惯用眼睛审视别人,还不习惯有这么多的眼睛看我。立时,我就像一只要被人宰杀的小羊羔一样,浑身哆嗦。
没等我站稳,舞厅里的音乐就响了起来。
“是狐步舞!”我听见有人说。悄无声息地,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静静地观看。果然,就见一群“狐狸”从“森林”里、从“山峦”里溜达出来了。他们踏着音乐的节奏,迈着奇怪而又规则的舞步,或大摇大摆,或轻轻缓缓……夸张、扭曲,极尽身体之能事,让我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我一下子呆了,看了那些狐狸舞的动作、姿势,心里直想笑。
几只打扮艳丽的“小狐狸”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踱到我面前,飞眉抛眼地挑逗我。
我吓得慌忙摆摆手:“不会,不会。”
她们对我翻了翻白眼,疑惑地溜走了。
一会儿,音乐变了。场上响起了悠扬的慢三步舞曲,这音乐马上赶走了“狐狸”。舞厅里的男男女女全像换了人样,变得斯文、舒展起来。男人搂着女人,女人搂着男人,男男女女的在舞厅里迤迤地走动,动作悠然而优雅。舞厅微弱而带有色彩的灯光闪烁着,男女们胶在一起,就显得朦朦胧胧、影影绰绰了。我朝舞场张望了下,这下看见了朱良和他的女友小爱。小爱紧紧地依偎着朱良,像一只温柔的小绵羊,朱良将脸紧紧贴在小爱的头上,在昏暗迷离的灯光里,我突然发觉,朱良长得很俊秀,浑身散发着一种冷淡的美,不加修饰的如同大理石雕塑般的脸庞透着一股英气,有一种迷人的气息。
一位姑娘邀我上场,我本来还想推却,但身子却稀里糊涂地站起来了。不会跳舞的男人在舞厅里像一个体面的木偶,上场被一位陌生的女人搂抱,就变得像在表演拙劣的木偶戏了。我有些不自在。攥在她手里的手指在微微颤抖,所幸她并不嫌弃我,说是带着我跳。我努力地保持镇静,配合她,机械而被动地跳了起来。
灯光下,我看清我的舞伴是一位漂亮的个子高挑的女孩。她披着一头长发,随着舞步的移动,她那散发着香气的黑发时而打在我的脸上,痒丝丝的。“放松!放松!”她不停地轻声指导我,手柔柔地搭在我的肩上。我看她那眼睛里,像漾着一湖春水,波光潋滟。跳着,跳着,我分明感觉到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的手指在我肩上慢慢蠕动。接着,她就和我贴紧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被女性这样搂抱过,幸福得有点儿晕眩……
我们转到了朱良和小爱的身边,我对朱良古怪地笑笑,咧咧嘴,朱良说,“可以了,可以了,就那么跳啊!”
受了他俩的鼓励,我的胆子更大了起来。这人胆子一大,全身放松,舞步也就轻盈欢快了起来。就在我刚有点儿感觉时,舞伴的手突然无声地滑落了下来,她有些意犹未尽,抱歉地对我笑笑,我一愣,差点儿就踩到了她的脚背……原来,悠扬的音乐停了下来。
一曲跳完了。
出了舞池,我们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朱良和小爱也凑了过来。在聊天中我才知道,和我跳舞的女孩叫唐姣,在人事局工作,是外地刚分来的大学生。一听说她在县人事局工作,朱良一下子就来了兴致,问起了物价局“招干”的事。唐姣有点儿莫名其妙地望望我,我就把朱良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她说了。唐姣犹豫了一下,信任地望着我说:“没有啊!没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录用的人,下午都发了通知啊!”
“不会吧?听说朱良还考了第一名哪!”小爱插嘴道,“我前天托人问了,朱良考的成绩是第一啊!”
我也听人说朱良考试的成绩是第一。我不仅听说——我还知道朱良为参加这次考试,没日没夜地复习了好一阵子。我更知道,朱良天生的就会考试。朱良说他在学校读书时回回考试都是前几名,我不敢担保。但我知道他这些年不甘心自己一个中专文凭,不断参加自学,考了大专又考了大本,还获得过县工会“自学成才积极分子”的称号,在县里做过一次演讲。况且这次除了考试,朱良还找了章回那条“野”路子,应该不会出问题吧?我有些不相信地叫唐姣再想想,唐姣连想也不想,就摇摇头,说:“物价局就报上了三个人,我还能不记得?”
“走,我们找他去!”
朱良一听傻眼了。连忙拖起我,丢下小爱和唐姣也不管。我有点儿发蒙:“找谁呀?”朱良说:“我去找钱局长,人家都说我是考了第一的,千真万确,我去问他。”
我们在舞场就这样不欢而散,匆匆分手了。
八
出了舞厅,在路上我才知道,朱良在章回的安排下找过一回物价局的钱局长。熟门熟路,我们很快就到了钱局长家,朱良气呼呼地走在前面,毫不犹豫地就敲开了门。钱局长打开门,把头从门缝里探了出来。我立即看到了他的那张脸,大概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眼睛红红的,脸腮上凸起的一个肉堆上还溅着一星肉末。边开门,他边用牙签剔着牙齿,见是朱良,显然愣了下。这时,他家沙发上坐的一位老者见我们进来,立即就起身告辞,然后冲我古怪地笑了笑。
朱良没在意,我却“卡”在那里,心里忐忑不安起来。
“钱局长,说是成绩出来了,有我吗?”朱良开门见山。
“没有!”
“我可是考了第一的……”
“谁说的?再说,也不仅仅是笔试,还要综合考虑!”钱局长做一脸无辜状,“你别急,下回会有机会的……”
“综合考虑?”朱良突然一声冷笑,脸立即就变了色。“综合考虑?权钱交易吧?!人生在世……”朱良的声音忽然变得异样了起来。边说,他边开始打起了手势,他每说一句话开头都用了“人生在世”……人生在世,不能只考虑权,也不能只考虑钱,还得要有良心,要行得正,坐得稳……朱良说,倘若他这回考试考的是第一,就应该录用他,否则这就不公平,不合理。
接着,他就用种种理由阐述不合理的危害与弊端……
我知道朱良遇事沉不住气。但没有听过他这样乱七八糟的说话,对他又是挤眼睛,又是打手势,还假装着咳嗽。可朱良分明沉浸在自己情绪宣泄的快感之中了。他没有看见钱局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脸上聚集着乌云黑暴,像一场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你不要胡搅蛮缠!”终于,钱局长吼了起来。
“你也不要仗势欺人!”朱良也不饶人,“肯定有人偷换了我的卷子,瞒天过海……”
朱良终于用了荒诞的骂人的字眼,这脏话分明撕扯着钱局长的尊严和霸气。钱局长气得全身直打哆嗦,脸上那块多余的肌肉不停地颤动。转而,他顺手朝朱良脸上就扇了一巴掌,掌声在朱良的脸上停留片刻,然后灿然地绽开,飞快地结出了五颗仙人指一样的红印……朱良蹲下身子,呜呜大哭起来。
我傻了……但我看清了钱局长是用左手抽打朱良的,钱局长是个左撇子。
九
那些年,最为流行的一件事还有大报小刊刊登的“征婚启事”。我自忖家在农村,父母年老体弱,我的爱情运一直不好,又生性胆小怕事,我内心清楚我干不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再加上县城小得屙一泡尿都能转个来回,没几个人不清楚我的底细。写“征婚启事”,找外面的女孩恐怕就要好得多。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迷上了写征婚启事,满世界地寄发。当然不久也有好多的回信落到我的小木楼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信拆开,看看,按省份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锁进我的抽屉里。
我桌子左边的抽屉里横七竖八地就躺着这些信。
但是,我却不敢再有什么动作。条件好的,我害怕高攀不上;条件差的,我又不甘心。天高皇帝远,人生地不熟,后来,我每接到一封信就害怕。
我渐渐地就把这“征婚启事”当成一种游戏。
朱良进来了。朱良以前进门总“咚咚”地敲着,把动静弄得很大,现在他就不喜欢打招呼,像幽灵一样身子一闪,就进来了。为此,我说过他一回,叫他进门一定要打个招呼,或者还像以前那样敲门也可以——因为我习惯了。但朱良显然不管这些。他说,他不管我是不是有兴趣和他说话,他是愿意也想和我说话的。这一点让我反感,但也无可奈何。
可这回,他一进门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神情恍恍惚惚。
“你晓得是谁挤对我进了物价局吗?”
一进门,朱良就神神秘秘地告诉我:“你猜猜?”
“猜什么?进物价局的不就是三个人吗?”由于朱良,我也很关心这事。
“是上回在我房间打牌的那个家伙,叫陈亚军,我那同学。”朱良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上回我就犯疑心,他在乡镇蹲了几年,进城也从不找我们同学玩儿,怎么一下子就找上了我?什么狗屁朋友,就是他……”
“他?”我眼前立即浮出了那晚打牌的情景。点点头,说,“他是很有心计的……但你也不要老想这事。章回呢?对了,你该问问章回,他总晓得一点儿内幕……”
“章回?他这几天连鬼影子也没看见!看来,他是一张寡嘴,山高水远的,吹牛不犯死罪,实际上谁也不鸟他。不说他!不说他!”
“等下回吧!总会有机会的。”我趁机劝他。
“下回?我一没靠山,二又没有金钱,还能指望什么?这辈子都没指望了!”朱良垂头丧气的。突然,又张开双臂,说,“你不知道,这社会就像是一张网啊!网住了我们自由的翅膀!”他像诗人一样吟诵了起来。
我无语。
“你做吗事?”见我没理他,朱良话题一转,硬生生地问:“你又收到了许多求爱信吧?你就知道意淫,也是个窝囊废!满大街都有!你就不晓得找一个?对了,唐姣好像对你有意思,还问过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把她弄上床不就行了?我家小爱……”
朱良放荡地说着,说着,忽然就一阵怪笑,话突然停住了。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看他的眼里布满网状的血丝,吓坏了!
朱良的脾气一下子变得古怪和暴烈了。他在房间里一个人踱来踱去,大声嚷着:“你晓得吗?我和小爱要吹了,她大大说我是个废物,说我是食品公司杀猪的,我还不如一个杀猪的!”
“给我烟!给我烟!”接着,朱良找我要香烟抽。我给了他一支,他吧嗒吧嗒地吸起来。吸了半截,把烟扔到地上,又用脚踩,踩完了,他索性把我一包烟抢了过去,将一盒烟全倒了出来,在地上摆成了一个圆圈。“零点六一八,黄金切割率!”朱良说,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就开始砸东西,见房里有什么就砸什么。烟缸、书、钢笔、收音机……抓起来就砸,东西“啪”地落在地板上,他就随着那声音跳一下,说,“对!就是这东西!我找到了!找到了!以前就章回懂八卦,周易、文王、伏羲、孔子……现在我全懂了!八卦也让我破译出来了!哈哈!钱局长,陈亚军,就是你们坏了我的事!……你们你们……”
朱良疯狂地叫起来,声音凄惨。过了一会儿,他筋疲力尽,眼睛翻成了死鱼眼,张大嘴巴只是喘气。
我惊呆了!
“你病了?”
“我病了吗?”
“你病了,你的眼睛太红!”
我说着,心里一阵恐惧。惊慌失措地赶忙跑出去差人去找朱良的家人——朱良和我一样,在县城没有亲戚,有的,也只有小爱家了。我也顾不得那么多——房里,朱良一个人仍在嚷着,语言清晰,逻辑混乱,锐利的喊叫声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耳膜,我的心一点儿一点儿地沉向了无底深渊……
十
天色向晚,夕阳在热浪中扯得丝丝糊糊,晚霞映照得小木楼格外凄凉。大家闻讯过来,把朱良弄进了他自己的房间。围着他,变着法子哄他休息。可朱良毫无感觉,拿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在手指上拭了拭,那闪耀着寒光的刀刃上,立即就有一滴殷红的鲜血流下来。朱良对着那血直发愣。“朱良,不值得!”小爱惊叫了一声。
很快,小爱的大大一步冲上前,把朱良紧紧摁住,嚷道:
“家里出了你这么个孽种,算是完了,要人样没人样,要鬼样没有鬼样,整个儿一个杀猪的!我女儿跟你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他夺下了朱良手上的刀。
“我不信钱局长能翻云覆雨,一手遮天!”
朱良嘴里不干不净,睁大眼睛,傻子一样地望着小爱的大大。没有水果刀玩儿,他就双手交叉,搓着自己一双大大的手掌。我心里一酸。我内心清楚,朱良现在沉浸在一种什么样的幻想里。只有我知道,朱良的脑子肯定在一遍又一遍地想象,想象怎样扇出去一巴掌,应付那一巴掌带给他的奇耻大辱!朱良打量着自己的手掌,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手掌能发出“啪”的声响,并能迅速地落到一个人的脸上。他扬起了手掌,朝桌上的一块美丽的玻璃板就砸了下去,光亮的玻璃板立即绽开了一朵残菊般的图案……他很高兴,嘴里咕哝了句什么。
我的耳膜似乎也随着那玻璃碎裂,面前一片朦胧,只觉得热泪夺眶而出。一个趔趄,我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四仰八叉地躺到了床上。
“朱良疯了!”我终于冷静地想清了这个事实,心里一紧,一种强烈的内疚和负罪感紧紧地包裹住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