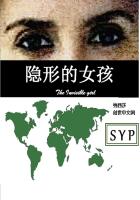第二十章针尖与麦芒
我和小欧是在门前剥大蒜时看见她的,那是五月里一个不太晴朗的早晨,房顶上的晨雾尚未散去,整条街道已经淹没在一片喧嚣之中。
坐地贩子与农夫的讨价还价,完成采购又发现称斤不对的外处小贩的谩骂,买到便宜货却有一大半东西不翼而飞的家伙的仰天顿足的诅咒,晚到的农夫正一脸鄙下地与街坊商量,希望有个地儿可以出售蔬菜,哪怕有屁股大个地方也行,而他们得到坐街户的回答差不多都是相同的话:去去去!
“看你模样都不像庄稼人,现在都几点了?还想找地方,真是异想天开。这里半夜就开始交易,怕你还在做梦哟!”外婆面无表情地和一位年轻姑娘说着。
她把一架板车横在我家门前,想让外婆给找个位置好出售她拉来的几大筐卷心菜,我们家门前一半地方出租给了一个贩蔬菜的老头儿,另一半由外婆安排,同样摆满了密实的各种蔬菜,想要去街上就只有使劲一跳,才能越过这道屏障。
她一定费了些周折才抵达这里,因为我们看到她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湿透,她用衣袖擦拭额头,留下一脸污迹。
这张左顾右盼,无可奈何的脸转向我们时,使我立刻有点心跳。不因她有一张令人心动的面孔,也不因她一副年轻的、曲线分明的身子,只是我曾见过她,还吃过她做的饭。一位城郊菜农的女儿,是的,她是印第安人的妹妹!
对面刘明亮家门前似乎有些松动,我起身走过去,和刘妈妈简短地交涉一番,再来了几个跳跃,才绕过街道中间的人群返回。
此刻她还在东张西望地寻觅位置,脸上不时出现焦急的神色。
“你把板车上的绳子解开,我们再把你车上的卷心菜抬去对面,那里好像有空位,你可以在那里卖菜!”我大声地向她说。
她似乎不相信我是在和她说话,环顾四周后十分惊讶地看着我,因为在她周围,尽管挤满农夫们肩挑车载的各种蔬菜,却没有任何买卷心菜的人。
“我真的可以去对面买菜吗?”她说着,脸上有了明显的笑容。
我和小欧过去帮忙,但我们抬不动那盛满卷心菜的篾筐。于是又花了些时间,才把板车挪去刘明亮的家门前。
“我说你吃在碗里还望着锅里,身边已经有了女友还向另一个女孩献殷勤,你想死啊?”刘明亮悄悄对我说。
“只有坏蛋才瞎想,是同学的妹妹,傻瓜!”我说。
“同学的妹妹?你再说一遍!”
“信不信由你,我忙着呢,懒得跟你说!”
“我们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小学。再一起进初中,你说说哪个同学是我不认识的?”这家伙简直不依不饶。
看着他失去双腿再也不能行走的样子,我不愿意揭开他尚未愈合的伤口,更不想告诉他这是印第安人的妹妹,只有坚持自己的说法,虽然把他弄死他也不相信。
“我再说一遍,你给我听清楚。这女孩只是同学的妹妹,今天碰巧遇上而已。你说的对,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小欧,除了她我现在不想任何女孩!”我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从以往的表现来看,你倒不像是一个说谎的家伙。既然如此,我可是要下手了哈,到时候你别后悔!我看这女孩确实不错,比你那个还要漂亮丰满!”
“请便!”我说,“只要人家姑娘愿意,我更愿意成全!”
刘明亮家门前的空地儿刚好可以挤进去一只菜筐,余下的两只放在他家的街沿上。
她把板车送去寄存处很快返回,十分感激又一头雾水地盯着我,我也知道,这个时段在这条如此喧嚣、如此拥挤的街道要找到一个可以摆摊的空地儿简直如同登天。
“真是太好了!”她说,“不知道怎样谢你,还让你们帮忙抬筐子,我很是难为情!”
“其实你不用感谢,我们曾经见过,我想你一定忘了。上次去你家,和你哥哥一起吃你做的饭,当时你只愿意倒一杯酒给我们,你哥哥再怎样恳求也是徒劳,我说的有错吗?”
“啊!是你呀!”她差点没叫起来,“虽然已经过了很久,我还是能回忆起,不过,真是对不起,我不记得你的模样了。若是你不说起,我还真是忘了!”
“我也只是记得迷迷糊糊,你哥哥说你们是城郊的菜农,而且你身上的白底黑圆点衫正是那天你在家里穿的,由此我推断大概是你。”
“你很聪明,你的推断非常正确,再一次谢谢你!”
她说她的衣服并不多,很少添新的衣服。哥哥虽然十分疼爱她,但她从来不要他买的任何东西,尽管看上去哥哥很有钱,她却只听爷爷的话。哥哥从来不下地干活,爷爷说哥哥的钱来路不明,千万不能要。她跟着老人学种菜,成熟后就拿去市场出售,爷爷说以他一辈子的经验来说,靠自己汗水所得用起来才踏实。
小欧觉得印第安人的妹妹是个好姑娘,一个人只能消费自己的能力所得,超出范围的话麻烦一定随时光顾。
安顿好印第安人的妹妹,我们回到对面的家门前,继续照看外婆的蔬菜摊子。
还未到午饭时间,听到对面传来一阵闹哄哄的声音。我站起身来,看见刘明亮家门前聚起一大堆像在看闹热的人。此刻,失去双腿的刘明亮尽管无法起身,两只手却在空中不停地乱舞,不知道他和什么人吵起来了,因为他发出的声音比任何人都要响亮。
事情再简单不过,两位穿军装的人来这里采购蔬菜,他们似乎看上了印第安人妹妹的卷心菜,其中一位说,可能的话他愿意将姑娘和卷心菜一并买回。不知他们是开玩笑或是有意的,刘明亮觉得这家伙简直是口出狂言,狗胆包天,大白天也敢在他家门前撒野,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岂知对方同样不想示弱,张狂之态完全盖过了这家经营蔬菜的坐地户。
我注意到他们没有戴军帽,军装上也没有领章。但衣服很新,不像退伍军人那种褪色的军服,倒像是新兵的装束。不过看年龄又不太对劲,两人中的一个看上去少说也在四十岁上下,另一个瞧背影比我大不了几岁。虽然如此,单凭他们身上的绿色军装便足以让人羡慕不已。因为这个时代(八十年代初期)对于一般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想出风头的年轻人来说,拥有一件别人穿过的、哪怕是褪色的旧军装都会令我们兴奋得长时间睡不着觉,何况眼前两个家伙还是一身崭新的军服。
年长的家伙一直和刘明亮斗嘴,口气颇含长辈对晚辈的训示。而此刻的刘明亮完全像一头发怒的野兽,若非他失去双腿、只能坐在靠背椅上的缘故,我想,他极有可能冲上去撕咬对方。若是有人说他可以立刻变成狮子的话,他肯定会不假思索地答应。
“你们没有羞耻吗?没见过与一个残疾人也能动怒!”刘明亮的妈妈吼那两人。
一直埋头的那位更年轻的绿色军装这时候忽然抬头,整个过程好像他没有说一句话,却在这时冷不丁地抓起一颗卷心菜,用力朝刘明亮的头上砸去。
残疾人躲过飞来的卷心菜,随手拾起身旁的一只带盖的茶杯向对方扔去。
刘明亮的妈妈和姐姐立马冲上去挡住那家伙,两张嘴里发出的声音也由谩骂变为怒吼。她们家的残疾人这时候看样子已经在靠背椅上坐不住了,他张牙舞爪地挥舞拳头,身子不停地蠕动,身边凡是够得着的东西都被他拾起来,飞快地扔向两位穿军装的人,靠背椅发出嘎吱嘎吱的快要散架一样的声响。
“呵呵,简直没完没了了!”年轻的那位怒气冲冲地吼道,“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看你像一条没有腿脚的杂毛狗,向我们下跪就算了。但是,你若今天不乖乖向我们道歉的话,我不敢保证你们一家今后会有太平的日子,你信不信?白痴!”
“要我相信其实不难,”刘明亮好像平静了些,“只要你承认你是我的种就行,你看起来脾气不小,简直太像我了,儿子!”
这位年轻人很快从一直坐着的三轮车上跳下来,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刘明亮家的菜摊前,在一只盛满土豆的筐子抓起来就朝刘明亮的头上一个个砸去,残疾人的姐姐上前与其厮打,被对手一脚踹倒在地。
见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忍不住开始怒吼,我回头看了看,发现一位农夫挑着的空菜筐里有一根手腕粗的不到一米长的木棒,顺手拿起它,却让小欧死死拖住,使我无法泄愤。
“我说你脑子没病吧!”她有些怒气地在我耳边吼道,“若是碰上这种情况你总是以这种方式解决,我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如果斗殴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国家的司法机构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尽管我听不进小欧的话,但愤怒的心却被她紧紧拥抱所软化,她在我耳边那句“我永远也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使我逐渐静下心来。我想,若是这个时候换了别人,什么样的劝告也是徒劳的。这件事尚若发生在以前,这当儿肯定可以看到鲜血了!
小欧认为今天这件事可以说因我而起,我们当然要解决,但绝不以暴力的方式。但是,她并不知道,我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斗殴。
这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那个张狂无度者的尊容,此时此刻他正面朝我,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我们县城里那个拥有不少特权的家庭中的一员!曾经在我工作的山上,植树节那天带一伙人袭击学生还桀骜不驯的人,有一张差不多令所有女孩为之动容的俊美面孔的家伙,他就是的老红军的儿子―—被印第安人称为“小白脸”的年轻人。
为了不让我再次激动,小欧一直挡住我的身体。看得出她虽然不允许我动手,还是愿意前去声援残疾人一家。
“不知道这家人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惹得你们如此动怒。既然你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一个残疾人下狠手,又把他的姐姐踢倒在地,说明你们肯定拥有至高无上的决人生死的权力,那你们两个为何不干脆来痛快些,让他们一家三口立刻从世间消失呢?”走到人群中间的小欧开始质问穿军装的两个家伙,她没有一点儿怒气,语气平和而淡定,似乎不容对方沉默。
“呵!看不出还有人冒杂音呢!”小白脸斜眼瞧了一下小欧,声音同样平静,“还有抱不平的,而且还是女人,真******没劲,这么说这街上的男人都他妈是缩头乌龟哟!”
“我认为就算与畜生交流也比你要好得多,至少它们有时候还懂得温顺!”小欧继续说道。
“说得好,把我们当畜生!请问,既然是畜生,那就是说你可以随便让我们骑哟!”小白脸边说边朝小欧走来。
“简直是一对衣冠禽兽!”小欧脸色严肃起来。
我觉得尚若此刻还需忍耐的话,便不能呼吸。在我努力寻找刚才那根木棍的时候,看见另外两位年轻人满面怒气地窜到小白脸的身后,一个是拉车匠家的王刚,还有一个是洗衣妇的儿子小林。尽管两人都把双手背在身后,我却清楚地看到他们握在手里的黑色砖头。
“小白脸”还没有走到小欧面前就一头向后倒地,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两块砖头几乎同时击中“小白脸,”一只在他的后背,一只在他的右耳,他背上挨的那一砖头发出“嗵!”地一声,另一只砖头倒是声音不大,却让他的右耳朵损伤严重,像是破了,顷刻间血流如注。
我们不太理解的是,印第安人妹妹此刻的表现让人费解。在“小白脸”倒地的同时,她像疯子一样开始狂叫:“杀人了,杀人了!报警,快点报警!”
派出所长一行人很晚才过来,他们不管人们如何解释,也不管多数人的阻挠,强行带走了两位以砖头为作案工具的行凶者。
令人难以接受的消息不久传到我们这条小街上,由于小林和王刚未满十八岁,虽然罪行被定为蓄意谋杀,他们也只能予以轻判,送去距我们县城八十公里外的一个劳教农场开始为期两年的改造生涯,使之洗心革面,以便将来重新做人。
愤怒冲昏了两个家庭里所有人的头脑,他们天天跑去法院狂叫嚣没有天理。司法机关的解释委婉又柔和,且句句在理:在自身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的情况下,以暴力袭人便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
我们还能怎么样呢?在这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令人肃然起敬的礼仪之邦,天理似乎总在天上游荡,它何时降临人间大概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