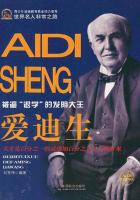这些写于1924年的文字,绝非是针对那次暴动事件的权宜之词。它们反映出这对曾经的师生之间所达成的一种默契。休谟教授间接地表明,阿道夫·希特勒当时暴动的目的源于他在学校的理想。然而对于教德文的休谟教授来讲,希特勒并不是个好学生,从他寄给我的信件和明信片上的语法错误便能证明这一点。
另一个受到了希特勒积极评价的老师是接替了颜士拿的自然史老师西奥多·基辛格教授。阿道夫之所以尊敬他,并不是因为他学识渊博,而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跟阿道夫不谋而合。基辛格非常喜欢户外运动,是一个耐劳的步行和登山爱好者。他是所有信仰民族主义的教师中最狂热的一个。在那个时期,政治分歧在教师群体中也明显存在,跟普通群众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紧张的政治氛围对青年希特勒的智力发展而言,要比他在学校接受的教育重要得多。通常情况下,一所学校的价值体现并不取决于它开设的学科,而是它自身的氛围。
顺便提一下,基辛格教授后来也给他以前的学生希特勒做了评价。这份引人注目的证明材料上写道:
“就我个人而言,希特勒在林茨的时候,既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在班上他绝对不是什么领导者。他身形修长且挺直,他的面容苍白而消瘦,就像是肺结核病人,他的眼睛明亮,目光炯炯有神。”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到了希特勒积极评价的老师,是教他历史的利奥波德·波希博士。他是诸多老师当中,唯一一个在当时就已经深受希特勒仰慕的人。希特勒一般不愿与我谈及他以前的老师,然而波希是个例外。
希特勒最尊敬的老师,利奥波德·波希教授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这个人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
“也许我命中注定,要碰上这样一位历史老师,他深明教学与考试当中最重要,但又很少人懂得的一个原则,即去芜存精。在我的历史老师,林茨实科中学的利奥波德·波希博士先生身上,这一必要条件得到了理想化的满足。他是一位和蔼而又严肃的老绅士,他不仅能用出众的口才捕获我们的注意力,同时还能点燃我们的热情。时至今日,当我回想起这个头发灰白的男人,我都感动不已,他那激情洋溢的言语有时会让我们忘掉现在,并如同魔法一样,将我们带回过去,他能撩开时间的迷雾,把枯燥的史实转变成鲜活的现实。我们坐在教室,个个满怀激情,有时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
利奥波德·波希是唯一一个在《我的奋斗》中被提及姓名的人,希特勒用了两页半的字数来对其进行描写。然而这样的描述无疑显得有些夸大。有事实为证:根据希特勒在林茨最后一张成绩单上的显示,他的历史只得了个“中等”,也许此事跟转校有关。但无论如何,波希博士给这个极其敏感的男生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觑。如果说学习历史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唤起人们对它的热情,那么波希教授无疑是个称职的老师。
波希是奥地利南部边区的人,来到林茨之前,他曾在马里博尔还有其他一些毗邻德语区的地方任教。因此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他可谓阅历颇深。我相信,波希对德语区人民的绝对热爱以及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治的反感,让年轻的希特勒深受启发。这种炽热的精神为他的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道夫·希特勒终其一生都对那位昔日的历史老师心存感激,的确,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学校和老师的怀念之情也在不断增添。1938年,希特勒造访克拉根福期间会见了阔别已久的波希。他花了不止1个小时与这位虚弱的老人在房间里独处,临行之时,他对随行人员讲道:“你们无法想象那位老人给我的恩惠有多么巨大。”
要想知道希特勒对他老师们后来的评价到底可不可靠,还得从他以前的同学所持的相反观点中去求证。真实的情况是——正如我亲眼所见——阿道夫带着一种固有的憎恨离开了学校。尽管我总是小心谨慎,不把话题往这上面引,但有时候他又控制不住要对其进行猛烈抨击。他从未与任何一个老师保持联系,就连波希也没有。相反,当阿道夫在街上碰到教过他的老师的时候,他就故意回避,装作没认出来。
另一场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斗争,正在与他和老师之间不断爆发的小规模冲突同时进行:跟她母亲的精神较量。不要误会了我的表达。事实上,如我亲眼所见,阿道夫竭尽所能的想要消除他母亲的忧虑,因为母亲是他生命的全部。但当他在学校的失败已成定局,并且偏离了他父亲为他设计的人生轨道之时,这种努力的尝试就变为了一种徒劳。他解释不清他为何要选择另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阿道夫内心的矛盾远胜于他跟老师们永无止境的游击战。我并不知道他对自己的糟糕成绩如何看待,但对他母亲而言,这就意味着阿道夫不会被大学录取。他选择的“另一条路”是个什么样子,连他自己都不能确定,即便在他母亲去世多年以后,他也仍然无法讲清。就这样,她把自己对儿子未来的担忧一起带进了坟墓。
1905年的深秋,阿道夫已处在了危险的边缘。从表面上看,这个16岁的男生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是在施泰尔实科中学复读四年级,还是永远的离开学校。但此番决定,意义重大:到底是应该为了母亲,继续踏上那条他认为是错误并且毫无希望的道路,还是应该不顾母亲的担忧,毅然选择“另一条道路”,一条他只能说是朝向艺术(可想而知,这样的字眼怎能让他母亲感到宽慰)的道路?
但鉴于阿道夫的本性,这并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决定,因为现实中根本没有出现让他左右为难的状况。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上第二条路,离开学校。他深知这样的决定会对他母亲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痛苦。
在1905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阿道夫挺过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危机,而这次经历也成了我们友谊中最沉重的一段时光。危机的表现是阿道夫患上了重病。在《我的奋斗》中,他将其描述为呼吸道疾病。但他的妹妹保拉,却提到过他的一次咳血症状。又有人断言,这是由某种心理暗示引发的胃病。在他患病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因为我得照常向他汇报斯蒂芬妮的消息——斯蒂芬妮是阿道夫当时很倾慕的一个姑娘。根据我的回忆,他的病症实际上是肺部感染。我记得很清楚,自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在遭受肺炎和剧烈咳嗽的折磨,尤其是在潮湿多雾的日子里。
同时,由于害了这场大病,他母亲也不再耳提面命地敦促他继续上学。如此一来,正好符合了他的决定。然而,这种疾病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自我暗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身内部病变引起的必然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纯粹的先天遗传?我不得而知。
从阿道夫走下病床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打定了主意。校园生活已经成为他的过去,现在他要扬起风帆,毫无顾忌地朝着他的艺术家生涯驶去。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没有任何明确的人生目标。当他在《我的奋斗》中描述这段空白时期的时候,感到有点别扭,于是他将其命名为“闲暇生活的空虚”。从表面上看,这种概括是恰当的。他既不用上学,也不需为任何实习而操心,他就待在家里享受母亲的照顾。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成游手好闲的懒汉,相反,他把人生的这一章节安排得相当充实。他画画,写诗,阅读书籍。总之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没遇到过无事可做的情形。如果我们在看戏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厌倦,他就会立马转身离开,然后重新振作,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当中。不可否认,他的生活因缺少清晰的目标而显得杂乱无序。他仅仅是将各种感受,经历和素材在他身上堆积起来。至于这么做的目的何在,我完全无解,反正他总是在不断地四处寻觅。
与此同时,阿道夫用实际行动向他母亲证明了一件事情:学校的教育在他身上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对母亲解释道:“一个人通过自学能够获得更多知识。”于是,他开始在俾斯麦大街的成人教育图书馆订阅书刊,随后又加入了博物馆协会,以便从中借阅书籍。同时他也经常光顾斯托约尔的租书馆和L.汉斯林格图书公司。我记得从那时起,阿道夫就总是扎在书堆里,其中,《德国英雄传说》尤其令他爱不释手。每当我干完活儿以后,他总是会要求我把他看过的书学习一遍,以便能同他一起讨论。现在,忽然之间他就具备了那些在学校所欠缺的品质——勤奋,有兴趣,享受学习。正如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我用学校自己的武器战胜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