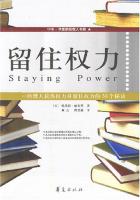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薄弱和企业家精神的缺乏是一个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现实问题。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已经日益彰显。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渐渐浮出水面,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显著加大。而随之而来的则是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能源、原材料进口依存度加大仍供给不足,特别是民族品牌的地位日趋下降,这一切又对我国开拓经济发展空间增加了难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来自国际强势主流文化的一种压力。而这种强势主流文化,往往是由人家的优秀企业家及其精神所承载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首先呼唤的是,我们民族的企业家呢?我们民族不死的精神在哪里?因此,时代再一次把中国企业家推上历史舞台。紧接着的是,作为和平发展的主角———企业家应该以怎样的精神面貌和素质内涵去面对这一挑战?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民族精神如何得以进一步弘扬?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如何得以建构和确立?这些问题已经严肃地,且充满挑战地摆在了国人的面前。
前些年当全球化大潮迎面扑来的时候,当我们在求解中国民族工业何处去的问题时,还出现过要不要民族工业的争论。人们还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孕育出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精神心存疑虑。当时,呐喊振兴民族工业被当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呼唤振兴传统文化,则被当成了守旧和不合潮流的代名词。时至今日,当中国成了世界工业原料消耗的第一大国时,人们却突然发现,我们国家离富强还有遥远的路程;当人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无奈地被国外强势的主流文化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似乎幡然醒悟,民族工业不可或缺。由当代企业家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实乃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凝聚民族精神、为民族工业长足发展提供动力的,则无可置疑地是民族的传统文化。本文认为:在经济产业领域,民族精神应集中地体现在优秀的企业家精神里。因此,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应该融入民族文化的基因,我们应当正视中国企业家队伍弱小和企业家精神匮乏的现实,并把这一现实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看待,放在社会结构的大变迁和社会精神转型的新视角下来观照。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今天的社会应当把塑造企业家精神作为社会精神转型的首要任务之一;作为文化转型的明确目标,应当让企业家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化。应全力锻造企业家队伍,形成对民族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有利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用饱含着民族精神因子的企业家精神来点燃驱动中国经济战车的引擎。笔者在本章中将着重论述以下三个观点。
一、企业家及其精神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今天的世界,每一个成功企业的故事后面,都蕴含着厚重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每一个知名品牌的前面,都行走着一个或几个引领它的卓越企业家。所以说,今天缺少具有经营智慧和管理才能的企业家,远比缺乏物质资源或资本更为严重。国与国之间现代经济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在企业家的质与量的差距,这已是被实践所反复证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其惨痛的教训就在于:只把眼睛盯在客体的生产要素上,而忽视了对作为经济主体之核心的企业家的重视。历史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因而有学者这样认为,一个工业国家企业组织完善与否,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关键要看它有没有一个成熟的企业家群。
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叫埃兹拉·沃格尔的美国人备受瞩目。那是因为他写了两本轰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书《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和《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再论日本名列第一》。作者在书中疾呼,日本已经名列第一,如果美国不迎头赶上,这个二战 [1]中的战败国或许会凌驾于美国之上。在分析日本大量成功企业的案例时,他特别剖析了山崎定吉和他唯一的徒弟在1919年共同创立的制造铁锅的山崎铁工所。经过短短的60年时间,这期间还经历了战败,然而就这么一个靠干铁锅起家的企业,到20 世纪80 年代,已成了世界瞩目的生产先进数控机床的跨国公司。埃兹拉·沃格尔不得不感叹道:“山崎铁工所的发展历史表明,在日本仍然存在着自强不息的企业家精神。”应该说,埃兹拉·沃格尔仍是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人,他的书中不无对美国政府应加强对经济干预的进言,然而这由衷的一叹却歪打正着,成了里根政府决心实行“供应学派革命”的有力注脚。供应学派的祖师爷萨伊120 年前提出的“萨伊定律”认为,“当一个产品一经产出之际,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限度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是生产开辟了对产品的需求’。这就是说,供给自创需求,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相等。”“萨伊定律”这次走红的原因则在于,主张以政府主导的、实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失灵了,经济活力的引擎正在由确定财富的企业家来推动,由企业的供给来引导。很显然,当“萨伊定律”比凯恩斯主义要灵验时,企业家一定走上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当企业家的创造性决定着万花筒般的世界经济发展时,企业家精神就必然是转动变幻万千之万花筒的永恒发展之力。
实际上,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一定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的反映;一个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一定孕育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而以重要人力资本形式出现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之间,同样也具有着如此相辅相成的关系。特别是社会精神作为上层建筑,在社会时代大变革的转型过程中,其能动作用就会尤为显著和重要。因此,企业家及其精神是今天推动整个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因素之一。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是中国当代社会精神转型的重要任务
纵观世界历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民族精神更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独特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民族精神总是体现在时代特性之中。当世界进入了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民族精神就必须由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企业家精神来承载和表现,舍此,传承民族精神就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会文化就有可能变成舶来文化占统治地位,这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精神转型的失落。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转型,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今天,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都没有缺过这重要的一课。
历史上,欧洲的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就是社会精神转型的成功案例。欧洲的现代文明是从古希腊文明中演变过来的。在欧洲的封建庄园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转型过程中,由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动的社会精神转型起着决定性的推波助澜作用。从人格化的层面来看,欧洲社会从骑士贵族精神实现了向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精神转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它成功地实现了从神权和皇权统治下的封建意识向自由平等的现代商业精神的转型。正因为有了这场社会精神的转型,欧洲较早地实现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德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有力地论证了这一观点。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欧洲的社会精神的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明确目标的,它的文明基质并没有断裂,而是很好地被传承下来,并做了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和变革。因此,若论当今西方世界主流社会精神的特质,可归结为企业家精神。
再举日本为例,就像当年欧洲的骑士从固有的社会阶层中裂变出来转化成为企业家一样,在近代日本,武士阶层也大量地从旧有的社会阶层中裂变出来,转变成了企业家。在欧洲,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广为人们敬畏和尊崇的骑士道精神,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工商业中成功地转化成为经济的骑士道,构建了西方今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同样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广为人们敬畏和尊崇的武士道精神转化成为经济的武士道,从而构建了今天带有大和文化特质的日本现代企业家精神。欧洲没有打倒骑士道,而把它转化成为企业家精神;日本也没有打倒武士道,而把它转化成为企业家精神。尽管这是两种不同气质的企业家精神,但同样都保留了各自民族文化的特质,同样实现了时代的社会精神转型,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当今日本,若论其主流社会精神的特质,亦可归结为企业家精神。
可见昔日欧洲和日本的成功,都有着共同的社会精神转型经历,而这种经历的结晶是不约而同地构建了新时代的主流文化———企业家精神。
日本在文化策略上的“挑”的精神和智慧堪称一流。它从中国儒家找到了“义、礼、智、信”,但放弃了“仁”;从中国佛家找到了禁欲,却放弃了慈悲;从西方文化中找到了科技,却保住了大和魂。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日本精神和西方技术》一书中曾指出日本的三种类型宗教对其精神塑造的作用,其中讲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的特殊气质,都跟它“挑”的智慧有关系。所谓的“挑”就是寻找时代需要的文化因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日本是如此,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古希腊文明和传统天主教中先进的因子注入当时的社会,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精神,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日本那种对原始文化“挑”的精神和智慧,给当代中国很多的启示。
世界上没有现成的发展道路可以复制,但有共同的发展规律可以遵循。中国的社会转型及时代精神的重塑,也必然要遵循以我为主的原则,走“以借鉴外来文化为契机,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的道路。从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看,中国经济上的明显落伍只是近现代的这一段。以儒、释、道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曾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灿烂的封建文明,到隋唐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峰。以禅宗为代表的隋唐佛学是儒、释、道的大合流,这一精神成果成为当时社会成功地实现精神转型的显著标志。那时,从人格化的层面来看,士大夫精神成为封建社会人们广为尊崇和敬畏的人格标志。宋明理学则把以隋唐佛学为代表的儒、释、道精神体系化、精致化。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生动活泼的封建文化慢慢地走向了僵化。以后,在社会历史转型中,在要不要社会精神的转型和怎样实现社会精神转型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层和官僚层并不像欧洲和日本那样清醒。
到明末清初,欧洲成功地进行了由封建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转型,中国不但没有抓住机遇,清中后期反而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在社会精神转型方面泥古不化、抱残守缺。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强势文化,“无为”并没有成为上上之策。鸦片战争以后,被西方列强打晕了的中国,在社会精神转型和社会文化转型的策略上,要么选择了全盘西化,要么冥顽不化。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中国的社会精神文化转型出现了新旧两种思想僵持不下的局面。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终于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请上了中国历史舞台,长期来被封建统治者扭曲了的孔孟之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中国又一次陷入了历史的误区,“五四”运动也没有最终完成社会文化和精神转型的任务。实际上,文化不可以割断,“孔家店”不应打倒,但对其进行合理取舍和“装修”则是必不可少的。必须促成士大夫精神向现代企业家精神转型。只有依靠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因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社会文化和精神转型,才能依此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无异于自毁基础,只会走进虚无的死胡同;而清末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成功也实属必然。不是发掘并凝炼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因子,而是糟粕与精华照单全收作为“体”,对自由平等的现代商业精神视而不见,却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割离出来定义为“西学”,焉能“为用”?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今天,中国应该有更为清晰的社会精神转型目标了———中国必须实现士大夫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实现封建小农意识向现代商业精神的转型,中国必须有培育和呵护企业家队伍成长壮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这才是今天我们彻底实现社会精神转型的首要任务。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丰富源泉
欧洲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早期,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扮演了企业家“助产婆”的角色,企业家以及企业家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体系所需要的主要条件,都是通过集中的、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之手实现的。因此,相对来说,现代工商业产生、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比中国更加及时和充分。而中国的文化特质和家庭组织、社会结构,在实现社会文化精神转型之前,较西方不利于企业家的产生,这也是事实。正是由于此,同样一个马克斯·韦伯,在为西方从传统的骑士贵族精神向企业家精神转型成功而欢呼时,却对中国给出另一个结论,他于一百年前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判定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不能走向现代商业精神,根源于儒家伦理和道家价值系统,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缺乏发展现代商业精神所需要具备的“独特的精神气质”。
尽管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生成,有着制度和文化支持上的劣势,但是从历史上看,既有经商有方、万贯家财的陶朱公,还有亦官亦商、“最为饶益”的“红顶”商人子贡;从近代看,则有晋商和徽商的辉煌,也有海外华商的成功;从现代看,在东亚文化圈有“论语加算盘”(日本) 的成功,在东南亚有儒家资本主义 (新加坡)的先例。这些骄人的商业成就无一例外地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乏生动的现代商业精神的文化因子,不乏士大夫精神向现代企业家精神转化的因素,这是勿庸置疑的。如果说马克斯·韦伯由于历史条件和视野的局限,从而做出中国不能生成现代企业家精神的论断情有可原,那么到今天,如果还死抱中国文化不能匹配现代商业文明的论断,就只能被认为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或是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迷惑所致。
其实,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国及其他亚洲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生成机理时,曾非常谦虚地声明:“我不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尽所能靠近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笔者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时他能到手的资料少得可怜,“用于研究中国的资料更是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更应该谦逊地估量自己著作的价值了。上述这些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无疑具有一种暂时的性质,那些论述亚洲的部分尤其如此。”他认为要得出正确结论,必须依靠汉学家、印度学家和埃及学家,“只有专家有资格做出最后评判”。遗憾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这些重要声明,居然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戴有色眼镜的人对此更是熟视无睹。
可是随着当代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等国家地区发生了经济奇迹,西方一些严肃的学者开始醒悟过来。例如,米切尔·莫里西就认为,“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儒家价值观念决定了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中集体主义伦理道德体系的确定。儒家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道德,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秩序关系的形成。”“西方社会中,道德上的个人主义与经济个人主义无意识地结合在一起,而日本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则会导致儒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由此可见,连西方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足以成功地造就具有东方文化特质的、完全可以和西方相媲美的企业家精神!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闪烁着无穷无尽的现代商业精神的因子,其弘扬和复兴之日,即是实现时代精神伟大转型之时。而时代精神伟大转型之日,即是中国经济战车迅猛向前之时。
注 释
[1].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