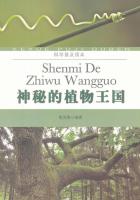1956年初, 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航空工业局在全力仿制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的同时, 决定向上级报告要开展自行设计飞机, 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策。1956 年9 月四局决定成立飞机设计室、发动机设计室和仪表设计室, 前两个设计室分别放在112厂和410厂代管, 业务上由四局直接领导。当时中苏关系很好, 整个航空工业得到苏联的大量援助, 不仅向有关的工厂、学校, 而且对新成立的材料研究所、工艺研究所和试飞研究所都提供资料, 派苏联专家当顾问。但苏联政府不赞成中国自行设计飞机、发动机, 所以采取不援助的政策。这样飞机设计室成立之后, 既无苏联专家也没有任何资料, 真可谓白手起家。飞机设计室由来自四局的徐舜寿、黄志千同志和112厂的叶正大同志分别担任正、副主任, 在四局机关和四个飞机厂 (112厂、122 厂、211 厂、320厂) 抽调骨干技术人员集中到112厂再加上一部分新毕业的大中专学生, 1957年上半年已有108人, 平均年龄22岁, 党员有30多人。
1956年11月, 接到通知, 调我去沈阳飞机设计室。正值四局徐昌裕副局长来哈尔滨检查工作, 他找我去汇报, 我汇报了40 号新机 (ИJl-28 ) 试修和歼5 副油箱试制以及最近接到仿制米-4直升机的通知, 说明书也看到了等等以后, 又顺便谈了要调我去沈阳的事。实际上徐局长早知道了, 他向我介绍了打算设计双座喷气式歼击教练机的方案, 最大速度800 千米/时, 喷气发动机由410厂发动机设计室设计, 推力为1600千克力[1], 分别以歼5飞机和涡喷5发动机为原准机, 这个自行设计起步虽然低一些, 但稳妥可靠。我听了以后, 很是兴奋, 从修理到仿制, 再跨到自行设计, 几年工夫, 连跨三大步, 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呀!
我和党组织商议了接任科长的人选和另外同时调几名设计人员的人选 (陈一坚、陈嵩禄等) 后, 移交了工作, 12 月上旬就和爱人一起打起铺盖卷赴沈阳报到。叶正大副主任让出他的一间住房让我先住了, 徐舜寿主任和我谈话, 让我担任机身设计组长, 我爱人金娥到标准组当设计员。
这时歼教1 (歼击教练机1型) 飞机已经有了初步的总体图和三面图, 设计是程不时、李文龙同志, 组长是陆孝彭同志。
不久, 徐主任偕黄主任一起来家里看我, 他谈到他到122厂要设计干部时发现陆纲厂长很有水平, 听说要自行设计飞机, 十分支持, 所以点名要输送干部, 真是二话不说, 说调就调。说到第一个任务设计歼教1, 徐主任说这飞机空军要, 技术上可参考歼5, 成功的把握大, 同时也是设计队伍成长的一个阶梯。黄主任笑着插话, 这也是一种教练。
我开始工作是先从学习歼5飞机的构造和制造入手的。因为我过去搞的是轰炸机和强击机的修理和部件生产, 对歼击机不熟悉, 对飞机的制造全过程不熟悉,这是不行的。全室了解歼5的人也不多, 室里组织112厂的一些技术人员, 给我们讲课, 不仅讲歼5 的构造, 而且讲工艺、讲冶金、讲材料、讲试验, 大家学习都很认真, 我每课必到。除看图纸外,还到车间去看实物, 还当仁不让地当老师讲课。另外, 我还抓紧复习飞机强度方面的知识。
1957年初, 人员基本配套, 具体设计工作要开始了, 但很多技术细节不清楚, 怎么着手干, 也没有头绪, 徐主任给大家讲: 总体设计有了以后, 要开展打样了, 什么是打样? 书本上这叫技术设计, 是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实际上就是结构和系统的方案设计。打样这个词, 是中国自己取的, 造船工业有个词叫放样, Lofting, 但那是1∶1地把图纸尺寸画到大钢板上, 取名打样与放样有些关系, 但含义可不一样。
当时室内真有设计经验的只有徐主任、黄主任和陆工 (陆孝彭工程师), 其他的, 在学校里学过又有仿制或修理设计经验的,是较好的了, 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是才从学校里出来的。后来才知道, 徐主任原来打算把曾在国外搞过飞机设计后来回国的老同志(老是相对而言, 当时也就40 岁上下吧) 集中起来, 如机身组长原拟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永寿教授来担任的, 起落架组长原拟请曾在122厂当过我的上级的胡昌寿工程师来担任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办法调集。于是徐主任便提出了一个请兼职顾问工程师的办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简称北航) 的张桂联教授, 西北工业大学 (简称西工大) 的黄玉珊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简称南航) 的程宝渠、张阿舟、高永寿教授等, 都被请来短期指导工作。
为了展开设计工作, 首先要有一些基准文件, 如制图规范、文件制度之类, 于是在摸索歼5仿制资料的基础上自己来编, 也参考一些徐主任自己过去工作时保存下来的国内外资料, 记得其中有一份是徐主任亲笔写的飞机方案晒蓝文件。字迹工整, 清秀如女孩写的字。这类事情由320厂调来的胡除生同志牵头, 我也参加了。成问题的是没有强度规范。开始时, 在黄主任的指导下, 强度组长冯钟越同志着手从歼5的强度计算报告及静力试验任务书中的有关数据和飞机情况来反推。后来, 320 厂的安-2 飞机设计专家斯米尔诺夫听说我们缺强度规范, 他很热心, 在回国探亲时带来一本苏联1947年的强度规范, 室里派人去拍了照片拿回来, 虽然年代老些,但用于歼教1够了, 总算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大家开始打样, 的确不知道从何着手, 都缺条件, 都等着, 徐主任于是又跟大家讲, 大家都要动手干起来, 不能光等着给你条件, 因为这期间, 各设计专业之间,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要相互提供情况, 相互协调, 逐次逼近。机身的协调关系最多, 徐主任希望我自己动手打样, 取得实践经验。我按他的意见, 决定自己铺开图纸打机头气密舱前这段结构的样。因为这段结构没有歼5结构资料可参考, 歼教1 是两侧进气的, 机头特设舱、前轮舱等必须自创。这期间, 徐主任常坐到我的图板前, 指导我的打样, 逐渐使我理解了: 制造是从零件开始由下而上最后总装的, 而设计是从总装开始的, 部装、段装到组合件, 由上而下一直到详细设计出零件图。打样即设计总装图, 以结构为主, 把结构、结构的运动和系统安装融合在一起, 并把结构传力系统弄清楚, 估算和确定主要结构材料和尺寸, 供第一轮强度估算, 落实分配结构重量, 然后再反复修改直至定案。我有了初步实践经验以后, 也学徐主任的工作方法, 经常坐到设计员的图板边, 去指导机身部件的打样, 特别是两侧进气的进气口, 下单翼传力那些没有可参考的结构。各系统的协调也是我工作的重点, 因为大家没有经验, 方案经常改变, 机身结构也必须相应改变, 于是经常有争论, 得罪一些人。后来1958 年大鸣大放有人给我贴大字报, 画着我带着设计员, 手执鸡毛掸子用把手那一头打人家, 用鸡毛那一头拂自己的设计员, 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 这种大字报温和多了。
这时设计室已由厂技术楼搬到大白楼后边的一排小平房里, 各设计组挤在一间大的“设计间”里, 按西方的模式, 排着一排排的淡蓝色制图桌。这制图桌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图板可以斜支起来。因为这间屋子很大, 也兼作开全室大会用。
徐主任待人谦和诚恳, 我从未见到他冷淡、愠怒的时候。他带有才子气, 不拘小节, 保留一些西方的习惯, 上班时有时嘴里含个糖, 没有干部的样子, 还常穿件西服上装, 那个年代, 极为罕见了。在飞机设计室五个年头里, 我没听到过领导对下边有什么批评的话, 当然工作上, 大家都很自觉, 人员组成的素质比较高, 党团员比例大, 为了设计自己的飞机, 不少曾是县团级干部的技术人员自愿在这里当设计员。徐主任在全室大会上讲话、布置工作或总结, 说到最后说“谢谢大家”, 开始我很奇怪, 领导讲话何必谢大家, 后来才知道这是西方人的习惯, 类似于苏联人一开始说“请允许我……”。直到20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国内这最后的“谢谢大家”, 才时髦起来。
徐主任还在室里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技术委员会, 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 开委员会讨论, 每周总有一两次, 其目的是集思广益。技术委员会由正副主任 (技术上兼正副主任设计师) 即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同志, 歼教1 主管设计师陆孝彭与总体、气动、强度、机身和机翼五个组长, 即程不时、顾诵芬、冯钟越、屠基达、沈尔康同志共九人组成。
我切身体会到, 参加技术委员会, 是自己成长、了解飞机全局的好机会, 也是培训干部的重要途径。后来我离开机身组出任初教6主管设计师, 也并无太大压力。可惜1957 年下半年大鸣大放时,有位左得出奇的人写大字报扣政治帽子, 说徐主任成立技术委员会是为了对抗党支部委员会云云, 那个帽子似乎就是反党的意思, 徐主任是建国初期入党的老党员, 老一辈的技术干部中是很少的了,也是支部委员, 平时对支部书记是很尊重的, 我看绝无此意, 而且讨论技术问题和支部工作也没有关系。但自此以后, 技术委员会的活动就消沉下去了, 直到1958年不宣而亡。
飞机设计员要“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要唯米格论, 也是徐主任在大会上提出来的。当时歼教1的原准机是歼5, 歼5 是当时我国唯一自己能制造的喷气式飞机, 也是技术水平最高的飞机, 不少结构和系统的具体设计, 把歼5移植过来, 也是很自然的。但有的设计人员, 一讨论问题就谈歼5如何如何, 特别是争论不清时, 就说歼5是这样的, 以便压服别人。有鉴于此, 徐主任提出不要唯米格论, 要设计人员“熟读唐诗三百首”, 即深入收集学习各类型的飞机方案和结构系统, 弄熟了, 就能广开思路推陈出新, 只了解一种飞机, 跟着干是不可取的。当时我们国内已有十几种苏联飞机和其仿制、修理资料, 米格飞机以外, 还有其他五个苏联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拉沃契金设计局、雅克夫列夫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 的图纸, 它们的设计风格各不相同,深入学习后博采众长, 这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徐主任自己在歼教1的方案中, 主张两侧进气、下单翼布局, 认为有利于维护,强迫着陆时更好地保护飞行员等, 即是不唯米格论的体现。
那年头, 大家只想着干工作, 其他很少计较。比如: 我们就住在北陵公园边上, 但一直没有去过, 一直到1958 年雅克夫列夫设计局的马尔道文和安东诺夫设计局的斯米尔诺夫专家来访, 我们才第一次陪同外宾去参观了北陵公园, 也就给我们大家包括三位主任一起留下了一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