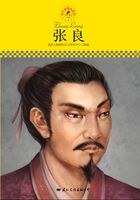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 8·13 上海抗战开始, 以后日寇占领了钱塘江以北的杭州一带,眼看绍兴也危在旦夕。1937 年底,母亲带着我和二哥随着亲戚一起自绍兴坐木船到宁波, 然后坐海轮出海到上海租界。我们坐的是四等舱,就在船舱下层的货舱里, 没有座位抢个空地挤着就地坐下。半夜上的船, 没见到什么大海, 只是听到烦人的轮机声。我靠着母亲睡着了,等到早上船靠上海十六铺码头时,我才醒了。母亲和其他大人实际上一夜都未合眼, 因为提心吊胆地生怕一路上碰上日本兵。
上海租界里一切都是正常的, 远离战争, 当时称为“孤岛”。租界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公共租界, 实际上是英国人在管理, 又叫英租界, 一个是法租界是法国人管理, 除都有驻军外, 还分别雇佣他们的殖民地的印度人和越南人 (当时叫安南人) 当警察。租界四周用铁丝网和日军占领的沦陷区隔开。租界里安全, 但住房很贵, 父亲在天潼路租了一间弄堂房子的“客堂间”, 安了家。1938年初我就在竞立小学插入五年级上学了。
这时听到的战争, 一是四行孤军谢晋元团长率带八百壮士在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里坚守阵地, 一名勇敢的女学生不怕枪林弹雨给他们送去一面国旗; 二是陆续从远房亲戚那里逃进租界的人嘴中听到的战争惨相; 一家在南京的亲戚幸好早已逃离, 但住房全被烧了; 一家在无锡的亲戚, 有两个大姑娘被日军抓住送给当官的强奸, 其中一人试图从内河轮船上逃跑, 淹死了; 三是从报章杂志上看到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照片, 提着军刀拎着人头哈哈大笑的……1939年夏, 我小学毕业后, 就考入育德中学。学校离家比较远, 当时大哥听说那是政府秘密在租界新办的三所中学之一, 教育比较正统些, 就让我去了。上下学都要走半个多小时, 所以中饭不能回家吃, 只能在学校附近买碗面条吃, 还要利用路上走的时间,背课文。
1939年, 我们家迎来了我的小妹妹, 她降生了, 比我整整小了12岁, 都属兔, 成为我们家里的老四, 而且是女孩, 大家都很高兴。父亲为她起乳名叫惠生, 纪念父亲在惠中旅舍工作10 年多了, 惠字也带有一些女性味。我们兄弟三个都有乳名, 大哥叫庚生, 二哥叫癸生, 我叫幸生, 大概1927 年我出生前父亲从绍兴到了上海这大城市感到了幸福吧, 平时习惯都叫我阿幸。很可惜惠生几个月即得病亡故了, 有病当然找医生, 那是一家私人西医诊所,打针吃药, 治不好, 父母也就认命。现在我分析, 小妹妹得的是脑膜炎, 头颈强直, 那时家里没有常识, 医生的水平也低, 如果经济条件好, 送大医院, 也许她不至于夭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口小棺材和母亲的抽泣。
1941年底, 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则是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了, 英、法驻军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我去学校上课, 正像过去学过的法国人写的《最后一课》那样, 老师含着泪给我们上最后一课, 以后, 不少老师和一些高中同学, 纷纷秘密离开学校到内地去了, 学校也由育德中学改名为博文中学,其中细节, 我也没有弄清楚。
我们家也起了大变化。大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遭到了破坏, 日军把经常来我家的姓姜的支部书记抓走了 (后来在狱中牺牲了), 大哥是支委, 当天即撤离上海, 秘密转移去苏南。后来才知道中共商务印书馆地下党支部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人运动战斗团体, 1927年前后大革命时期支部书记是陈云同志。大哥逃走后, 留下不少进步书籍和他主编出版过的刊物资料, 由父亲和二哥整理后送到父亲单位的暖气锅炉里烧掉。二哥的学校上海苏州工业学校也停课了, 让毕业班提前毕业, 父母让17 岁的二哥非常仓促地随一个亲戚逃离已经沦陷的上海租界, 去了浙西内地暂时工作, 免遭迫害。由于大哥的事, 父母在家日夜提心吊胆, 晚上听到楼梯响, 都会惊醒。幸好这位老姜宁死不屈, 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 但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
我们中学开始有了日文课。虽然没谈政治, 老师还是位年轻的女教师, 但是同学们总是有当亡国奴的感觉, 很反感, 只是对付着学。苏州河桥头等要害地方, 都有矮个子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岗, 还有沙袋和铁丝网, 走过那里都觉得阴风惨惨。
生活每况愈下了。一方面市面经济萎缩, 物价飞涨, 父亲在旅馆做小职员的工薪相对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在日寇统治下控制越来越紧, 如粮食按户口配给, 叫户口米, 质量不好不说, 还常常缺货, 一来了米, 就要排长长的队去买, 而且硬性搭配上海人不喜欢吃的面粉, 老百姓叫苦连天, 后来电也限制用, 每户每月几度, 我常常只能在小油灯下做功课。每学期学校要交学费, 父亲负担不起, 就让我到社会上打听申请助学金来交, 记得常去申请的有《申报》助学金、绍兴同乡会助学金等, 我硬着头皮怯生生地自己去奔走, 总算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地过来了。
后来博文中学维持不下去停办了, 我转到住家附近的正中中学上学, 那已是高中了。在高中我遇到了一位书教得很好的数学、物理老师, 叫施汉章。他是浙江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 江苏人, 没找到对口的工作, 就在学校里当老师。在他的影响下, 我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 打下了我以后有机会上大学时学工科的基础。
这时我家早已搬到北海路的荣寿里的一幢弄堂房子里, 住的是间在亭子间上层的晒台搭出来的房子, 用层板隔成两小间, 中间过堂没有门。楼下各家生煤球炉子, 木柴烟气全往我家跑。这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里大约住着10 家住户, 原来的灶间早租给人住了, 炉子都放在走廊里, 所以也没有新鲜空气可言, 只是烟更呛人, 我们就在门框上挂个草席挡一挡。有一个星期天, 一个同学来找我, 在满是柴烟中憋着呼吸, 跑楼梯上来, 掀开草席找到我家,他的脸憋得通红, 我的脸也一下子全红了。贾谊的《过秦论》有句“陈涉瓮牖绳枢之子, 氓隶之人”, 我特别理解, 陈涉家的门没有轴用绳子系着, 恐怕是木柴门, 我们虽然在上海大城市里却连木柴门也没有。抗日战争胜利后, 父母才出钱请人用层板做了一个没有油漆的门。
大约1944 年初, 大哥的一个同志杨炎的妻子扮成卖菜的人,找到我母亲, 说上海又有一位大哥熟悉的同志被日本人抓走了, 要我们想法子尽快通知大哥。这时大哥已在苏州葑门外住下, 我去过, 于是这个担子落在我肩上。第二天, 一早我就坐火车去苏州通知大哥, 正好大哥的同志张琪也在他家, 他们对我的勇敢很是称赞。当晚我即返回上海, 返回时发生了惊险的一幕。苏州火车站站台上人挤得不得了, 车到后, 大家都往车门挤。对我来讲, 挤不上车, 不仅车票作废了, 大哥家离车站很远, 晚上也走不回去, 而且母亲在上海肯定不睡觉等着我, 所以非上不可。但我力气小又没有经验, 只踩上了一节车厢门口的脚踏板, 手拉住把手, 半个身子悬在车门口。那时火车门都不可能关的, 因为每节车厢门口都吊悬着人, 就这样火车开了, 过了几个站, 挤着的人群动都不动, 原来车厢里坐的全是日本鬼子, 中国人一个都不让进去。就这样, 我在呼啸的寒风中, 坚持拉着把手站到了上海, 手脚都僵木了, 稀里糊涂地在半夜到了上海, 不知道站了几个小时, 事后想起来还很后怕。
1945年初, 美国飞机开始飞到上海来轰炸, 是四个发动机的“空中堡垒”轰炸机, 可能是炸市区外的军事目标, 所以市区没有受到轰炸, 我们是又高兴又担心。我们家住得比较高, 可以看到高射炮烟火, 因为市区里有高射炮阵地, 只是飞机飞得高, 高射炮一团团爆炸烟火够不上它。这时, 市民开始紧张了, 菜场里黄鱼比较便宜, 母亲和邻居们都开始腌黄鱼, 以防以后没菜吃。
那年暑期前我高中毕业了, 上海正是乱糟糟的时候, 根本不可能找什么工作。我在亲戚的小糖果店里做了一阵子店员, 又做了一阵子评弹剧场的售票的, 都不是长远之计, 正好舅父的一些朋友要到浙西内地去做生意, 又听说内地考上大学可以有公费, 于是父母决定让我跟舅父一家走, 既可能有些出路, 又可逃离即将到来的战乱。临别前, 虽然谁也不说, 但似乎有种生离死别的气氛, 母亲早坐在床边上抽泣了, 本来不大讲话的父亲, 更是紧闭着嘴, 只在提着行李送我到楼下上三轮车时, 呜咽地叮嘱说:“一路上要自己小心。”50多岁的父亲, 把孩子全送离了身边, 那时我17岁。
坐火车到杭州, 再出发坐船到桐庐, 步行一天穿过封锁线, 我们终于摆脱了日寇的阴影。我们一行在浙西淳安住下后不久, 日寇无条件投降了, 大家真是欣喜若狂, 没有想到抗战胜利那么快。不久, 我随舅父他们离开淳安, 坐船回到杭州, 之后又回到上海家中。混乱之中, 时机错过了, 便考入了上海临时大学先修班复习,准备1946年夏天考大学。1946 年夏各大学分别招考, 为保险计,我在上海先后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 (简称上海交大、交大) 航空系、清华电机系, 去杭州考了浙大化工系。那年考生特别多, 报考交大的有上万人, 因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年招生, 小日本被赶跑后, 历年积压失学的学生有了转机, 纷纷寻求继续复学。我在三个学校都发表录取后, 毫不犹豫地决定进交大, 因为我家在上海。这一年交大共录取了800名学生, 我们航空系学生即有40名。
交大是穷学校, 上边给的经费少, 新生入学, 住的宿舍花钱盖起来, 要收学生的钱, 我家没钱, 就走读。好在国立大学不收学费, 而且航空系属于建训班之一, 每月还给学生发几块钱公费, 够我作为上学的电车费。到了第二年, 才免费住入了学生宿舍电讯斋。宿舍里一个房间八张双层铺, 住16个同学, 空处挤满小桌子,供每晚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