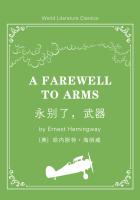这下可就捅了马蜂窝!因为“天不怕”父亲的外号就叫“不怕天”!“天不怕”扔掉手中的柳树龙,一个箭步蹿到“黑铁塔”跟前,挥拳就打,说:“你还想当我爸?”
“打,打!”街上派小孩全部扔掉手中的柳树龙,向乡下派小孩冲过去。
“不能打,不能打!”“小虎子”连忙扔掉龙头,跑过来劝架,“都是一个村的人,不能打架!”
大家你拉我扯,乱成一团。“小虎子”不知道该拉谁的架,想起“擒贼擒王”的话,急中生智,紧紧地抱住“天不怕”的身子,说:“小强哥,别打了,别打了。”
“天不怕”和“黑铁塔”势均力敌,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被“小虎子”拦腰抱住,难施拳脚,“黑铁塔”趁机挥拳砸向“天不怕”脑门;“天不怕”脑袋向上一扬,拳头不偏不歪,正好砸在鼻子上。顿时,暗红色鲜血委委屈屈地从两个鼻孔里涌出来。“天不怕”觉得人中处有虫子蠕动感,用手背一抹,见是殷红鲜血,立刻“哇”地哭了起来,扁着嘴说:“不要脸,两个人打一个。我告我爸去,我告我爸去。”
“小虎子”见“天不怕”出了血,心里也慌了,赶忙撒手,用手背帮着“天不怕”擦鼻血。
打架双方顿时作鸟兽散。
“满口香”茶馆座无虚席,香气四溢。人们天南地北地神聊,口里吐出的声波黏在碗中冒出的热气里,袅袅地上升,扩散,最后蒸发得无影无踪。三十来岁的“不怕天”,腮帮微微鼓起,嘴巴急速地往淡黄色竹烟筒里灌进一股气,只听“噗”的一声,一粒豆豉般的烟灰从烟筒头上的烟眼里蹦出来,掉到地上,扯着一丝淡蓝色的烟尾巴,苟延残喘着,慢慢地悄然逝去。“不怕天”吐掉了烟灰,嘴巴腾出了空闲,不甘落后地张开,大声呱叫地说:“肏,这次到九江行动真过瘾……”话未说完,儿子“天不怕”呜呜地哭着跑进来,说:“爸,乡下人欺负我。”
“不怕天”看见儿子胸前的白衣服上染着红血,惊问道:“谁打得你这样?”
“天不怕”如此这般、添油加醋地诉说一番。“不怕天”一听,火冒三丈,屁股从板凳上蹦起来,说:“走,找他们大人算账去!”
“不怕天”领着“天不怕”,奔出茶馆,往南径直而去。刚走一箭之地,迎面碰上“小虎子”母亲杨李氏,提着一小竹篮鸡蛋。杨李氏见了“不怕天”父子,连忙满脸堆笑,十分内疚道:“金刚侄子,真是对不起,我那个憨崽哩不会劝架,弄得小强挨了打。我拿点鸡蛋来给他补补身子。”说着将篮子递给“不怕天”。
“不怕天”左手一挥,一篮子鸡蛋满地打滚;右手扬起手中的烟筒,往杨李氏头上一砸。随着“咯嘣”一声闷响,一股殷红的鲜血从杨李氏额头上流下来,杨李氏身子晃了晃,慢慢地倒了下去。
“不怕天”见杨李氏躺倒在地,心里不免发怵,嘴里却说:“怎么啦?你还会装死啊?”说着就想脚板搽油——溜之大吉。不料,族长托着烟筒背着手由南向北而来。族长大惊,说:“你这个不孝之人,竟敢打婶娘?打得婶娘倒在地上,不但不扶,反而说装死?你乃习武之人,怎么毫无武徳?当年武举人杨寒柏,三岁小孩打了他,他都摸摸脑袋笑。你却打婶娘!我今天要是拄了拐杖,你便作死!”
“不怕天”虽然看见族长手中是托着烟杆,不是拄着拐杖,但到底还是有点怕,结结巴巴道:“我……我……没想到……”
族长扶起杨李氏,从烟袋里撮出一撮金黄柔软的烟丝,揉成团,敷在她伤口上。杨李氏脸上的红色蚯蚓慢慢地停止了蠕动。族长瞪了“不怕天”一眼,说:“你等着!”
……
族长耳朵里仿佛至今还回响着龙头拐杖敲打屁股时“噗噗”的声音。听见这声音,就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杀猪刮毛前,木槌敲打在死猪肚子上那种沉重的富有弹性的声音。那次,“不怕天”本来也要沉潭,由于他母舅出面求情,族长看在他母舅和他母亲的份上,网开一面。白马寨有个规矩,沉潭者的母舅出面求情,可以免于沉潭,改为“杖刑”。
那天,族长正和几个房长商议对“不怕天”动用族法,一个拐脚男子跌跌撞撞地闪进来,扑通地跪在族长面前,泪流满面地哀求道:“求族长开恩,求族长开恩……”话音未落,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也摇摇晃晃地跌进来,跪在族长面前磕头如捣蒜,哭哭啼啼地说:“族长,我十六岁守寡,就这一点血脉,您就看在我的老面上,放他一马吧!我娘俩下世一定做牛做马报答您……”
看着这位额头挨着地面的杨万氏,族长不由得生出几分敬意。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三天,丈夫跟人去常德经商,三个月后,患急症而死。杨万氏悲痛欲绝。晚上,杨万氏躺在床上垂泪,泪水洇湿了半个枕头。忽然,杨万氏隐隐约约听见后间的婆婆哭唧唧地和公公说:“老头子,我们这户人家要散了。”公公也哽咽着说:“我们命苦啊,生了一伙女,老年得子,没想到他没带寿来!现在……媳妇太年轻了,守不住啊。”婆婆说:“没有生育,守什么啊?这个家早晚要散啰。唉!”杨万氏听了,好比钢刀挖圆心,连忙擦干眼泪,起床叫开公婆的门,哽咽着说:“爸,妈,二老放心,我已经有了。生下来无论崽女,我都守一辈子,将孩子带大,为您二老养老送终,决不改嫁。”说得二老又悲又痛,又惊又喜,搂着媳妇号啕大哭一场。七个月后,杨万氏生了三天三夜,急得婆婆三步一拜、九步一跪地前往北屏禅林求观音菩萨,终于生下一个八斤半重的儿子,取名杨金刚。
杨金刚是全家唯一的希望,视如太子,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飞了。只要一声啼哭,公公婆婆就心惊肉跳,杨万氏就浑身筛糠。长到三岁,看见村里一个官员骑马回来,哭着要骑马。公公没办法,立即趴在地上,叫孙子坐上去,自己在地上慢慢爬行,一边爬,一边“嘶嘶”地学着马叫,逗得杨金刚咯咯大笑;婆婆则拿来一根小棍子,塞到杨金刚手中,教他一边抽打公公的头和屁股,一边“驾驾”地叫着。杨金刚平时看见村里哪个小孩手上有什么好吃的或者好玩的,他志在必得;倘若对方不肯,他便大哭大闹,满地打滚,哭得昏厥过去。吓得公公婆婆连忙找到对方的家长,求情乞讨或花钱购买,以满足杨金刚。慢慢地,杨金刚就成了村中的小霸王,自称“不怕天”。
族长双手手掌往上一托,示意杨万氏姐弟俩平身,看了几个房长一眼,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们也不是铁石心肠,只怪你儿子自小惯坏了,忤逆不孝,不惩罚也不行。要不,看在你和他母舅的面子上,放他一马。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第一,叫他向婶娘打爆竹赔礼;第二,进家庙,打三十族棍。此乃我个人看法,还不知几位房长意下如何?”
村中大事小情向来都是族长一言九鼎说了算,房长只是个陪衬,谁也不会违背族长的意志说什么,何况都是一个村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纷纷点头同意,说族长考虑得周到,杨金刚也是村里一个人才,或许是一时考虑不周,行为莽撞,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白马寨墟场人山人海,人们踮脚翘首,两个眼珠子瞪得如同两个黑葡萄,一眨不眨地盯着戏台上。戏台东侧坐着族长,西侧坐着几位房长,正中端坐着头裹白毛巾的杨李氏。族长看着戏台下面人头攒动,估计能来的差不多都来了,便慢慢站起,走到戏台前,双手朝下按了按,示意人们肃静。戏台下顿时鸦雀无声。族长轻轻咳嗽一声,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们白马寨出了个不孝之人,就是自称‘不怕天’的杨金刚,竟然用烟筒打破了婶娘的头。在我们白马寨,别说是婶娘,便是一般妇女也不能打!女人是什么?女人是男人生命的另一半!道教《太平经》讲得多好,‘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当得衣食也。’我们白马寨女人不比一般地方女人,任人打骂。我们白马寨女人不容易,男人在外挣钱,女人在家管田管地,建房盖屋,孝敬公婆,教儿育女;而且,个个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人人都称得上巾帼英雄。所以,绝不允许任何男人欺负!‘不怕天’打婶娘,大逆不道,按照族规,本该沉潭。可是,他母舅出面求情,加上他是个遗腹子,他娘杨万氏十六岁守寡,守身如玉,几十年来没有半句闲话,不容易。要是沉潭,杨万氏没人养老送终。所以,我和几位房长商量,网开一面,从轻发落,叫他一是赔礼道歉,二是打三十族棍。下面,就要杨金刚向他婶娘赔礼道歉。”族长迈着八字步,坐回原来的位置。
“不怕天”从戏台后面出来,双手托着一个枣红色传盘,传盘上一只青花瓷小茶盅,冒着腾腾热气,跪在杨李氏面前,将传盘举过头顶,说:“婶娘,对不起,侄子金刚打了您,罪该万死。侄子在这里向您赔罪,请婶娘喝了这盅茶,原谅侄子行事鲁莽、忤逆不孝的罪过。侄子今后一定像孝敬亲娘一样孝敬婶娘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