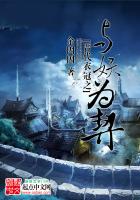“不可能!”他瞬间自思,转念ご想,“此事极端秘密,绝无仕何人知晓。倘若沐从道真的知晓了,必定会前去直取,何必再ブ来问我呢?他的话显然有诈,放的是试探气球,无非在诈问,探听虚实而已。我决不能上他的当!”
“哈哈!”想到这里,王俊民突然放浪大笑,说:“沐大人真会开玩笑啊!您是贡院的首席主考官,杨荆公若有东西转交,自然应当先上交于您才是,怎么会下交于我呢?您要是不信,亲自派人到西经房里去査看二下,不就二清二楚了吗?”
沐从道阴沉着脸,见王俊民说得天衣无缝,立刻改变了腔凋,说:“康侯,你这是说的哪家子的话呀?请千万不要怪乎。我只不过是为杨荆公着想,想知道他生前对自己的后事有何交代。因为若有交代,非你即我呀。现在看来,既然没有什么交代,那我们不过是替古人担忧而已,那就罢了!”
沐从道一无所获,虽然稍有放心,但仍心有余悸,不甘心就此罢手。于是,他假仁假义地说:“康侯啊,杨大人已经走了,老夫心中十分悲伤,万分难过。我们毕竟共事一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行影孑立,倍感孤独。这样吧,你也莫住西经房了,这就搬到这边的院子里来,一个住东,一个住西,咱俩做个伴吧,免得两人都太过清闲。”
王俊民一时不知所措,但转念一想,立刻明白了沐从道的用意,无非是来个“清空之术”而已。他明白这不过是让自己冠冕堂皇地离开西经房,好借机变相搜查他的住所罢了。
面对这雕虫小技,王俊民智者若愚,佯装不知,若无其事一般,便领了个顺水人情,说:“沐大人如此关照体贴,多谢一片好意了!我这就去取行囊,立刻搬过来。”
“慢!何必如此呢?这类区区小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劳神费力吗?”沐从道随即吩咐自己的亲随;“去,到西经房去,替王大人把行囊搬过来。”
“是。”随从应声而去。
王俊民心知肚明,这是为了方便“清空搜查”,遂轻蔑地一笑。
杨荆公自杀的消息,很快由沐从道径直禀报于曹皇后。
曹皇后听罢,禁不住又吃一惊,开口埋怨沐从道和张茂则,争勇说:“你们干得好事!一个个竟然这般的不中用!一件区区小事,竟然越闹越大。死了言齐一个人,事情尚可说得过去,可如今又死了一个杨考官,这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啊?事情一旦闹于朝廷,告之皇上,科考案事焉能不发?那时追究起来,你们如何是好?”
沐从道诚惶诚恐,急忙跪在皇后面前,说:“在下无能,愚人始料不及。”
张茂则也匆忙匍匐在地,说:“万望皇后宽恕!事已至此,恭请赐教。”
曹皇后也难免焦躁不安,但强打精神,说道:“自古英雄多磨难,成事未有一帆风顺之理。咱们本来就有点利令智昏,可事到如今,没有退路,只有一贯到底!你们应知轻重缓急,千万不要麻痹大意。目眼下要处理好善后,同言齐大人一样,杨荆公按病故殉职处理,厚恤眷属。一定要注意控制事态,不能让星朝皂星之火酿成燎原大灾!还有,那柄金如意,那几张银票,还有其它相关的东西,那都是涉案的麻烦东西,要统统地找回来,把自己的股擦拭干净,以绝口舌之患!”
“是。”沐从道、张茂则头如捣蒜,应声答道。
曹皇后略加沉思,又叮咛道:“事不宜迟,要加速办结账试啊事,早日放榜!此事不决,科考未了,人无宁日,夜长梦多。”
“是,遵命。”沐从道、张茂则连连点头。
曹皇后又特别嘱咐道:“王俊民,可是这件事情的关键人物。他的态度至关重要,他的状元身份也格外引人注目。事到如今,他是否了解事情的内幕与详情?你们应该心中有数,他是活着的人证!你们一定要在他身上做好文章,千方百计把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为我所用。要动点脑子,多想办法,别像个榆木疙瘩似的,总不开窍。”
接着,曹皇后又悄声对张、沐二人细语一番。
“是。”沐从道、张茂则心领神会。
告别曹皇后,张茂则跟随沐从道,马不停蹄,来到贡院。
沐从道急匆匆地,把王俊民叫到会经堂来,说:“康侯啊,张公公今儿来贡院,带着皇后的懿旨,特地向你传达。”
“是。”王俊民躬身听候。
张茂则当面宣读:“曹皇后懿旨:应天府南京考试官王俊民,行操端正,年轻有为,望悉心供职。今特命你与诸位考官和衷共济,齐心协力,讲求时效,即刻办结殿试一切事宜,事毕回朝听封。”
“谢皇后。”王俊民听罢,心里很不平静,活象吞了五味子。曹皇后的旨意不言而喻,他一清二楚,心中琢磨:“好一个皇后的懿旨啊!这不明明是给我戴高帽子,以封官许愿之法,假借王俊民之手,公然成全科考舞弊之事吗?上命如山,下官难违啊!顺之则将背负同流合污之名而飞黄腾达,违之则将大逆不道而遭罢官削职之虞,真难煞人也!”
此时,沐从道站在一旁察言观色,心里嘀咕:“如此的器重与恩宠,这般的高官厚禄悬赏,前有言齐死亡之鉴,后有杨朔公声自尽之训,王俊民岂能无动于衷吗?他将会如何选择?他到匙科是个识时务的俊杰,还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傻瓜?”
他坚信王俊民一定会掂量出个轻重来,惟命是从地遵照行事,甚至感激涕零。想到这里,他很开心惬意,说:“康侯湾心可真是皇后的掌上明珠啊!看,她对你是何等的器重,何等的远厚爱!机遇难得呀。”
“是的,俊民心里明白。”王俊民微微点头。
“明白就好。”张茂则也加以催促。“及早办结殿试之事,乃曹皇后对你的期盼,望康侯从速定夺。”
王俊民心中盘算:“皇后的懿旨在上,我是不能明拒硬抗的,那样做太不明智。但我不能盲目就范,也不能总是含糊其渝词,应当及早亮明自己的主张才是。”
于是,他张开口说道,:“皇后如此器重下官,俊民不胜感激,行一习今命我等及早办结殿试事宜,俊民岂敢怠慢!作为贡院主考官,俊民当不遗余力,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也。然而考官之良责,乃为国举拔贤英,必出以公心,亲阅试卷,择优录用。而俊民刚进得贡院,尚未遍阅文卷,又未识得贤英,举荐将何以为所据?况且,对于现在拟定的殿试名单,考官们意见并不一致,言已齐大人至死未签押,扬大人签后又自尽了。在这种情况下,位大民不经深思熟虑,焉能轻率签押呢?”
沐从道和张茂则听了王俊民的一席话,显然大失所望,郭冷水浇身,心里凉透了。
天王俊民看到了他们的扫兴;却不加理会,心想:“我应当拇赖下他们的疮疤,捅一下这个马蜂窝,打消他们的幻想。”于是,他打开天窗说亮话,开口说道:“二位大人,恕我直言,我在进得贡院之前,曾亲眼见过许将等人默写的试卷,那可称得是本届科考的冠顶杰作。而进得贡院之后,至今却尚未看到此卷,不知原因何在?”
沐从道和张茂则听后心里一怔,相互看了一眼,显然有点心慌。王俊民不屑一顾,紧接着说:“秉公而论,许将的试卷,要远胜于张仲的试卷。此次殿试,若弃贤英而纳平庸,不荐许将为而另推他人,就难免众人说考官们瞽目无光,有眼无珠,阅卷输掉眼色,如此则必将上不允、下不服。我等既为朝廷命官,今日为国计,理所当然地应当举荐许将为本科状元。”
沐从道和张茂则听着,不料结果事与愿违,心里又急又慌,一时哑口无言,默不作声。王俊民趁机主动出击,态度坚不可渝,说:“沐大人若无异议,我们就另拟呈文,即刻签押,马上送达,当日办结,岂不快哉!请二位知我之心,解我之意,助我之行,共复王命。如此,则可上遂皇后之愿,下合考生之盼也。”
张茂则、沐从道听罢,气得七窍生烟,欲发作而不能,对视良久,垂头丧气。
沐从道并不甘心罢休,反驳道:“康侯此言差矣!一来殿试所选名单,并非庸才,乃考官们共同商定,择优选录,且三人中已有两人签押,并无私心杂念,不能矢口否定。二来言齐和杨大人之死,其各自事出有因,责任个人自负,不能与殿试大事硬扯在一起,那是二十个鸡蛋——两把,不可混为一谈。三来闽州考生许将的文卷,其现就在秘阁,前有争议,虽已破损,但阅无妨,其不过也是平平之作而已。你乃新充考官,切莫听见风就是雨,以讹传讹,混淆视听啊!”
听了沐从道的狡辩,王俊民不慌不忙,反问道:“事实胜于雄辩。诚如沐大人所言,科考如此光明正大,公平无暇,岂会引发考生告状、考官之死、考榜难张、考场泄密之事吗?”
“这——”,沐从道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张茂则拉大旗做虎皮,以攻为守,说:“康侯,你不要太过自信!殿试的名单与呈文,并非随意而定,沐大人业已禀报曹皇所后,皇后已点头恩准,可谓上下融通,诸方和谐。而你却以一己之见,全盘否定,另选他人,岂非排挤异己,违逆懿旨,行事有点自不量力吗?你这样做,何好之有?莫非私心膨胀,目中无人吧!”
王俊民莞尔一笑,沉着回答:“张公公,你莫以一己私心而度人之腹啊。俊民一生别无他求,志在天下为公,之所以荐许将为状元,乃因其试卷胜过张仲,取之有据,问心无愧,岂在一己之见也?而张仲文卷较之许将等,显然相形见绌,有人却力举张仲而舍弃许将,请问这是何心膨胀?公心还是私心?难道是目中有人吗?”
张茂则被揭了疮疤,戳到了痛处,张口结舌,变成了哑巴,但他并不甘心,以威胁的口味,说:“康侯,请你自重!你虽身为考官,是否有些清高自傲,行事怠慢,固执己见啊?如此亵渎职权,辜负朝廷,这让我如何回去复命呢?难道你要自绝于人,自毁前程吗?”
张茂则的话,的确对王俊民有点震慑。年轻的王俊民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追求锦绣前程是很自然的事,听后心中怎能不无所顾忌?他的脑海里如波浪翻腾,暗中思忖;“是啊,逆上峰而行事,仕途皆短命也!难怪古人常云:在朝为官,‘伴君如伴虎’,‘不如回家种红薯’。然而,惟上峰而是从,心有不甘四人生在世,何以为宗?鸿雁尚且留声,况且人也!生当为人斧死亦为鬼雄。人乃高级动物,当拥光明之志,行大中之正,岂能顶戴乌纱,趋炎附势,屈膝谄媚,形同走兽?”
王俊民思虑再三,他知道小腿是拗不过大腿的,硬顶下去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而出卖灵魂他又于心不甘,实难从命。正所谓“无欲则刚”,他终于拿定一个主意:“以退为进,逼其改弦易辙!”遂毅然决定激流勇退。
于是,他拱手回道:“俊民不才,虽承蒙皇后厚爱,但力不从心,不胜其任,难尽其职,空负其责,故烦请张公公启禀皇后,俊民这就请求辞职,复旨领罪。”
张茂则和沐从道一听,张飞穿针——大眼对小眼,目瞪口呆。他们不曾料到王俊民会来这一手,一时尴尬不已。这一非常之举,其在朝多年,竟然前无所遇,后无所闻。
张茂则明白,王俊民在这个节骨眼上辞职,对尽快结束殿试一事,实在太不利了。他不得不压住心火,欲行挽留,说:“康侯,请不要轻率放肆,望三思而后行!”
沐从道也赶紧上来打圆场,说:“状元公,开的什么玩笑?切莫后悔啊。”
“无官一身轻,逍遥游太虚。”王俊民睥睨一笑,义无返顾。
张茂则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回到宫中,禀告皇后:“王俊民不想按我们的意志行事,宁肯辞去主考官一职。”
“不识抬举的东西!”曹皇后一听,大为光火,气狠狠地说:“他辞的什么职?无非是想要挟我们吧!他不听当当,用不着他辞,把他抹了就是!”张茂则说:“王俊民这个人,我先前曾闻说其人,他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性刚峭,不可犯,言有信,行必果。今日得见其面,从他说话的口气来判断,好象对科考取状元一事,全然知晓,内情一清二楚。”
曹皇后问:“他都说了些什么?”张茂则说:“他提到了张仲,说到了许将,一口一个‘光明正大’,一声一个‘秉公行事’,口口声声‘在其位,谋其政,司真职’,好像洞察一切,成竹在胸,即使九牛牵拉,也难以回头。”
曹皇后说:“他一个小小的主考官,刚进京人贡院,又能晓得多少事情?”
张茂则说:“他虽然初来乍到,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伺况人有顺风耳。王俊民肯定掌握了科考的把柄,有可能是最了解内幕的人。”
曹皇后一听,倒有点坐卧不安起来,说:“这个情况不能轻易小看。你们不要麻木不仁,要立即设法,探明其心迹,摸清他的动向,看他手里都掌握些什么真凭实据?无论如何,不能让醋酸在他的手里!”
“是!可他有些软硬不吃。”张茂则嘴里答应着,但心里茫然无底,不知所措。
“他不是要辞职吗?你再去贡院,传我的话。然后……曹皇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连忙与张茂则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一番。
张茂则奉皇后之命,复至贡院,先见了沐从道,叙说了曹皇后的旨意:“对王俊民的请辞,皇后意在又打里拉。‘准辞’是要刹一刹他的骄气,‘待命’是为了稳住他。前提和关键是,要摸清他的心底。”
沐从道听明白了,然后把王俊民叫来。张茂则对他说:“康侯请辞考官一事,我已转呈曹皇后。皇后得悉后,特予准辞。但念你往日忠于朝廷,今番进京又日夜劳顿,特命你就地休假,候旨待命。”
王俊民一听,心中顿感茫然,那滋味不知是喜还是忧,前景也不知是福还是祸。
无论如何,他毕竟如释重负,仿佛走出了泥潭,超脱了是非之地,两个肩膀似乎轻松了许多,遂躬身谢道:“多谢皇后一片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