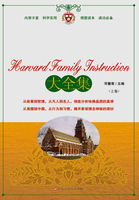律师破口念完了,何丽吓傻了,整张脸变得雪白,精神也萎靡了,这房子看来是没了,那个死律师说的头头是道,还有什么戏唱?何丽抹了抹后背,发现衣服汗湿了,身体却冰凉。小惠瞅着何丽,盯着她发紫的嘴唇,伸出了暖手,给何丽搓了搓背,轻轻拍着她。
法官趴在桌子上,瞟了瞟张军:“被告,你说。”张军问:“我说啥?”法官严肃地说:“说你该说的。”张军说:“按照律师的说法,我姐姐还有继承权呢。律师你没搞清楚啊,我家里几口人都不清楚,还分啥财产嘛。我父亲抚养我是没错,李学娟倒没抚养过我,她来我家时,我都长大了,都上班了。她没给我洗过一件衣服,没给我一分钱花,我也没喝过她一口水,我凭什么要养她。就这些,没啥好说的。”
法官看着律师说:“举证。”律师呼的站起来:“李学娟跟张定山结婚,有结婚证为证,张志立和张志欣为张定山继子,有户口本为证,常小惠为张定山和李学娟私生子,有小惠堂嫂作证。请求传唤证人。”说完上前,递上了证件。法官接了证件,松开了紧绷的脸:“传。”这时,法庭的门开了,小惠的堂嫂进来了,在律师的指引下,站到了证人席上。律师照例确认了她的身份,无非就是姓啥名谁之类的,接着问了小惠演变成私生女的原因。大姐就毫不隐瞒地,把麦地里的故事再讲了一遍,跟前次不同的是,这次讲得更流畅。
最后,律师问张军:“请问,你的姓名。”张军答:“张军。”律师问:“可有其他姓名?”张军答:“小时候大家叫我狗子。”律师说:“答有,或者没有。”张军说:“没有。”律师问:“张定山是不是你亲生父亲?”张军答:“你这不是废话吗?”律师说:“答是,或者不是。”张军说:“是。”律师问:“你父亲是不是去世了?”张军答:“还去世呢,早烧成灰了。”律师说:“答是,或者不是。”张军说:“是。”律师问:“李学娟是不是你继母?”张军答:“是。”律师说:“我问完了。”说完坐下了。
法官盯着张军说:“被告回答问题时,态度要诚恳,要正面直接回答问题。”张军应道:“是。”法官说:“你有啥问的?”张军说:“我问一个问题,大姐,你叫啥名字?”大姐答:“我叫大姐啊。”张军说:“你正经点嘛,这里是法庭,老实说。”大姐说:“我是叫大姐,姓大,跟我妈的姓,名字是姐,叫大姐。”张军惊愕了:“我问完了。”
法官说:“法庭辩论。”
律师说:“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法庭如实判决。”张军说:“事实清楚个屁,我还有个姐姐呢?你搞清楚了吗?”律师说:“这个,这个有待调查。”张军说:“那个小惠,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口说无凭,你有啥凭证?”律师说:“有证人证言证词。”张军说:“那我说你是我儿子,我叫我老婆作证,你信不信?”律师说:“你这是人身攻击,藐视法庭,我请求停止发言。”法官说:“同意请求。被告立即停止人身攻击,立即停止藐视法庭的行为。”
张军说:“张志立和张志欣,跟我没半毛钱的关系,我可怜李学娟,两个人的学费几万块钱,都是我垫的,她没打算还,我都没打算要,我就想问一句话,李学娟,你要不要脸?当年,充当第三者,搞得我爸妈离婚,害得我妈死在荒山野岭,我再问一句,李学娟,你是不是个人?你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你跟牲口有啥区别?”
李学娟说:“谁没良心?是谁整天提着刀,要砍自己的老子?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见过杀老子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你想没想过,没有老子哪有你?啊?你老子走了,尸体都没烧完,你还有说有笑,好像巴不得他早点死,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就这么做儿子?啊?我大几十岁的人了,还不退休,还帮你们洗衣服,帮你们做饭,帮你们带孩子,我还要赚钱养家,我跟你们计较过什么?啊?谁没良心?啊?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
何丽突然站起身,气愤地吼道:“要钱不要脸。”法官啪啪敲了几下锤子:“安静安静,不要说跟案件无关的事,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不得进行人身攻击,要遵守法庭纪律。”张军说:“凭啥说小惠是你女儿?律师你来说说,我看你能说出个子丑寅来,在法庭上忽悠人,你也太丢人了吧,你也太小看人了吧。”李学娟抢着说:“我在麦地里怀的她,还有大姐证明,那还错的了?”张军说:“全都没有证据,全是胡说八道。”
小惠瞅瞅左手边的亲妈,再瞅瞅右手边的亲哥,最后瞅瞅身边的嫂子,看着他们唾沫横飞,恨不得把丑事说尽,把裤子脱下来晾晾,心口就像扎了大把针,眼泪吧哒吧哒地往下掉。自从李学娟认出了自己,自己是既惊喜,又害怕,惊喜的是妈找到了,对养父养母有个交代了,他们在天之灵安息了,害怕的是接下来怎么办?如何面对这个妈,怎么跟她相处,怎么跟她过日子,怎么安下家,哥哥嫂嫂,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对待自己,都是个未知数。让她感到欣慰的是,深圳人没有串门的习惯,没有闲言碎语缠着她,大家各忙各的,谁也不在乎谁。
如果那个偶然的机会错过了,如果妈妈没有认出自己,如果没有搬进妈妈的家门,也许他们不会闹到法庭丢人现眼,也许自己的出现,就是大家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如果自己偷偷消失掉,也许大家的关系会有转机,要是这样,也不是不可以,妈还是自己的妈,就是分开过嘛。如果真的消失掉,就怕妈妈受不了,她老了,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还带着两个孩子,这日子太艰难了。哥哥是个仗义人,虽然嘴巴上硬,心里不糊涂,平时不跟妈妈计较钱财上的事,但是这么闹下去,他就寒了心了,哪里还会理睬妈妈,那不是更惨了?小惠立马推翻了出走的念头,要是拍屁股走人,自己是轻松了,孩子就要吃苦了,妈妈也没个指望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怎么办?也许苦口良药,就是沉默不语,先忍着吧。
法官说:“原告总结。”律师说:“由于原告和被告人户分离,增加了取证的难度,这个有待调查。我请求法庭调解。”法官说:“法庭调解条件不具备。”律师说:“我请求延后审理。”法官说:“鉴于案情不清,关系复杂,下次再审。律师务必提供完整的证据,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避免浪费公共资源。休庭。”说完敲了一下锤子,起身走了。其他人也稀里哗啦站起了身。
小惠跟着李学娟走出法庭,在门口停住脚步,转回头瞅着哥哥。张军看着可怜兮兮的小惠说:“看好你妈,想钱想疯了。”小惠立即掉下了眼泪,泣不成声地说:“哥哥,是我对不起你。”李学娟插嘴说:“没出息的东西,跟他废什么话?”说完扯着小惠走掉了。
何丽望着李学娟的背影,跳起来叫道:“老家的麦子长高了,回去再生几个,生的越多钱越多,赶紧啦,麦子割了就没机会啦。”张军喝道:“别吵了,跟骂街似的,八婆。”何丽气愤地说:“老不要脸,看着就脏我的眼。”张军看着祥子摊开手,无奈地说:“祥子哥,你看看,这事搞大了,老不死的早有预谋,不搞出个结果来,她是不会罢休啊。”祥子说:“怎么突然搞到这个地步了?”张军说:“可能是她压力太大了,我也在尽力帮忙啊。”
三个人离开了法院,找了家餐厅,吃完了中饭,就散了。何丽说:“我们没律师吃亏啊。”张军说:“我有理,一样打官司。”何丽说:“不知道接下来他们要搞啥鬼。”张军说:“就是分了,也没啥好担心的,难道真把房子卖了分钱?我不签字,看她怎么卖。无非就是要我掏钱,我不掏,我拖着不给,看她能咋样?”何丽说:“到时候,烦都烦死你了,最后你还得给。”张军说:“我拖死她。”
李学娟这边三个人,也是找了家餐厅,吃了个中饭。李学娟问:“律师,你准备怎么办?”律师说:“叫张军和常小惠做DNA鉴定,有没有血缘关系,查查就知道了。”李学娟松了松气:“要是张军不同意做呢。”律师说:“我在行使权力,他有义务配合,如果不配合,我们的举证成立,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他没那么傻。”李学娟说:“他姐来了怎么办?”律师答:“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那没办法。你事先都没讲清楚。”李学娟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阴笑:“这口气,我总算是要出了。”小惠说:“我还要上班,你们慢慢吃。”说完起身走掉了。李学娟接着跟律师东拉西扯问了一堆问题,然后西扯东拉聊了一堆无趣的话,最后才回家。
几天后,律师找到张军说:“请你跟常小惠做DNA比对,以证明你们有没有血缘关系。”张军瞅着律师,露出蔑视的目光:“你说做就做,你以为自己是谁?你凭啥要我做?”律师说:“我有权利要求你做,你有义务配合,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张军说:“如果我不做,你能怎么样?”律师说:“如果你拒绝配合,就是没有履行义务,判决对你肯定不利,最好还是做。”张军说:“做这个要花多少钱?是你出还是我出?”律师说:“你是履行义务,你自己掏钱。”张军说:“我跟老婆商量一下,回头给你电话。”律师说:“尽快,早完早收工,对大家都好,我等你电话。”
律师走后,张军立即上网查了查,发现自己还真得做,这下他紧张了,如果跟小惠真的是兄妹,分家就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了,说不定真的没房子住了,这可吃大亏了。回到家后,他立马给姐姐打了电话,跟她说了缘由,叫她马上来深圳。张军的姐姐张蓉蓉义愤填膺,气不打一处来,说带几个女将过来弄死她算了,最后应承张军马上动身。
何丽哄着冰冰睡着了觉,走出卧房来到客厅,心神不宁地坐下说:“赶快想办法,要是老不死的得逞了,我们住哪里啊?”张军说:“你急啥?姐姐过几天就到,她一来,我看老东西还有啥招。”何丽说:“来了又有啥用?你们两个人对四个人,还是分不到一半,还不是要掏钱?”张军说:“我每个月给她两百块,我拖死她。换了在老家,找两个人活埋了她。”何丽说:“你多大了?跟个小孩子似的,尽说气话,这里是深圳,不是老家,不能乱来,由不得你任性。”
张军开了瓶白酒,咕咚咕咚喝了几口:“老东西没入土为安,是不是他没安息,找麻烦来了?”何丽说:“是啊,就是啊,我老催你,你就拖着不办,这下好了,死定了,死人都跟你过不去,我看你怎么斗得过她。”张军说:“没时间你叫我怎么回老家?也是没办法嘛。他走了,还是不肯原谅我啊。其实,只用一招,就啥都搞定了,可惜啊可惜啊,老家伙走得急,没有交代,他大意了。”何丽说:“是啥?你快说。”张军说:“老家伙没留下遗嘱,我就造个遗嘱,啥事都不用愁了。”何丽突然睁大了眼睛,放出奇异的光芒,猛地起身跑进了卧室。张军吓了一大跳,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声问:“你受刺激了?”
何丽没有理睬,没有应答,唰的一声,揭开了被子,翻开了床垫子,只见几本杂志,还有一些不知道写着什么的纸片,她拿起来,瞅了瞅,甩手就扔下了。接着,她翻箱倒柜,在衣服堆里挖,在袜子筒里掏,挖完了衣服挖床底的纸箱子,掏完了袜子筒掏沙发,查完了卧房搜书房,进进出出,急急忙忙,噼里啪啦阵阵响,稀里哗啦搞搞震,最后一无所获。她走到张军跟前,抹了抹额头的蜘蛛网,瞪着眼睛,还没开口,张军就问了:“你怎么啦,被狗咬了?”
何丽问:“存折放哪儿了?”张军说:“你自己的还是我的?我的都给你收着,你的你也收着,你问谁?”何丽焦急地说:“那十五万的存折,不知道藏哪儿了。”张军说:“别急别急,好好想想,自己家里,还能跑到哪儿去?”何丽坐下来,翘着嘴巴说:“爸出事前两个月,给过我一封信,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开看。”张军张大了嘴巴,瞪圆了眼珠子,颤抖着声音说:“你早说啊。”何丽说:“我忘了说了,你刚才提醒我,我才想起来,说了也没用,不知道放哪儿了。”张军说:“我来找,那是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