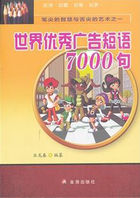王青麟驱马趁夜驰行,他虽追行甚急,但一路下来,却未曾碰到燕馗和那帮黄胡子的人,不知行了多久,只觉景致越来越明晰,抬头一看,东方已露出一丝鱼肚白,原来天光已亮。
突然,跨下马脚步忽地放慢,口中不安地发出一声声低声嘶叫,他疑惑地抬眼望去,只见路边倒毙着两匹马,离那马尸不远处,两个人也伏卧在地上,一动不动,从体内渗出的鲜血将地上的草丛都染成红色,惹来不少蚊蝇钉在上面,嗡嗡乱飞,甚是恶心。
从那死者的装束上,还有明显地头部受到重器钝伤的惨状上,他一眼便认出,这两人正是黄胡子一伙的。
他不敢怠慢,急急催马加鞭,行得十数里,又瞧见同样几具尸体,只是仍然没看到黄胡子的大队人马和燕馗。
接下来几日,那黄胡子和燕馗便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既无踪影,也不留丝毫痕迹,他漫无目的地沿着大道又急行了数日,逢人便打听有无大队人马经过,可碰到的都是一脸茫然地摇头否认。
这前后算来,已行了六七百里路,到了这时,他已然情知追赶无望,心中不由大失所望,刚刚走到大漠边缘,这大漠尚未来得及踏足深涉,便急火火地追随着黄胡子一众又折返回中原,照他心中想法,纵然无缘大漠探奇,结识一位世间豪杰,也不失为美事,可眼下,两桩愿望都落了空,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
怅然之中,于是放缓了步伐,一如前路,走走停停,只是情绪远远不如来时高涨,看着一切都索然无趣。
这日行至秦岭脚下,在一个小集市用过饭后,醉熏熏地翻身上马,踏入群山密林之中。
马儿不紧不慢地在山谷中走着,只是马上的王青麟酒劲上来,双眼不住地打架,身子摇摇晃晃,眼见难以成行,他晕晕乎乎中下了马,眼见前方有一棵大树,牵着马踉踉跄跄地奔向大树,将那马缰往树上胡乱一系,扶着树干慢慢坐了下来,闭上眼,便睡死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听得有人在耳畔说话,他睁开眼,只见眼前立着一人,相貌颇为熟悉,似有早识,却又叫不上他的名字,那人见他醒来,道:“好大的睡劲,叫都叫不醒!”
王青麟见到那人颇为新奇,伸手挠挠头,疑惑道:“我好像在哪见过你!是么!我们一定见过面,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那人苦着脸,抱怨道:“我在伏魔山受尽苦楚,你却整日里游山玩水,好生自在,不要光顾自己潇洒痛快,你这般做人可有点太自私了!”
王青麟默默思索,手抚着脑袋,将生平中熟识的人迅速在脑中过一遍,却是仍然想不起来这人来历,听到那人的话,不假思索反击道:“你这人说话好生颠三倒四,你受苦受难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这世间还有这种道理?自己受苦,便不允许别人享乐?”
那人大怒,扑上来掐住他脖子道:“你这忘本的小贼,没有我哪来的你?我今日便掐死你算了!”
王青麟心中大惊,伸手便欲扳开那人的双手,不料那人力气颇大,怎么也挣脱不开,他只觉呼吸越来越困难,忍不住大声叫了出来。
这一声叫出来,他双眼霍地张开,手臂兀自在胡乱挥舞,一顿胡乱张望,却不见那人身影,这才悟起,原来是梦魇一场,只是这一受惊吓,浑身汗透,这酒劲也醒了过来,山风一吹,顿觉得身上凉飕飕的,不由打了个寒颤。
他抬头一看,只见天际远处一小块一块的乌云正在前方的山项尖处汇聚,不一会便聚满整个山顶,,眼前景象瞬时间更加暗淡了下来,云层中不时传来一阵阵如牛吼般的雷鸣声,接着,卡喳一声巨响,一道闪电撕裂云层,脸上忽然一凉,原来几颗雨点打在了头上.。
“不好!要下雨了!”
他见状不妙,急急站起,解开马缰,跳了上去,奋力一鞭,那马乍一吃痛,撒蹄便狂奔起来,雷声轰隆不绝,但天色已全然黑了下来,前方目视能及之处,不过二三丈,漆黑之中,也难辩方向,只是一通乱走,他也不知胯下坐骑把自己带到了哪里,只是感觉自己处在一片无尽无边的森林之中.
忽然,前方似有一丝亮光闪过,他一勒马缰,细加端详,前方隐隐约约矗立着一大片建筑,似是一只张牙舞爪的黑色巨兽,那丝时明时灭的亮光,便是从其中一间屋子闪出.
这时一道闪光撕破长空,眼前景象被耀眼的电光照射地一清二楚,眼前确实是一所大庄子,只是处处破败萧条,有些屋子缺门少窗,有些只剩一些残墙败垣..
他从马背跳下来,将缰绳随意拴在一棵树上,信步向那间亮光的屋子走去..。
王青麟抬步上阶,伸手叩指在门门轻轻敲了两下,“有人吗?”
里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门吱呀一声被打开了,里面探出一个青年的脸来,见到他,神情中有些意外,他盯着王青麟,神色中带着些不安:“阁下是?”
王青麟拱手道:“夜黑风急,小可在这山中迷了路,只求一宿,打扰之处,还望海涵!”
那青年看着他,犹豫了半天,方打开门道:“言重了!这是一所荒宅,小生也是寄居在这里的!并非主人,请进!”
进到屋内,王青麟一眼扫过,才赫然发现,这竟然是一座庙堂,只见这庙内地方也不大,正中一大尊神像便占了不少地方,那塑像是一名面容祥和的中年人,体着绯袍,外罩金甲,一手持剑,一手持令旗,王青麟瞧了半天,也没端详出供奉的是何许人物。
神像右边,支着一张木床,床上整整齐齐摆着一个小几凳,上面放着一盏油灯和一本摊开的书,王青麟眼尖,远远瞧了几行字,便知是本《礼记》,他心中一动,原来这是位俟考的学子。
床前一张木板胡乱钉就的桌子,放着一些碗盆之类物事,除此之外,便别无他物了,倒是地上,被清扫得干干净净,不见浮尘,显见这个寄居的人,是个极爱干净的。
那青年见他不住打量,不禁有些局促:“荒庙简陋,这位公子莫要见笑!”
王青麟连连摇头,道:“哪里!哪里!荒庐幽居,芝兰畔侧,又兼山幽花寂,水秀草青,所谓闲看春花秋月,浮云卷舒,坐听山风林泉,松涛如怒,离俗世纷扰,避红尘羁绊,正是治学的好所在,何言谈陋?”
那青年听他夸奖,极为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惭愧,公子谬赞,小生不得已寄居此地,其中略有苦衷,只是不足以为人道而已,不全然像公子想的那样!”
那青年看了他一眼,试探道:“我听公子言吐不凡,难道也是我孔门弟子?”
王青麟哈哈一笑,自嘲道:“叫我抡枪耍棒或许还行,可若教我写经论策来,那可比杀了我还难!”
那青年一怔,半天脸上才挤出一丝笑颜,拱手道:“公子说笑了!”,他突地一拍脑门,口中唉呀一声,道:“我真是犯浑了,灶上还煮着粥呢!千万可别糊了,兄台自便,我且看看去!”,说罢,匆匆向后堂奔去。
两人言谈之时,王青麟便闻到一股淡淡的怪味,这时听那青年一说,心中不由嘀咕道:“可别真是糊了!”
不一会儿,只见那书生从后堂走出来,手中端着一盆散发着焦味的看上去黑糊糊的粥,不消说,适才那怪味便是来自于此,那青年将盆子放到桌上,口中不住地叹气,“原本足够招待公子的,可眼下,便是一顿粗茶淡饭,也是指望不上了,真是汗颜!”
王青麟连连罢手,道:“没关系,我此前已用过饭了的,现在也不饿!”,他见那青年呆呆地看着那盆粥,一脸的痛惜,始终舍不得将粥倒掉,一会之后,大约是饿极了,他自顾自地将那糊了的粥倒入碗内,皱着眉慢慢呷起来。
他每喝一口,眉头便自然而然锁成个川字,然后又松开来,再喝又皱得紧紧的,显然是十分难以下咽,王青麟瞧得一阵恶寒,忽地想起背后行囊中还有一些在前面镇子买的大饼,急忙取出,一并递给那青年,“兄台,我这里还有一些面饼,虽然硬了点,可总比吃这糊了的粥强点!”
那青年只是推托不要,王青麟哪容他这般客气,拉过他的手,不由分说,将一摞大饼放在手中,“兄台,不过几张饼而已,切勿客气,你孤身一人在此,甚是不易,若是吃坏了身子,误了功课,岂不因小失大?”
那青年急忙站起来,连声道谢,王青麟道:“你也莫公子长公子短的,我姓王,名青麟,叫我名字便可!”
那青年甫一坐下,闻言又站起来,拱手道:“王公子,幸会!在下梁在臣!”
王青麟见状急急罢手道:“梁兄,坐下说话便可,你这动不动便站起来,又是拱手作揖的,礼数太多,我可受不了!哈哈!”
那青年赧然一笑,细声道:“王公子不拘小节,豪迈大气,梁某是自愧不如的!”
王青麟左右望望,目光又回到饭桌上,道:“这晚饭也太凑合了点,看来梁兄这日子过得有些清贫啊!”
那梁再臣闻言脸上一红,点头道:“惭愧!先父母离世得早,家中除了十几亩薄田,便没别的东西了,我又疏于世务,不擅经营,索性租于他人,自己跑到这深山里读书,每年收的租子,足够裹腹便可!逢上时节,在山中也能采些野菜山笋之类打打牙祭,有容身之地,无饮食无虞,对于这种生活,梁某已经很满意了!”
王青麟道:“困厄可守心,贫贱不移志,梁兄甘忍孤寂,能沉下心来在此发奋图强,潜心修学,这份毅力,小弟极为佩服的,小弟相信,他日梁兄定能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梁再臣闻到此言,脸上未有喜容,闪过一丝羞惭之色,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正要开口说话,王青麟这时突然竖指作了个噤声的动作:“嘘!有人来!”
“有声音么?我怎么没听到?王公子您听错了吧!”,那梁再臣竖耳细听了半响,方才摇头应声,只是神色间却颇有些古怪。
王青麟凝神再听,除了风声呼啸,却没有别的声音了,他疑惑道:“怪了,刚才我明明有听到声音!”
“好像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我决计没听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