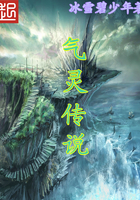(感谢收藏支持并留言打赏的朋友们,二更送上^^)————————————————————————————————
白达旦部的叛乱最终将随着时间慢慢淡忘在人们的记忆里。可是耶律贤不能忘也不敢忘。他要做的还有很多。
眼下的云州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桩桩件件都要他亲自处理。新任刺史还未到任,耶律贤成了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大至赈灾救济、城防布控,小至挖井开渠,插秧播种。事无巨细他都一一过目。他每日天未亮便到府衙署理政务,夜里打更的敲过三下才肯熄灯休息。可即便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呕心沥血,云州的情势依然不容乐观。
西南大旱,又遭匪患,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奏请朝廷赈济的银子迟迟发不下来,云州城外饿殍遍野。正所谓久灾必乱。补充城防军和巡防营的人马尚未到位,耶律贤只能从招讨司急调一千人稳住云州城以及周围几个县。寰州,蔚州,代州与朔州募集来的粮食只能解燃眉之急。五州均有旱情,互相帮援也极为有限。几万张嘴嗷嗷待哺。耶律贤只得勒令招讨司先调出一部分军粮解百姓之困。然而受灾范围之广、民众之多,这一点从士兵口中省下的口粮完全是杯水车薪。仍然不断有人饿死。耶律贤命人每日及时处理城里城外的百姓尸体,又让人将流民集中安置。每日定时由府衙统一向灾民发放水和粮食。然而受灾人数越来越多,可供给的粮食越来越少。灾民因为抢不到粮食常常发生推搡挤压,甚至致死致伤。
午时刚过,耶律贤经过城中一处集中派发粮食的地方,眼睁睁看着百姓因为抢不到粮食而发生口角,进而拳脚相加。他叮嘱跟在自己身边的司仓与司户在朝廷赈济的粮食与钱帛到来之前无论如何要将城里的灾民稳住,不能让灾民变暴民,重蹈白达旦部叛乱的覆辙。
骑马经过城郊一处荒废的宅院时,耶律贤停下问道:“这是何处?”
司法参军答道:“此处是临时设的牢狱。关押的都是白达旦叛乱中的乱匪家属以及袭击盐铁司的煮盐人。乱匪攻进云州城的时候,破坏了府衙的牢狱。这些犯人只能暂时关押在这里。”
听见“乱匪家属”四个字的时候耶律贤心中狠狠拧了一把。“走,过去看看。”原来所谓的牢狱并不是这处荒废的宅院,而是宅院地下的一处地窖。耶律贤带着人下了地窖,里面又脏又乱,臭气冲天。目之所及都是一些老弱妇孺。有很多人已经死去,还有许多奄奄一息。尸体无人处理,活人和死人挤在一起。简直是泯灭人性。
“怎么会弄成这样?”耶律贤心中一痛。
司法参军也面有不忍。“大多是饿死的。这些人秋后就要全部坑杀,所以暂时关押于此。从寰州调拨来的赈济粮连城里的灾民都吃不上,哪里能顾得上这些死囚。”
耶律贤双手紧紧握拳,指甲刺入手掌心却浑然感觉不到痛。那日在云州城中他承诺过那些“乱匪”,只要他们甘愿伏法他一定设法保全他们的家人。可是他失言了。眼睁睁见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却毫无办法。没有皇上的御旨赦免,谁也救不了这些犯人。
顾井匀一整日都未见到耶律贤,甫听闻他回府,即刻寻到刺史府正厅。一脚刚踏进门就见他耶律贤怒不可遏地在屋中来回踱步。云州知事郭廷伟拿着笔畏畏缩缩地坐在一旁的案几后。面前摆着几分空白的奏折。
耶律贤路气冲冲地道:“给我写。第一份递交到南面大王院,再催赈灾银两与汉地守军。倘若他们再募集不到银两就给直接送粮食来。第二份交南枢密院。云州刺史周必昌,面对乱匪,毫不畏缩,为救百姓英勇捐躯,请求善置其家人。第三份直接递交御前,请求皇上赦免白达旦之乱中所有乱匪家属死罪,准他们以罪奴身份服役抵罪。”
郭廷伟脑袋上豆大的汗珠一颗接一颗。连手中的紫毫舔上端砚都颤颤巍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按照耶律贤的意思写完了三道奏疏。
“即刻命人将这三份折子快马加鞭送往上京。”
郭廷伟刚把折子拢在手里就见一直静立在门外的顾井匀走进厅中道:“殿下,万万不可。”
“即刻启程!”耶律贤看也不看她,吩咐郭廷伟道。
“万万不可!”顾井匀直直望着他,没有半分退缩。
郭廷伟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抱着折子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虽不知这女子与宁王是何关系,却看得出宁王对她极为看重。一个连戍边西境、涉险降匪都带在身边的美人,定然不只是美人。
“这里几时轮到你做主?”耶律贤面色沉郁,沉默了一瞬咬牙道。
自从云山一路追随,耶律贤从不曾对她说过这般重的话。顾井匀微微一愣。“前两份折子殿下想怎么送都可以,可是第三份万万不能。”
“为何不能?”耶律贤仍然没有半分好脸色。“当日我在城中答应过那些死去的矿奴一定会保全他们的家人。当时你也在场。我既然说了就一定会做到。”
顾井匀望着耶律贤,耐心道:“正是因为殿下当初对他们有过承诺,所以此事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切不可操之过急。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凡事还需慢慢筹划。”
不知是哪句话触怒了耶律贤的神经,他突然横眉冷对,冲顾井匀道:“事到如今你还让我忍,还让我慢?若不是皇上称病不朝,处决这些人的圣旨已经在来云州的路上了!你真应该去牢狱里看看那些人此刻是怎样的处境。你若是看过绝不会说出这番话来。当日在城里我问你有没有方法可以救下那些人,你告诉我你没有。如今我要去救他们的家人,你又来阻止我。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残忍冷血之人。我一直欣赏你的智慧与胆识。可是你的才华就只能用在勾心斗角、阴谋算计上吗?你就不能用你那些可谋天下的智计为这些无辜百姓谋一条活路吗?”
顾井匀也难得拔高嗓音,寸步不让。“正因为我与殿下一样在乎他们的生死,所以在没有十全把握之前我仍然会劝殿下不要躁动。这份折子贸然递到御前,皇上心中必然怀疑殿下与叛乱之事有所牵扯。殿下心中也知道对于皇上来说,整个大辽不论部族、属国还是皇亲贵胄,谁都可以乱,只有殿下不能乱。一旦皇上心中将乱民与殿下归为一党,那么这些乱民才是真正的必死无疑!”
顾井匀这番话一针见血,真真点醒了耶律贤。他心中不是不明白,白达旦之乱虽然不是朝中政敌一手策划,却肯定少不了他们推波助澜。这样一件大事,就算周必昌故意瞒着掖着,卫王的探子,宋王的探子,若说京里没人有半点察觉,他绝不相信。这些人一早得到消息却隐而不报,无非是想把他和乱匪搅在一起。他们太了解皇上的心思。他是先皇遗孤,只要他与任何带乱字反字的事情沾边,皇上心中就不会痛快。皇上不痛快,就不会让他痛快。今日看见满街流民与牢中罪奴的惨状,他气自己无能为力。当日救不了周必昌,救不了那些矿奴,如今依然帮不了他们。他知道自己是一时意气用事,乱了方寸,才把气撒在顾井匀身上。
这是二人自云宫相识以来第一次因为意见相左而争得面红耳赤,僵持不下。耶律贤当时气得七窍生烟,可过后静下来想想,又觉得与他怒目相对的顾井匀竟多了几分人情味,不似平日那般凉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