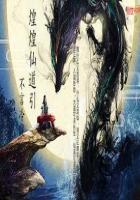布阵场,位于牟山颠的一个残旧战场,为当年闻人谦隐居之所。虽名为战场实则一个装饰,还原了西临关的那一场战事。其间断墙残瓦,深沟浅洼纵横,四处都是陈国和秦国士兵的战甲,布满了深红的血迹,深处布阵场不自觉便会遥想当年发生在西临关的那一场残酷战事。
——《星月地理志》
牟山高约数百米,或是布阵场的缘故,其间常伴随着风声鹤唳,犹如那些死去的战士的哀鸣,胆小之人罕有进山者,胆大之人也对此山望而却步。这山自从闻人谦来之后,便有了神鬼之山的名号,因着山顶本就不大的缘故,再加上一个方圆十里的布阵场,是故这一次的牟山论道大会的开胃菜百家论道放在了牟山村,待论道结束后,各家派代表上山讨论本次大会的核心议题,重定百家之长。
一阵风过,断墙前出现一个女子。此女一身黑衣,抱拳看着这一堵墙,两只眼睛紧紧盯着丝毫没有注意身边多了一个长发老者。老者看了看她,叹了一口气,找了一个石凳子,也不理会上面的灰尘,便坐了下去,说道:“你还没有放下?”
女人淡淡说道:“你也并未放下,何必说我?”
老者继续说道:“不知你下回来时,我是否还在?”
女人并没有看向他,而是走到山边,目光似乎透过层峦叠嶂的坡峰,看到了牟山村的人,说道:“你看他们现在的模样,像不像当时的西临关,那时候每个人都安逸,充满了信心。”
老者答道:“世无难事,何必自扰,自然是活得快乐,岂止这些人安逸,整个秦国都如此,你不知?”
女人突然加重了语气,说道:“那为何独我西临关不可安逸,为何要杀全城百姓!”女人说着话身形忽地窜到了老者面前。
“自你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我便说过,要杀的话,我的命随时都可以给你。”
“你的命。”女人惨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你的命值几钱,能抵我数十万西临兵士和百姓?”
“我布这个布阵场的本意就是恕罪,若非我当时克敌心切,也不会让那人攻了我心智,听信了他的建议,铸成大错,但是抛开这些不谈,那一场战事事关秦陈国运,是我之故又非我之故,时势自然而已,我想你也清楚。”老者说得真切。
女人转过身,边走便说道:“我这些年早就想明白了这一层道理,也知道了一种名为命运的东西,本想着跳出,近些年却越来越觉得身处其中的好处,你说得对,时势自然,那便顺着跟着,你不知这些年我看得通透,越发通透就越发觉着时势太慢,但终归是朝着我要的那个方向去了,于是我便想着推一把,就像这样。”女人这时候走到了断墙前,右手按在墙上,轻轻一推,那些用巨石堆砌而成的墙垣如同棉花一般倒了下去。
“如若我那位老友见到你成了这个样子,心里也会难受吧。”
“他早就不在了,如若他在,我岂会是我?不过,既然已经这般模样,我颜如玉便要将他当时失去的都讨回来,要让那些人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你放心吧,我们离那个目标不远了,待一切结束,我便来陪你!”
身后传来老者浓重的一声叹息。
牟山村的一处偏僻角落,布了一张台面,坐着一个人,那人长得纤细,若不是那人上方的“农家尚贤”四字表明他的身份,还以为是一位弱不禁风的女子。
“前几次论道,不见农家前来,这一次倒好,竟还论起道来?”
“或许来了,但是根本上不得台面的。”
“尚贤不是那个史家老四,怎么改投了农家?”
“听说勾引了史家家主的女儿,被赶出来了。”
四周来的人寥寥无几,但多半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还时不时发出几声刺耳的笑声。
“我农家务本,求实,当世时,世道纷乱,人情不古,有的是太多离合,数不尽,也道不清。”尚贤说得慢条斯理。
台下人则起了哄,叫骂道:“道不清,要你何用!讲的什么狗屁道义!”
“离火尚不能照全明,我本一家之道,如何道清这万千世道!”
“百家中显学无一不自成一理,自圆其说,你农家既然成不了大道,成不了显学,为何不独居深耕,来此论道为何?”
“此言差矣,既是论道,那便是将自己的道义说明,至于是非曲直自有公道,万事皆可议论,你怎可断了先生的讲学?”这时,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少年开了口。
见旁人开口,在场的人都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当即笑了起来。
“你一个毛都没有长全的小屁孩,懂什么道义?”蔑视道。
尚贤对这些视若无睹,只是安静地闭着眼睛。
“纵闻百家论道,先礼后听,既是尚贤乃农家大家,你们既然来此便当遵从古礼,行后辈之礼,后跪坐听农家道义。”少年侃侃而谈,丝毫没有畏怯。
这时候从人群中出来一个男子,说道:“看来娃娃书看的倒是不少,但你不知何为论道,论道讲的是一家道义,道义便是了然一种道理,如道家五行之术,博大精深,儒家仪礼之论,千古名扬,法家,知情尚法,国之大用,兵家,兵法三通,百胜之论。试问他农家何为?”
少年摇摇头,说道:“儒家言为人,讲究深通,先生方才所言,确是显学大家,自当成一体系,扬于百家,却决不可以之为全,厚此而薄彼,道虽大不用则小,道虽小用之则大,如儒家仪礼之术,讲究与人干系,如我红历人人仪礼,何来征战,那兵家兵法三通怕也是失去了用处。尚贤先生所言农家务本求实,其实于当下而言,正是苦口良药,荒漠绿洲。”
来人点点头,拱手道:“在下法家陆友明,小公子年纪轻轻便有这般学识,这般见解,前途无量,请问小公子名讳,所属何家何派?”
少年被他一夸奖,小脸微微一红,回礼道:“在下木子煜,孤家寡人。”
“陆友明,那不是法家长老史可法的高徒,听说在法家地位很高,想不到也来了这里。”
“连陆友明都称赞,这个孩子真的了不得啊。”
“木子煜,这人是谁?木姓很少见啊。”
原先怼尚贤那人看到这个小孩子竟然得到了陆友明的赞许,心中不快,开口说道:“你方才说我们先礼后听,你自己为何不做啊,竟安坐在椅子上,是不是你爸妈教了你道理,但没有教你怎么做啊!”
“我自知道理,来时已经向尚贤先生行了晚辈礼,不跪坐是因为晚辈腿脚不便故而向先生赔了礼,得到先生允许后才坐在椅子上。”木子煜说得淡然。
这时候,尚贤突地睁开了眼睛,对着那人立声喝道:“史家全魏,我见你为史家道友,容你猖狂,而今于我这道场当众骂人,可还有一丝史家风范,你这般让史家先祖颜面何存!”
“你一个被我史家扫地出门之人,竟还在这里骂我史家人?尚贤,今日你死到临头,拿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