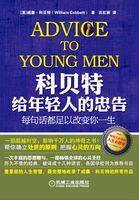先看简介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这些只是本书所要讲述内容的冰山一角。资深媒体人、知名专栏作家许骥认为真理是常识,常识却不一定是真理。绝大多数的常识都是感觉。所谓文明社会,是在常识的基础上,大家进一步建立起共识。许骥开腔不走火,用温和、客观、中立的态度告诉我们:世界不是我们表面看见的那样!每一个敢于和别人不一样的人,都有一颗强悍的大脑!
人日常的行为只是复杂心理的冰山一角,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了所有类型的人,有好人、有坏人、有会认错的、有死不认错的、有强迫症、有征服欲、有人渣、有购物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你召唤出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你自己。
好人根本不存在
常识未必靠得住
我们《原来酱紫》这个节目有个口号叫:“颠覆常识,寻找共识。”常识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协力合作的根基,非常重要。美国建国时候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常识》。香港的梁文道先生也写过一本时评集叫《常识》,分明就是对潘恩的致敬。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颠覆它呢?因为,常识可不见得都是好东西。
常识是什么?有一种定义是这样的:一般人所应具备且能了解的知识。这句话里面最值得推敲的就是这个“应”字。谁规定的啊?有人说:“约定俗成的呗。”没错,就是因为它是约定俗成的,才最危险。不相信的话,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常识:你是好人吗?
一听到这个问题,我猜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回答:我当然是好人!就算那个公认的卖国贼汪精卫,还有当时追随他的一大批文人、政客,回看他们当时留下的资料、日记,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才跟日本人合作,成立南京伪政府的,他们觉得那是中国的出路所在——所以,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不是好人。
不仅我们自己是好人,我们看整个世界,都要分出好人和坏人。小时候我们看电视,不也总是会问:“妈妈,他是不是好人?”“妈妈,坏人什么时候出来?”善恶忠奸,是中国人看待历史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凡有好,就有坏。刘备好,曹操坏;岳飞好,秦桧坏。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阴阳失调,大事不好。
但是,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心理学家关心的不是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人会变成好人或者坏人。1971年,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名字叫作斯坦福监狱实验。主持这场实验的心理学家,后来也成为大师,就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他曾经是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还是美国公共电视台心理学节目的主持人。
有次津巴多在演讲中说起,他从小就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就是:好人是怎么变成坏人的?要知道,任何坏人也不可能天生就坏,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津巴多举了一个例子:路西法。路西法是谁呢?他是上帝最喜欢的天使。可是,路西法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撒旦。路西法是怎样从天使变成魔鬼的?这就是津巴多最想要解开的谜题。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果,因此也就有了另一个名字:路西法效应。
这个实验太有名了,有名到什么程度?2010年它被改编成电影《死亡实验》,这是一部小成本电影,却有两位奥斯卡影帝在里面,分别是演《钢琴家》的大帅哥阿德里安·布劳迪(Adrien Brody)和演《末代独裁》的黑人大胖子科力士·韦德加(Forest Whitaker)。可以说,这个实验从根本上颠覆了很多人那种忠奸善恶的世界观。而且了解这个实验之后,你就会明白:世界上哪有什么好人哟,只不过是没把你放到那个坏人的位置上。
斯坦福监狱实验
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大体上说,这个实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登报招聘志愿者,要通过海选,保证志愿者没有心理变态,如果有的话,比如本身就是个变态杀人魔之类的,那么这个实验就没有科学性了。所以,最后挑选了24个心理健康的志愿者。他们的任务是分别扮演狱警和囚徒,在实验室里模拟监狱生活。注意,只是模拟。
第二阶段,模拟生活开始了。这个时候,津巴多通过闭路电视,观察所有人的行为举止、心理变化过程。他发现,那些扮演狱警的人起初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对扮演囚徒的人下手,但很快就投入角色,开始奴役囚徒。在他们被赋予的权力范围之内,那真叫像脱缰的野狗一样,尽情放纵自己的兽性。比如让囚徒罚站,搜身以羞辱囚徒,等等。如果津巴多等实验工作人员不在现场,他们甚至还超出他们被赋予的权力,滥用权力。人是很容易得意忘形的。
第三阶段,大家也能猜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扮演的囚徒反抗起来了。他们和“狱警”发生冲突,几乎酿成了暴动。这时候,只不过是实验进行到第五天而已——整个实验不得不被紧急停止了。
听起来,你可能还是觉得很奇怪——这些人又不是真的狱警,那些囚徒又不是真的囚犯,怎么就那么入戏呢?说实话,津巴多也没想到实验会变成这样。根据他的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周时间,但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对劲儿了,很快就发展到失控的局面。第五天的时候,津巴多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来探访津巴多,看到令她震惊的局面,才强烈要求暂停实验的。
津巴多的这位女友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她对实验也有独到的观察,其中有个细节特别有趣。有天她来到实验室,正巧碰到准备去更衣值班的一个狱警。美国人嘛,反正性格就是那样,互相吹捧跟不要钱似的,两人很快就聊了起来。在聊天的过程中,津巴多的女友觉得这个狱警亲切有礼貌,是个超级大好人。可是等这个狱警换上警察制服以后,津巴多的女友从闭路电视里看见他,当时就惊呆了,她说:“才几分钟,他就好像从头到脚换了个人,不但走路的姿态不同,讲话也完全不同——带着南方腔调……他正在大喊呵斥犯人,命令他们‘报数’,所有不在他规矩里行事的,都被视为对他的无礼和挑衅。”后来她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好人”,正是狱警中最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们还给他取了外号叫“约翰·韦恩”。
这个细节有趣在哪里?如果我们用中文简体字来看“制服”这两个字,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当名词用,是穿在身上的制服;一个当动词用,是我要你服从我的制服。当“约翰·韦恩”穿上了那套假的警察制服的时候,他瞬间就被那套制服给制服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超级大好人”,会因为一套制服,也就是赋予他的权力,马上变成一个“暴君”。听了这个故事,你还敢那么肯定自己是个绝对的好人吗?现在你是好人,是因为你并没有面对考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这点你必须承认。无论你自认为是个多么好的人,无论你信或不信,总有办法让你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好人、坏人这样的二元对立法则,是不懂事的小孩子的天真世界观。而正如美国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说过的,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自动丧失了天真的权利——你,只能面对复杂的现实。
好坏二分的价值观有用吗
现在我们虽然弄清了坏人之所以是坏人的原因,脑袋清醒的时候恐怕所有人也都知道好坏二元对立是过于简单的判断,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我们要问,为什么人们要建立好坏二分的价值观呢?这,当然也是津巴多的问题。
在津巴多看来,这种好坏二分的价值观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世界。要知道,现实世界是很复杂的。我们小时候考试,做判断题,有对错两个选项;做选择题,大不了A,B,C,D,E五个选项。但现实世界可不得了,那是无数种可能、无数种选项,如果没有一种简化机制,人们要怎样面对,并且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世界分成好的和坏的。说白了,也就是分成“我要的”和“我不要的”。要的,就亲近;不要的,就远离。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并非出于恶意,我们往往还会本能地判定那些被我们认定为“坏人”的人,是“天性如此”,也就是无药可救。
而我们建立好坏二分的第二个心理机制,则是可以让“好人”——也就是我们自认为的自己,对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免责”。好人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还是以岳飞、秦桧为例,只要我们都认定秦桧是坏人,那么整个宋朝的覆灭,都和我们没有关系。直到今天,秦桧的塑像还跪在杭州的岳王庙。记得前几年有个雕塑家想要帮秦桧站起来,生生被社会舆论给压回去了。
除了这个问题,还有那些扮演囚犯的人,他们又不是真的犯法,为什么要甘于受压迫呢?不得不说,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里都有对权威的崇拜。说得好听点儿叫“服从”,说得难听点儿就叫“奴性”。为什么说这是我们的基因里的东西?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人类还是类人猿的时代,就是谁强硬谁说了算,谁要是敢不服从,那就弄死谁嘛。所以,有不服从基因的人,最早就被杀死了。那些只有服从基因或者能够假装自己有服从基因的人,才能存活下来。要知道,人类的这套“丛林法则”运转了成千上万年,这种对“反抗精神”的清洗持续下来,到现在沉淀下来的奴性是很自然的。反而是没有奴性的人会显得很古怪。所以,你说人要找寻内心的自由,难不难?
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世界观,建立日久,是很不容易转变过来的。但是,套用那句伪造的情诗的格式来说:你转变,或者不转变,世界的真相就是那样,不好不坏。好坏对立,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应该被颠覆掉的常识呢?而现在,终于可以回头说说为什么我们《原来酱紫》节目要提出“颠覆常识,寻找共识”的口号了。
共识为什么重要
话说有一次,我和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林毓生教授谈话。我问他,早年在美国求学时候的种种小故事如何如何。他告诉我,有次他去找一位老教授求教问题,人家老教授听完,连回答都不回答,直接问:“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这种时候,恐怕只要心智稍微不正常一点儿的人,立刻就会觉得一连串的受歧视感喷薄而出。可是,林毓生教授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你不回答就不回答呗,大不了我回宿舍自己思考就是了。很快,林教授就知道教授不回答他问题的缘由了。林教授对我说:“在美国的学院,很多共识的问题大家是不谈的。”林教授这话,那真叫醍醐灌顶,突然让我看懂了今天的现状。
我们随便打开网络看一看,恐怕从古至今,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声喧哗。就我的观察,无论什么热门话题一出来,很多人首先不是看立论推理过程什么的,而是直接看结论,分成左中右,比如只要一说美国好,那就是汉奸,然后吵得不可开交。每天,我们这个国家的人都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资源在这些无聊的争吵上。如果我们不这样,而是拧成一股绳,那该多好呢?所以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想办法,为这个社会把脉、开药方。
这几年,很多人都说社会缺乏常识。但你去看看网上网民的言论,就知道他们不是没有常识的。还记得前面那个对常识的定义吗?“一般人所应具备且能了解的知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具备了应该具备的知识,说白了,人们不是没有常识,而是各有各的常识。这些各自的常识早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甚至发展到“成见”的地步。你看看网上那些人,谁会妥协?我还记得,前不久浙江大学的苏振华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就说到,他上了这么多年网,最大的体会就是:自己没办法说服任何人,任何人也没办法说服自己。看完那篇文章,说实话,我都有点儿开始怀疑网络是不是公共空间。因为根据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公共空间里讨论问题,真理应该越辩越明才对。这时候,你会知道,常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需要常识,我们需要的正是林毓生教授口中的“共识”。我对“共识”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共同的常识”。只有我们放下成见,颠覆常识,获得共识的时候,才能坐下来好好聊天。
在过去,共识是很难建立的。权力至上的时代,只有掌权者灌输下来的共识,从来没有民间的共识。但《路西法效应》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环境一旦发生改变,人心就跟着改变。今天我们,遇到一个最好的时候,那就是网络技术出现了。过去许光头想要开一个电台节目,可想吧,谁会给我机会开节目呢?但网络一起来,像荔枝电台这样的软件出现,我们谁都有机会说话,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
说实话,《原来酱紫》这个节目能玩多久,要怎样玩下去,我完全没底。但我知道,这是个机会,不能白白浪费。传统的媒体形态,犹如春晚,春晚导演必须把一台晚会做得面面俱到,什么歌舞、相声、小品,小品有分给军人看的、给教师看的、给农民看的……这完全是一种“粗放型”的媒体模式,浪费大量资源。试问如果我不爱看小品,那你的这些节目对我来说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