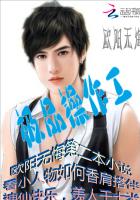“你是在怀疑我的动机呢,还是专业性呢?”我取过包,正好有张证书在包里,便拿出来放在她面前以示证明。
“呦,心理咨询师三级。”天真翻开我的证书,又看了看我的脸,补刀一句:“照片P的挺年轻的啊”
我强压着把她掐死的冲动,瞪了她一眼,回道:“我拍这照片的时候就你这么点大。”
天真讨饶道:“好了好了,不逗你玩了,你说的刘锦添和余深深我都认识,还很熟,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咯,至于回不回答,回答到什么份上我会酌情考虑的。”
“那好,先说说刘锦添吧。”刘锦添和丁凡的关系,是重中之重。
“诶,我还以为你会先问余深深呢。”天真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头朝天回忆了半晌,开始向我徐徐道来。
丁凡和刘锦添认识,大概是07年的8月,天真说,她们刚入院没多久,他也跟着入院了。其实那会儿,她和丁凡大学都还没毕业,(医科大学是5年制),不过她们医院是学院的附属医院,所谓的定向招生,最后一个学期她们已经开始见习了。
刘锦添不是医生,他是被救护车送进医院的,听说是从四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送他来的一帮人都穿着红衣服,带着绿帽子,绿帽子正前方印着‘国家电网’的标志。
至于他是怎么掉下来的,送他来的人都三缄其口,不过有人偷偷告诉天真,他是触电被从变压器平台上打下来的。
其实他伤的也不算重,就断了两根骨头,手臂上有些烧伤罢了。但他那些领导仿佛天塌下来似得,前三天一天来三波,拿来的水果和营养品够把他埋起来了。不过三天后也就没人来看他了,有的时候送饭的人都没有。
刘锦添这个人不爱说话,一整天躺在病床上看窗外的天,忧郁的仿佛担心天随时会塌下来似得。
天真给他查房的时候,他邻床的病人悄悄问天真:“天真,啊呸,金医生,那人是不是哑巴?哑巴也会偶尔放个屁啊,他一天到晚屁都不放一个,我看着他就觉得憋的慌,能给换个床位不?”
他这样说的时候,天真细细的观察着刘锦添,可能是那天她站的角度正好,在她的视野里,刘锦添和窗、病床、窗外的天空组成了一张比例绝佳的构图——一个忧郁堪比巴乔的男子,安静的躺在洁白的病床上,撑起一条腿,上着洁白石膏的手臂搭在膝盖上,脸四十五度看向窗外,黄灿灿的夕阳从窗外透进来,照着他的脸,仿佛给他的脸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天真的眼神在这幅美轮美奂的图上定格了好几秒,然后突然,刘锦添朝她转过脸来。
天真说,在刘锦添的脸转向她的那一刻,她仿佛看到了上帝朝她微笑!他的脸就像黑洞吸引光线那样吸引着天真的视线,直到他隔壁床的病人拉她的衣角她才清醒过来。
“喂,金医生,我刚跟你说话你听没听啊,我说我要换床位。”
“闭嘴,你就不能学人家安静点!”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朝那病人发火,当她看到那病人惊讶的张着嘴巴,瞪着她的时候,她心里乱成了一锅粥。她跌跌撞撞的退出病房,她说从没体验到那种感觉:头有点晕,心跳的频率仿佛有一种魔力,让她感觉自己能飘。
她一路如神游一般穿过走廊,回到办公室,医生都出去了,只有丁凡一个人在,她快步走到丁凡身后,拦腰抱住她,问到:“小丁,你有没有发现,2134-B床的病人,长得像上帝。”
丁凡愣了一会儿,反应过来哈哈大笑:“那个哑巴啊,他是蛮帅的,可惜是个闷葫芦,天真,你……不会看上他了吧?”
“我就觉得他很帅,我可没说喜欢他。这世上……帅的人海了去了。你了解我的,我要找男朋友,一定找比我还会聊的,要让我一辈子对着一个只能看不能用的洋娃娃,我不得憋死?”说这句话的时候,天真心里总感觉囧囧的。她眼神游移间,突然发现丁凡的桌子下面放着一大束花。
“哇,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又有小开送花来了?”天真不由分说的把花从丁凡桌子下面捧出来,翻开上面的卡片,喃喃的念了出来:“凡,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一千零一天,我送你一千零一朵玫瑰,代表我对你相思的一千零一个日夜,落款……爱慕你的鱼?那条鱼啊?开宝马那条还是开奔驰那条?”
“是开保时捷那条哦,余深深呢,你忘了,他还请我们吃过饭呢,你点了三个象拔蚌。”丁凡呵呵一笑。
天真一拍脑瓜,问道:“是他啊!又高又帅又有钱那个,你们怎么认识的啊?”
“我爸和他爸是朋友,我们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丁凡皱了皱眉头,嘟囔着嘴说:“这阵子,我妈一见我在家呆着就浑身不自在,我爸也在饭桌上老提起谁谁谁的儿子从哪里留学回来了,谁谁谁的儿子毕业在哪里工作了,我都烦死了。”
“丁院长这是关心你啊,你既是他的下属又是他的女儿,关心一下你的私生活也是应该啊。”天真讪笑道。
丁凡默默的摇了摇头,说:“我不想把自己给卖了,余深深是挺好的,但……没感觉就是没感觉,而且他对我是不是真心,我也不知道,他的确肯在我身上花钱,但钱恰恰是他最不缺的。”
天真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说:“我有个朋友嫁了个老公做生意的,也很有钱,但是结婚以后连个面都见不到……”
“所以我不喜欢嫁做商人妇。”丁凡斜了天真一眼,说:“嫁个每天不着家的还不如嫁个哑巴,你说是吧?”
“那时候,我们背后都叫刘锦添哑巴,他也名副其实的不说一句话,直到有一天……”天真顿了顿,喝了一口茶,大大的眼睛看向窗外,仿佛在缅怀着什么。
我给天真的茶杯里续上水,她才把眼神从窗外收回来,朝我笑笑:“我相信你是心理医生了,我说了那么多,你一句嘴都没插,要是我的话,肯定会被憋死。”
“你又不是我的病人,我只要听就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的故事精彩一些。”我耸耸肩道。
天真伸了个懒腰,把头靠在椅背上,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伤感,说:“好吧,好吧,我继续。”
天真说,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CD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强降雨,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倾盆大雨从深夜一直下到黎明还不停歇,那个天昏地暗,天真说她都怀疑太阳是不是再也升不起来了,或是被这雨浇灭了,被这风吹跑了。
“……江油盘江大桥被冲垮,拱桥一节一节往下垮……强降雨导致江安河漫堤,光华大道已在实施交通管制……”
她们正在值班室看着新闻里外面水天泽国一般的情景,突然屏幕闪了一下,没了画面,办公室外走廊里的灯也全熄灭了,周围一下子暗了下来,暗到她们只能看见面面相觑的对方的脸。
“停电了?”丁凡看了看周围,若有所悟的说了句。
“世界末日提前了?”天真狐疑的看了看窗外阴云密布的天空。
“诶呦!这可怎么办呀!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断电呀!”一声沧厉的喊叫仿佛乌鸦为这暗无天日哀啼。丁凡和天真循声看去,就见何秀珠——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拎着电话筒,气势汹汹的喊着:
“设备科吗?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给我断电呢?有急诊病人等着开刀呢!……啊?妇产科有两孕妇都已经推进去了?没电不敢剪?你们看看,看看,这电停的让我们医生多被动啊!……不是我们设备啊?是电力局的线路被树枝刮断了啊?那要多久能来电啊?……两个小时!路被水淹了?哦我的天啊,等开刀的病人骨头还在体外那,你跟他去说,让他等两小时!”何秀珠气呼呼的把话筒摁在电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