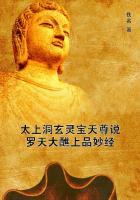短暂的兴奋过后,我逐渐平静下来。俗话说无功不受禄,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做事讲原则。
一百万,确实很有诱惑力,我可以用它买本来舍不得买的设备,也可以用它扩大诊所的规模,光这笔定金,就起码可以让我少奋斗三年。
但扪心自问,我有没有治好那个女人的把握?可笑的是我连她的症状都还没弄清楚,更遑论余深深说的,要摘取掉她脑子里的一段记忆,这是我入行以来听到过最离谱的要求了。
记忆又不是盲肠,怎么摘啊?
既然没有治好她的把握,怎么能要这么多定金呢?这不符合我做为一位医生的原则!为了这个,我辗转反侧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我做出了我这一生最艰难的决定。我决定——改动一下我的原则。当然,我绝不是心安理得随便改的,我发誓我会对这个case格外上心,即便不能把那个女人治好,也要让余深深切实的感受到我的用心,让他觉得这一百万物超所值。
心理治疗和生理治疗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延展性。生理病症再复杂,病灶总是在病人身上,但心理病症的症结,大多是一种经历,是一种感情压抑太久得不到宣泄。
西医发展了几百年,建立了一套针对生理疾病的完整体系,而他们渴望在心理领域复制生理领域这一成功经验,也建立一套诊断——开药——输液——手术——化疗——临终关怀的完美送终体系。
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当年额叶摘除手术(切除三分之一的大脑,因过于残忍现已消声灭迹)和电击疗法制造了无数行尸走肉,却依旧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甚至额叶切除手术的创始人还得过诺贝尔医学奖。
而现在的药物治疗,在我看来依旧是治标不治本,不用怀疑,大多数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成分是血清素,也就是五羟色氨,说穿了就是兴奋剂,还不如直接吸大麻,效果好多了。
心理治疗最理想化的手段,还真让余深深说中了,就是让患者失去一部分不好的记忆,(但绝不是失去脑子),可惜现代科学达不到。
退而求其次,我个人认为效果最好,也是最实际的,是催眠,特别是深度催眠,通过数次深度催眠,潜移默化的通过潜意识引导,去改动患者的记忆和印象,淡化压抑的情感,是最标本兼治的治疗手段。
但深度催眠要求极高,不仅是催眠师的水平得很高超,干预师也要非常专业,并且对患者的记忆必须十万分的了解,所以这是种十分注重个体差异性的治疗手段。
注重个体差异性就和现代医学系统化的理论相驳,所以这种治疗手段注定无法全面推广,显然医生不是警察,不可能去调查每一个患者的人生轨迹。
当时我想,事已至此,不该答应的也答应了,捏在手上的钱送回去实在太难受,思来想去,也唯有对那女人尝试深度催眠,才能对得起余深深的一百万了。
虽然一晚上几乎没睡,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强撑着眼皮起床了。做深度催眠需要对患者的痛苦经历非常熟悉,熟悉到感同身受的地步,而我现在对我的患者几乎一无所知,这显然不行,我必须抓紧时间去了解丁凡。
我通过震后心理干预建立起的微薄人脉,辗转了解到,丁凡震前在CD某医院工作过,她在那里有个朋友姓金,据说关系还蛮好的,我要到了金医生的电话,试着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是丁凡的心理医生,想向她侧面了解下丁凡在震前的情况。
“小丁怎么了?都几年了,我都联系不到她,正为她担心呢。”金医生挺热情的,一口就答应午休的时候抽空和我见面,我顺水推舟的邀请她共进午餐,她欣然应邀。
电话里听金医生的声音有些低沉,一口一个小丁叫的顺溜,那口气即便不是领导,我猜想也该是个长者,所以那天我恭恭敬敬的等在岷江饭店门口。
没想到一个目测二十六七岁的小个子女孩走过来啪一下拍我肩膀,瞪着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问:“你就是胡医生吧,我是金晓丽。”
“你……就是金医生?”我诧异的看着眼前这个小个子女生,她穿着一套阿迪达斯的运动服,扎了个马尾辫,脸蛋有点婴儿肥,眼睛大的跟核桃似的,跟她细小精致的鼻子嘴巴极不协调。
“是啊,我就是小丁的朋友,刚才是你打电话要请我吃饭吧?”她一脸萌呆的望着我。
我挠了挠头,说:“等会儿,你说的小丁是丁凡?我觉得她岁数应该比你大吧。”
“是啊。比我大一岁。”她理所当然的回答道:“我们单位的人都这么叫她,所以我也跟着叫她小丁了。”
“那你们单位的人怎么称呼你的?”我讪笑了下,问道。
“金医生。”她这样说的时候,眼神有些飘忽,我一看就知道她在说谎。
我把她请进饭店,谈正事之前先一顿好饭好菜伺候,熟络熟络感情。不过跟她聊了一会儿后,我发现这顿饭算是白请了,她根本就是个自然熟,我怀疑随便搭个讪都能熟。
还没上几个菜呢,他就老胡老胡的叫开了。
“老胡啊,小丁可是根难啃的骨头啊,不瞒你说,当年她在我们院里,那可是抢手货,号称妇科谢霆锋的谢帅,号称骨科陈冠希的陈酷见到她那也是两眼发直,更别说还有开宝马的小开……”
“打住,打住。我什么时候说我想泡她了。”我斜了她一眼。
“你不想泡她啊?那你给我献什么殷勤?不会是想泡我吧?”她睁大眼睛一脸防备的瞪着我,双手做捂胸状。
“天真。”我无语的摇摇头。
“诶。”她下意识的诶了一声,然后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在叫她,整张脸都不好了。我见她的反应,立马反应过来,哑然失笑道:“原来人家都叫你‘天真’啊,真是个雅号呦。”
“老胡你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取笑我吧,那些都是俗人,不懂我灵魂深处的成熟,你是心理医生,你应该懂我的。”天真幽怨的看着我,活像我以前养过的一只博美小狗,从头到脚都像极了。
我不置可否的笑笑,对她说,还是谈谈丁凡吧,问她:“你和丁凡认识很长时间了么?”
“她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我们是同一届进院的,见习跟的是同一个医生,除了睡觉和上厕所不在一起,其他时间她都粘着我,甩都甩不掉。”天真甩了甩手,露出鄙夷的眼神,但鄙夷的目光又有些游离,让我感觉这话可信度不高,如果主宾语调换一下,可信度就高了。
“她性格怎么样?跟你一样大大咧咧的,还是比较内向。”我接着问道。
天真大眼睛转了一圈,说:“要看对谁咯,就我们俩的时候她就是个疯婆子,有外人的时候她就是个端庄的淑女,见男朋友的时候呢,就是小鸟依人的样子了。”
我点点头,接着问:“她男朋友是谁啊?余深深还是刘锦添?”
天真白了我一眼,满脸坏笑的说:“哇,老胡,你对她研究还挺深入的啊,心理治疗需要知道那么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