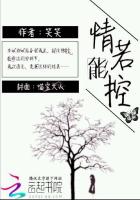“大人,坊间传闻已经认定赵常发就是凶手,无论如何也该把此人正法才是。”巩师爷这句话,纯粹是废话。上百号人看到了冤魂认凶的戏码,当天在场的人就被震撼到了。如今经这百十来张嘴传播,整个冀州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巨大的舆论下,杀了赵常发可谓人心所向。
奈何通判大人断案被舆论左右,那置官府颜面何在?更别说福王爷已经重视此案,总要给他老人家一个交代。(老人家是尊称,福王今年才三十多)
现在福王爷重视的是案件,并不是重视潘长河这个官。若潘长河草草把赵常发杀了,哪里能体现出潘大人的精明才智?当然,潘大人为官多年,深知在这个事情上是不能抖机灵的。越是上头有人盯着,越应该按来,才好显出他潘大人为官清正,不是拍马溜须昏庸之辈。
福王爷只说了关注案情,并没有具体嘱咐他怎么做。若是福王爷交待下来的事情,潘长河那必然是肝脑涂地。到那时,福王爷也要把潘大人视为心腹了。以后有福王爷罩着,他潘大人可说仕途无忧了。
奈何此案如今尽人皆知,不知道多少人在关注,又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潘大人不循规蹈矩查案,也不行啊。
按规矩办案本是通判的责任所在,难就难在西门小侯爷整的这出“鬼魂伸冤”。怕就怕明日西门小侯爷不能提出有利证据。到那时赵志常鬼魂不见踪影,难不成还要查他西门庆栽赃陷害么。
想到这里,潘大人也是眉头紧皱。他抿了一口茶水说道:“我自然知道此案已是万众瞩目。可越是如此,越不能草草结案啊。”接着潘大人把自己的顾虑说给巩师爷听。巩师爷听罢也皱起了眉头。
“大人所虑极是,是学生考虑不周。如此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议才是啊。”
“巩师爷。”
“学生在,大人有何差遣?”
“这破案关键,依本官看还要落在西门小侯爷身上。劳烦师爷这就去侯府走一趟,一来询问小侯爷身体如何,明日能否出庭作证。二来问明小侯爷手里可有什么证据,又或者那鬼魂赵公子有什么特别交代。总之一切对破案有利的线索,还望师爷仔细询问。明日公审才不至于出什么差错啊。”
“是,学生领命。那学生这就走往侯府一趟,学生告辞。”
潘大人刚打发走师爷,还没一盏茶的功夫,突然听见府衙外有人鸣冤击鼓。大人急忙整理衣冠,来到前院大堂上。不一会儿,差人领着一中年妇人来到公堂。
那妇人四十上下,看模样只是寻常百姓。潘大人只道是一般案件,不由得勃然大怒。
“大胆愚妇,你可知本府主管真定一府狱讼听断之事。你有何冤屈也该去长治县、平安县申诉。为何越衙上告?”
原来真定府下有长治、平安两县。喊冤也要既定依照程序来,先去长治、平安两县县衙。长治、平安两县典史若是不受理或者审判不明,才可上真定府府衙告状。潘大人主抓真定府刑名狱讼,没听说长治、平安两县最近有什么案件审判不明,需要他这个州官出面摆平的。
潘大人不禁心里纳闷儿,最近真是乱了套了,意外事件成了杀人案,偏偏还搅得满城风雨,世人只道是他潘大人遇事不明。现在又有大胆愚妇人,直接来府衙上告。这一个个的拿我真定府通判当什么了?敢情潘大人余怒未消,见这妇人跪在堂前口中只喊冤枉,手中却无状纸,不禁更恼了几分。
(本文为历史架空小说,请各位不要与现实及历史对号入座。真定府是有的,就是现在河北正定。但长治县和平安县是本人杜撰。因为“真定”离不开长治和久安嘛。本书中大半都是作者自开脑洞胡诌的,如有人喜欢那就最好不过了,但请不要较真。其他胡诌的内容不再多加赘述,各位看官只要看的开心就好。)
“来人啊,给这妇人乱棍打将出去。”
“大人,民妇孩儿赵常发现被关在真定府大牢里。民妇这才来府衙上告。”那妇人一边磕头一边接着道:“大人,我儿冤枉啊。我不信我儿能杀了赵家公子。故来此只为喊冤,不曾带诉状。若老大人能还我儿清白,您就是打死我,民妇也心甘情愿啊,大人。”
原来这是赵常发的生母赵田氏。
赵常发是遗腹子,从小只与母亲田氏艰难度日。后来母子沦落冀州,是赵家老爷收留了她母子二人。
赵常发当时还小,就做了赵家少爷的书童伴当。田氏在赵家做些缝补营生,赵家老爷素来待家仆员工不薄。她母子余生也算有了着落。
可谁想到,赵家公子落水身亡,自己儿子无缘无故被当成犯人抓了起来。虽然赵家上下忙着安置棺木,重新布置灵堂,一时也没顾不上她。可她知道,这赵家她是待不下去了。等赵家管家再去寻她已经不见了她的踪影。
田氏自觉儿子不会杀人,又觉在赵家不能呆不下去了。可她一个妇道人家哪有什么好办法。离了赵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田氏只觉天大地大,却没有自己容身之处。加上她听街上风言风语,也认为儿子这次是必死无疑。田氏只觉得天都要塌了,自己也不该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一个妇人哭哭啼啼走了一路,路人多是好奇却鲜有问原因的。也有熟人认出她是赵常发母亲,也知道她是有了死意,便远远的躲开了。如此田氏一路走到河边,投身碧波也就没后来越衙上告什么事儿了。可她偏偏遇到了一个人,吴是非。
吴是非乃冀州城一流氓无赖,以坑蒙拐骗偷为生。最高兴别人家有个红白喜事,他能趁机混进去吃喝一顿。今日本来去赵府打秋风,却因为他在席间偷人东西被发现,遂被一伙人团团围住。吴是非还没吃上几口热食,偷的东西却被失主要回。众人都知道他是惯犯,趁搜身的功夫,硬是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也抢了去了,这才把他赶出来。
却说吴是非被赶出赵府,却是腹中空空。他在冀州城四处晃荡,也没找到什么吃的。等傍晚时分,才悠悠然来到河边,只盼着能捞些鱼虾充饥。正这时候,他听到有人哭泣,四处一打量,就看到来河边寻死的田氏。“那边大嫂子可是来上吊的?”
“我要有绳子上吊,还特意跑河边做什么。”
“那是我唐突了,就是不知大嫂你身上可有什么值钱东西。我腹中饥饿,反正你也要死了,不如临死前做做好事,都给了我罢。俗话说穷不帮穷谁帮穷,看在我俩都是苦命人的份儿上。您就可怜可怜我把。唉,你别走啊。”
田氏一心想死,哪有时间跟他打牙祭。
“本来你死了,东西也能给我。奈何你不是去上吊,是去投河。你一介女流,跳了河里我也不好再去打捞啊。你还是行行好,就把头上的那簪子给我吧。”吴是非倒是好算计,死人的家当他也惦记啊。这小子要没偷过祭祀的供品,那是任谁都不信的。
田氏烦他聒噪,没多想就把头上的簪子给他了。
“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吴是非得了簪子却不肯走,只见他接着道:“大嫂你死意已决,我也不好再劝什么。可我收了你的簪子,也该为你做点什么。你若上吊,我把这簪子换了钱,吃过饭后还回这里,一定把你好好掩埋,也免得你尸首被野狗毁去。可你执意跳河,这簪子的钱却怕是不够打捞费啊。要知道,最近漕帮有号称【职业打捞人】的,那打捞费可是天价啊。”吴是非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田氏也不理他,只顾往水里走去。
“大嫂,你为何要死,总该和我说两句吧。我既然收了你的簪子,总不能连你是谁为何要死都不知道吧。”吴是非眼看田氏身边的水已经没过小腿,河岸不比平地,很可能田氏再往前走一步就整个人掉进水里了。
“这位小兄弟,老妇人承你的情,谢你关心。但我身上的事,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既然你有心相问,我是赵常发之母。我儿常发现在身在死囚牢,不日就要身死。我一个妇道人家,只能眼睁睁看着,没半点法子。想来是老天爷要亡我母子二人,我还是死了算了。”
“慢着,你怎么知道你儿子一定会死?”
田氏怪异地看着吴是非,她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这么说啊。坊间热议的就是赵公子死的如何冤枉,赵老爷中年丧子如何凄惨。那赵常发是罪大恶极,是死定了。却没人想,赵公子是儿子,她儿子难道就不是儿子了。赵老爷中年丧子,她就不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么?
“你说什么?你有办法救我儿子?”田氏终于动容,两三步就窜回了河岸,紧紧抓住吴是非双手,狠狠攥住。
“大嫂,大嫂,你松手,攥疼了啊。”吴是非一阵子瓷牙咧嘴:“也不一定真能救了你儿子,只是我想不明白一点,你可去府衙问明。想来你也不信自己儿子会杀人,难道你就真做个糊涂鬼么?”
田氏一听这话,大失所望。死的不明不白和死的明明白白,到底哪个更好些?反正都是死路一条,明不明白很重要么?可让她再回身跳河,她却是不愿意了。人一旦萌生一丁点生的希望,那是万万再不愿意死的。
吴是非却怕她又要寻死,继续说道:“何况你死了,我还能想办法将你安葬。你儿子死了,却是谁安葬呢?你至少也要等确定他有罪了,再寻死不迟啊。”
田氏终于被他说动,又急忙问他,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吴是非巧舌如簧,鼓动田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田氏要寻死没死成,这才让本来明朗的案子,又起波折。市井间不知又要传出什么闲话来,可大家都乐的见事情有些转折,才好有新的谈资,配酒下饭那也是极好的。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