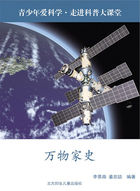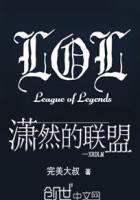当初他在广州营生,有一个叫陈树生的人,常来照顾他的生意,也特别爱喝他煲的蛇羹,说他是原汁原味,增一分则太重,减一分则太轻。两人在这蛇羹上就有说不完的话,由此渐成老友。那陈树生则每周必来光顾他。
那陈树生乃是当地教书的中学老师,身材瘦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平时不大爱说话。戴一副黑边框眼睛,眼睛却精光透露,难为他还是有些近视。他为人诚恳,亲切,休闲时间,最喜欢漫步溜达,寻一些地道美味来品尝,也常写些文章或诗词来抒发情感,这也难为他是教数学的老师。但更让他难为的事,也许除了陈树生自己,外人中就只有王贵业知道。
这陈树生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却有一样是美中不足,年届四旬,却膝下无子,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弄子之福。
他这一样,却不肯轻易对他人说。这个中原因,只有他和老婆黄梅知道,再有就是这外人王贵业。他们夫妻不能生育,原因不在黄梅,而在陈树生。陈树生笃信中医,专门去看中医,中医给他的结论是“肾水亏而至血精不足”,用西医的话说,就是精子质量不好,难以受孕。这病却没有十分把握能够治好,他又不能接受西医取精受孕方法,就这么拖着。
但中医告诉他,可以常喝蛇羹,以调理身体,说不定可以有些奇迹出现。正是因为此,他才有了这个嗜好。也正因为这个嗜好,他才能跟王贵业聊得起来。
王贵业了解他的心思,也了解他这么多年,颇有积蓄,便有意要从他那里得财。一天瞎聊,他就有意试探陈树生,说,要是我从乡下给你带一个孩子来,你要不要?
陈树生看了他一眼,却说,违法的我可不要。
王贵业说,哪能?我也是本分人。
陈树生笑了,说,那行,不过得聪明点的孩子,最好是男孩啊。
王贵业心里笑了,脸上却严肃,信誓旦旦地说,包在我身上了。
虽然包在他身上,但王贵业当时也没有什么招数。他什么时候回去也还不知道。但也许因为这个诺言,半年后,他就开始犯病不能再弄蛇,这才动了回冀村的念头。
他回乡下,陈树生不可能不知道,也赶来给他送行,说了很多感情深的话,临了,又说起“包在我身上”那档子事,又说,不会让你白辛苦。
王贵业当时就拍桌子说,你不相信我。说包我身上了,就是包我身上了,不出半年我就给找个来。
陈树生见他急眼了,赶紧说,哪能不信,哪能不信。
王贵业回到冀村,就发现了郑有信,觉得能够实现他“包在我身上”这句话的,就只能是郑有信了。这才格外与郑有信亲近,就是让郑有信对他不再抱有戒心。
那天早上,见到郑有信跟他爷爷一同去赶集,他就觉得是个机会。那集上人山人海,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果不然,毫无察觉地把郑有信偷跑了。当然还多亏了那化了安眠药的酸溜溜。
他抱了郑有信,搭了一件衣服在郑有信头上,才绕圈去了市里,搭上火车,一路奔广州而来。
下了火车,他没有直接去找陈树生,而是先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来,让郑有信过一过药劲。告诉他,这是因为有事,顺带着带他出来玩,又说,这跟他爷爷说了,都巴不得你出来玩一玩。又说,之所以不带王小剑,是因为他不听话,老是尿床。王贵业跟他胡诌一顿,倒也让他信了。王贵业这才带他去陈树生家。
陈树生和黄梅看到郑有信,十分喜欢他。这孩子生的白净,不像是从乡下来的,除了那脖子上的泥垢。说话也清凉,虽然有些听不懂。
郑有信看眼前两人,只是有些怯怯的,但接过了不知名的水果,吃起来甜甜的,却也渐渐放开了,与陈树生和黄梅也熟起来,开始满屋子跑着看。
黄梅领着郑有信去另外一个屋子,这个屋里倒是摆满了各种玩具,有枪,有车。黄梅就带着他玩,虽然彼此听不太懂,但也沟通的不错。
在外面,王贵业就小声跟陈树生说这个孩子的来历,说他家里遭难,父亡母嫁,对方家里容不得这个孩子,才让王贵业带出来送人,希望他有个好人家可以长大,免得受罪。
陈树生听了嗟吁不已,又是说王贵业做了一件善事,又感谢王贵业帮了他的忙。于是从里屋拿出来两千元钱,递给王贵业,说这是给孩子亲生母亲的,希望她见钱后不要在记得这个孩子,又递了五百给王贵业,感谢他没有忘记前事,是个守诺言的人,也不能让他辛苦。王贵业喜笑颜开。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那黄梅走出来,说孩子玩累了,睡着了。王贵业见此,就说,那我赶紧回去了,免得他见了我又要跟我走。
陈树生夫妻把他一直送到门口,挥手作别。
郑有信在陈树生家里睡着了,等他醒来,天已经黑了。揉了揉朦松的眼,还下意识地喊爸爸妈妈,只不过跑过来的不是郑碧坛和秦,也不是他爷爷,而是陈树生和黄梅。
见到陈树生和黄梅,他又想来王贵业,是跟了王贵业才到了这地方。他便喊叔,但也没见王贵业出现,就只有陈树生和黄梅抓着他叽歪地说着听不懂的话。
他感觉到情况不妙,他被孤零零地扔在这儿,内心的恐惧油然而生。他挣脱陈树生和黃梅对他束缚,又像是逃避那听不懂的说话声音,在房间里四处游走,喊叫。找遍了所有的屋子,只有他和两个不太熟悉的人,他感觉到孤单。他哭了,大声地哭了。
陈树生和黄梅谁也没有经历过这样阵场,以前想过的千万种应对策略和方法,万千种甜言和蜜语,此刻都无力的很。
那郑有信也只是哭,哭得房子都响了,后来,他的嗓子就哑了,成了抽搐,那眼泪早已经不再从眼晴里流出。他如此这般,可真是吓坏了陈树生夫妇。但是,他们也束手无策,哄得整个人都心力交萃,却又不敢离开。三个人就在屋里,和那满屋的火车,机枪玩具一起坐着,只有郑有信在抽搐着沙哑地哭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际树生和黄梅早已经停了各种哄骗,席地而坐在地上发愁,那郑有信也坐在地上,虽然仍在抽搐地哭,但声音却小了很多。黃梅细看,心里禁不住一松,推了推旁边的陈树生,朝郑有信努了努嘴。陈树生禁不住笑了,黄梅却一把捂住他的嘴,没让他出声。两人相视一下,黄梅轻轻爬过去,把一条毛巾被盖在郑有信身上。
两人蹑手蹑脚走出来,那紧绷的身心稍微有些放松。这天早已黑了,已是十一点多了。两人都无气力再做饭吃,只得胡乱吃了白饭,锁好门窗,才去睡觉。
陈树生和黄梅虽然睡下,但也不敢深睡,还不时听着动静。时睡时醒,时醒时睡。这广州本是昼长夜短,眼见的天也才就放光了,两人才深深一睡,却又被叽哩咣荡的声音惊醒了。两人赶紧跑出看,那郑有信不仅在地上小便,更把各种玩具乱摔一气,此时见陈树生和黄梅来了,更是摔得起劲,喊着,我要回家。
两人见此光景,不由得哭笑不得。陈树生说,他精力十足,这是拿劲耍刁,不用理他,他觉得没什么意思,自然就不闹了。
果不出所料,郑有信闹了几个钟头就不再闹了。下午却耍起门来,不停地脚踢身撞,咣咣地响。陈树生夫妻却不再搭理他,任凭他制造声音,却不许他出那个房间。
要说没有担心,那是假的。自打昨天到了,到现在,郑有信还滴水未进,滴米未吃,一个六岁的孩童,身体如何承受得了。
果不然,到了晚上,郑有信就摊倒在地,浑身发烫。黄梅急得都哭了,一个劲埋怨陈树生。陈树生要抱了孩子去医院,黄梅拉住他,说现在怎么能够去医院,要是他又闹起来,不就把事情泄露了吗?!
陈树生听了这话,才恍然大悟,赶紧跑到楼下,找到老中医陈元彪。
陈元彪来后,看了孩子说,这是急火攻心,不能用猛,还是先退烧吧。于是开了一副药,又让陈树生跟他下楼,去药店买了医用酒精,擦给孩子,降降体温。
两人折腾到半夜,孩子的体温也没有降下来,再一量体温,都升到40了。
黄梅是真急了,也不跟陈树生商量,抱了孩子就奔医院去。陈树生就在后面跟着跑,还喊道,慢着点。
到了医院,进了急诊室,两人就在外面坐着,黄梅就哭,说,要是孩子有什么不测,这不是作孽?
陈树生心里也是后悔不已,但是说的,谁能想到孩子有这么大的气性?
两人提心吊胆到天明,老天也终归没有给他们作孽的机会。郑有信的体温总算是降下来。但医生说,还不能出院,因为高烧,也并发了肺炎,还需要住院治疗。两人对天,千恩万谢。
此后,为了照顾郑有信,黄梅暂时向单位告了假,专心在医院照顾郑有信。那陈树生一下课,就直奔医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