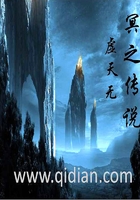哪知武照将军却问她“如果以后你反悔怎么办?”
哎,是赞他有勇有谋好呢还是骂他性多疑好呢?何花拍拍胸脯,十分仗义的说:“您放心好啦,我虽是小女子,也能做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用我的人品向你保证,绝不反悔。”
这样一个质量上乘的师父摆在眼前,她还反悔,傻啊。
他显然并不相信她的人品,“口说无凭,立字为据,颜城,笔纸拿来。”
他身后一个书生打扮的斯文青年男子立刻从怀里掏出笔一只,纸一张。
口,连笔纸都事先准备好了,这是要写拜师贴呀?看来这样的事他以前没少干,难道这武照将军跟南海鳄神岳老三一样有强迫人做徒弟的嗜好,没事就到街上物色徒儿?
如今的城阳县住的都是什么牛鬼蛇神啊,几年不见,变化大得令她有点应接不暇。
叫颜城的青年很礼貌的问她:“请问姑娘芳名,家住何处?”
这句话听着很熟悉,似乎谁说过,对了,那只旱鸭子今天早上就问过她同样的话,想起他“别(恋)有(恋)居(不)心(舍)”的眼神,何花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但事已至此,只有硬着头皮说了:“何花,家住水莲村。”
颜城蹲在地上以腿作案,提笔刷刷刷飞快地写着,很快就写好了,他拿着笔纸走到何花身边:“好了,姑娘只需按个手印,契约就成了。”
何花凑上去,想看看他到底写了什么,哪知他动作奇快,只来得及看清“永不背弃诺言”几个字,大拇指就被他捏着在毛笔上一蹭,白纸上印下一枚黑黑的指印。
“有必要弄得这样隆重?”拜个师而已,搞得这么神秘诡异,何花几乎有一种签了卖身契的错觉(事实上这次真不是错觉)。
“必须隆重,还有比这更隆重的。”
武照将军笑得春风得意,何花也跟着笑,师徒关系嘛,师唱徒随,师父笑,徒弟自然效仿,虽然不知道到底哪里好笑。
“那就这样定了,我会选个良辰吉日到水莲村亲自迎娶你。”
何花简直受宠若惊,心里十分甜蜜高兴,面上却做出一副中国好徒弟的谦逊模样,连连摆手:“使不得使不得,既然是拜师,当然是做徒儿的去拜见师父,哪有师父亲自去水莲村拜……你刚刚说什么?”
她瞪大眼睛,差点失声尖叫,“你刚刚说去水莲村做什么?”
“迎娶你啊,有什么问题?”武照将军剑眉一挑。
“不对不对,拜师怎么忽然就变成迎娶了,一定是哪里弄错了。”何花忽然想起什么,惊恐地看着他,“你说的小六,到底是什么?”
正在折卖身契的颜城笑着给了她准确答案:“我家老爷说的小六,就是‘六夫人’”。
“所以刚刚那张纸,其实真的是卖身契,并不是什么拜师贴?”她这次没有装,是真的快要哭了,她怎么就忘了他最大的嗜好——好色如命呢?
武照将军从颜城手里拿过纸,在她眼前慢慢展开,让她看清楚上面的字迹:
“小女子何花今日有难,幸得武照将军张廷松相救,作为报答,我自愿以身相许,嫁与张廷松做六夫人,特立此据为证,永不背弃诺言。”
落款“何花”二字,旁边印了一坨黑乎乎的手印。
何花感觉自己像某个QQ表情,整张脸慢慢裂掉,最后连眼珠子都掉了下来。
稍稍冷静下来,她开始仔细回忆整件事情的经过,到底是如何把自己卖出去而不自知的?
想起来了!他说做他的小六,她先入为主的认为是第六个徒弟,他说“可以这么理解,做了我的小六,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我学功夫。”
也就是说,六夫人一样可以跟他学功夫,而并非只有徒弟才能学。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说过小六不是夫人,也没承认小六就是徒弟。
他偷梁换柱,利用她的先入为主让她掉进圈套。
不是说打仗的人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这厮怎么就如此火星另类,如此阴险狡诈,如此老奸巨猾?
哎,不是自己太弱,而是对方太厉害啊。
等何花反应过来想要抢回卖身契的时候,张廷松已经将她的卖身契折好放进怀里。
“是谁说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反悔的?”他剑眉更加飞扬,双眸灼灼生辉,真正像刚从战场上凯旋的将军,带着胜利之后的极大喜悦,对她说:“记住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会选个良辰吉日,亲自上门迎娶你。”
其实何花想大声说:“那张契约带着欺骗误导和隐瞒引诱的成分,显失公允,是无效合同。”可是她知道这时候的法律并没有那么严谨,即使上了公堂,她也赢不了这场斗争,更何况,当事人张廷松已经走了,只剩下她一人在风中凌乱。
那些在看官和卖柴人之间自由随意转换身份的人们又退到柴堆后面,继续等着少得可怜的顾客临幸他们的柴火,热闹的柴街又恢复了之前的冷清。
何花觉得有些虚脱,她要去买本黄历,看看最近的良辰吉日到底是哪一天,天晓得,她从没哪一刻像现在这样,希望整年整月一年十年都没有一天良辰吉日。
她活了两世,曾在二十一世纪生活过,已经习惯了一夫一妻的观念,习惯了男女各顶半天边的平等,期待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所以即使失去父亲,失去兄长,失去竹马,她一个人依然坚强而独立地活着。
她不要像其他女子一样,要么靠着丰厚的家底嫁给男人做原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亲热那些莺莺燕燕却冷落自己,要么靠着几分姿色做人妾室委曲求全曲意逢迎乞求男人的垂怜过活,也不要一辈子做丫鬟等着男主人兴趣来了就临幸一下兴趣失了就弃之若履。
所以在她眼里,威风凛凛的武照将军跟轻佻无礼的徐大少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两者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同而已。
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做谁的小六小七,更何况,她一直等着魏子清,想起他温和如水的目光,心里一暖,之前的不快和委屈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今天注定不是卖柴的好日子,她决定先去买本黄历,然后打道回府,她需要好好治疗一下受伤的身心。
当然,临走之前,不忘带上那两捆不离不弃的柴火。
就在何花挑着柴满大街寻找黄历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熟人”。
一身青衫裹着硕长的身体,简直称得上体态风流,清俊雅致的脸充满书生气息,双眸深沉似海,目光穿梭在熙攘的人群中,似乎在寻找什么人。
那张脸美则美矣,却让人觉得讨厌,何花下意识皱了下眉。
他的目光随意扫过人群之中的何花,又看向别处,蓦地又转回到她脸上,眼睛攸然一亮,快步朝她走来。
坦白的说,何花十分反感这人,潜意识里,今天所有倒霉事都是因为他。所以她快速蹲在一个书摊前,放下肩头柴火,低头去寻找承载她后半生幸福生活的黄历。
“姑娘,买什么书呢?”老板问。
“有没有黄历?”
老板递过来一本黄得冒烟儿的黄历,何花一把抓过来,伸手去掏钱,猛地想起自己根本没有带钱,她讪讪地笑一下,“我忘了带钱了。”
原本脸上带着热络笑容的老板瞬间垮脸:“没钱还买,大冬天的摆地摊容易吗我?把黄历还给我。”说完伸手过来抢。
何花使劲握着黄历的另一头不放,她也是被徐大少和张廷松气昏头了,早想起没带钱,还买什么黄历啊,假装买书,看看黄历上最近的良辰吉日是什么时候,再装着没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潇洒离开不就得了?干嘛非要买呢?
“给我看一眼,就一眼。”何花急忙央求。
“不行!我这书是拿来卖的,不是让人看的。”
就在两人争夺不下时,斜里伸出一只五指修长的手,手心躺着几个铜板,“这本黄历我买了。”
顺着这只手望上去,何花头仰到九十度,看见那张清俊雅致充满书生气的脸,面无表情地对老板说:“这些钱够吗?”
老板一下松开死死握住黄历的手,去拿杨濂手中的钱:“够了够了。”
猛然失去争夺对手的何花因为力道的关系往后一仰,差点跌到地上,幸好被后面的人一把扶住。
借着那人的力道站起来,何花一把甩开他的手:“多谢,不过您可能多此一举了,凭我的身手,怎么会摔倒,即使摔倒,我自己也能起来,不劳烦杨大人费神。”
真不能怪她不懂礼貌恩将仇报,说起来,今天一连串倒霉事都是他间接引起的,尤其想到刚刚被张廷松卖了还对他感激涕零,她就对无事献殷勤的人十分反感,所谓吃一堑长一智,防火防盗防男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身后人嗤笑一声,何花转过身去瞪他,意外地看见杨濂身边站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少年,那声嗤笑,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