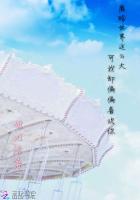妈已经很少来电话了。姐姐更是不曾,我和老三自爸走后就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夏天一到,又放了暑假。
我是最怕放假的,总想着要是能在学校里呆一辈子就好了。这样的话陡然不可能实现,但最起码呆在学校里的那五天不用干活,不用那么累,也没有头顶着太阳那样热。
暑假往后生活变得以田为中心,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我在田地里最深刻的感受,每天下田回来,去前面的鱼塘洗衣服,洗完衣服烧锅,吃晚饭休息到一两点钟再下田。
总也干不完的活,拔完麦茬开始除草,除完草一看棉花长的差不多了,又要施肥,施完肥又开始逮虫,还有四亩地的大豆玉米花生都等着施肥,除草。
有的时候奶奶打农药,我去井里打水。这一系列过后,还要给棉花松土。做这些事,并没有引起我的反感。相反地,我思念爸妈的情绪在田里会冲减下许多,仿佛自己也再也多余力气去想这件事,甚至在身旁的老三我都很少注意。
我拿着犁子步行下田。这犁子和许多的农用具一样完全是铁的,有锋利面,很长的铁架子。因为自己的个子在大人群里算是最矮的。不高自然拉犁子很矮,犁刀入土很深就变得非常沉,沉也要一列一列的拉完,手上虽然不会磨出新水泡,手掌十分的疼。
到了七月下旬一天,乌云滚滚而来,顷刻间闪电劈着天,大风呼啸着,雷声声震耳,雨豆落在地上“砰砰”直响,不一会儿雨帘哗哗啦的从远处赶来,只是转过身再往院子里瞅,已经开始积水了。
这样的大雨一连下了几天都没有停歇,有的时候虽然小一点,但地上的雨还没有浸到土里去又开始和其他的雨水溢在一起。
半夜的时候,雷声“咔嚓”一声把人从睡眠里惊醒,第二天早上看到前方的树被雷劈成了两半,不压到电线算好的,有的时候压到电线,一整个村庄里用不到电,蜡烛变得紧缺。不过奶奶家是用煤油灯的,只是听说秋天要扯电线用电,因为家里没有男人来办事,这件事又被无限期的延后了。
——
奶奶说:“怕是今年又淹了水,庄稼要减产了。”
她重重叹了一声,我偷看了一眼奶奶的神色,她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
天要下雨,本就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几天后,院子里的水都齐膝深了,奶奶家的地基也不高,和上面的鱼塘连成一片,很多人都不敢再往上走那条大路,纵然是走习惯的人,也要绕一绕,也许是怕脚一不小心就踩进了鱼塘里去。
走到视线宽阔的地方,土黄色的雨浆水泡着树,泡着草,泡着墙头,泡着屋子。
下久了,奶奶家的房子也漏雨起来,这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大家的房子也都漏雨。我经常听奶奶说这样的事:谁谁谁家的房子比咱们家的漏雨还要厉害。
雨稍停后的一天,我去了自家的院子,很不幸,瓦被雨冲掉,房子正中间一大片窟窿,屋角的地方从里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鸡蛋大的亮光。
大厅旁另一间的木头被浸湿了,这本是爸要盖新房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