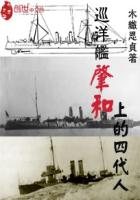黑夜,终于侵袭了大地。这片夜幕低垂的森林,寒颤阴森。微风声,小动物的低沉声都彷佛已销迹。空荡的森林带有腥味的空气中不时扩散着几声鸟的呜咽与低鸣,似乎是生命最后的挣扎,似乎也是临死前的救赎。
黑云遮盖了月亮,酝酿着孤独,充满了死气。
茫茫的黑夜吞噬着这一切,树林原有的虬枝蔓藤彷佛也浸泡在一片死光之中,显得颓唐。
夜空中,一丝光射穿了树上密布的枯枝败叶,映射在一只鸟的瞳孔中。
尔后,乌云才慢慢的退却,一点一点的将月亮呈现。黑夜像一只无形的手,揪着两人的心。不知道走了多久,两人感觉已无力再走了。
在一处干燥,地势稍高,有点靠山脊之地停留了下来,他们清理了四周的杂草,很快燃起了火堆,捡来一些干燥的树枝与叶子铺在地上,铺开了简易的帐篷,火光弥漫着四周,照在他们脸上。
他们相邻坐下,嚼着干燥的面包,喝着淡水。但是,对于此刻的他们来说,就像皇帝坐在龙椅上吃着美味的珍馐佳肴喝着陈年佳酿一样。
这个空旷的夜晚,高翔突然想起当初只能嚼干面包的日子。他又想起了家乡,一草一木,一房一院,一砖一瓦,那么亲切自然。
那些歧视他的人,背后嘲讽他的人,他们是多么无聊与幼稚,现在想起来,自己跟他们计较就算是一种失败。他又觉得那些人很可怜,居然无聊到要去嘲讽与诋毁别人,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匮乏与无知。
他想了很多,想到了第一次与关可道在病房的纠缠,又想到了宋婉,总是让他伤怀,她的离开他至今不明所以。
他只能怀着这个难以明了的疑问等待着,矛盾而错位的关系。李星火呢?在他心中又算是个什么地位?也许是宋婉离去后的替代品,也许是生理需要的衍生品,也许他也贪心的喜欢这个清纯坦率而特异的姑娘。
他偶尔也会怀着愧疚的心理,想:“以后该怎么处理与李星火的关系。”他毕竟是一个农村且带有点传统思想的人,他绝对不是那种吃完抹抹嘴就走的人。
他是一个自尊心强烈的人,就像狮子,它只要认为是属于他的东西,绝不会让其它的动物抢走。高翔恰巧也是这种动物。
在他的认为当中,此时的李星火就是他的东西,宋婉也是他的。只是各占的份量不一样,如果你定要他形容出两个女人在他心里的地位,那么他只能说,宋婉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李星火则也许就是他所穿的衣服。
但是,他永远也不会觉得女人像衣服。他从来都很尊重女性。世界就因为有了母体才会繁衍下去。而且非常尊敬这种伟大的母体。每个人都是母体所生,有什么理由会让我们不去尊敬她,孝念她呢?
每个人的出生都包含着种种的偶然因素。
你能想象,晴朗的夜晚两颗相距甚远的星星突然相撞的场景吗?这种偶然性的发生,让我们惊疑且纳闷。但是,一个人的出生岂非如此?
夜,慢慢的沉了。原本乌云密布的天空透射出月光。他们用火灰围绕着帐篷洒了一圈。孙一棠彷佛很困,睡得越来越深。
高翔用手枕着头,还是难以入睡,不知什么原因,他感觉心理很空,肚子也很空。一阵空虚。实在难以入眠,他起来了。
孙一棠也被惊醒。问道:“怎么不睡觉,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你继续睡,我想前面走走。”他低声回答道。
孙一棠突然坐起来;“既然睡不着,哪我们去干点野味啊!”
他们始终忘不了高翔烤给他们吃的蛇肉与狐肉,越嚼越香。吃惯了城市的各种菜式与干面包,偶尔面对烤的东西,当然垂涎欲滴。高翔反正也不知道该干嘛,干脆就一起去了。
两人迅速收拾帐篷,整理背包,哪里停下哪里就是他们的家,背包始终在背上。
月光下,两个朦胧的人影往低垂的丛林潜去。
草丛里,夜鹰正在捕抓着老鼠,猫头鹰也再到处寻觅,蝙蝠在夜行,野猫等等各种动物都在夜晚流浪着,远方偶尔传来几声让人悚然的狼叫声。
孙一棠抖了抖肩膀问道:“遇到狼怎么办?”
高翔简单的回答:“杀。”
孙一棠彷佛被这种霸气所感染,振奋着说:“今晚一定要吃到你烤的东西,要不然回来也睡不着。”
高翔紧握着拳头:“好,今晚我们就猎一头大的晚餐。”
他们配合得完美极了,一左一右,一边防役一边前行。夜晚充分发挥着他们的听觉与嗅觉,努力的分辨着各种动物的味道,分析着可能存在的地方。
偶尔惊动几只兔子,也没有去追击。决心要干一件大的猎物,当然不能要小的,浪费了体力,还顾此失彼。不断的前进,狼嚎声不见了,前方模糊的传来沙沙声,像蛇吞食东西。近了一看,果然是一条不大的蟒蛇,一米多些,二人看一眼,绕开了。
既然不想杀它那就不要去打扰它。打扰别人吃东西本来就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他们居然很有礼貌。右边的丛林越来越深了,动物的气味越来越浓厚,偶尔有几缕残弱的月光透射进丛林,看起来乌烟瘴气。
他们没有说话,但是却有他们的脚步声,脚踩在树叶上发出的声音足以让丛林的动物们惊醒,茂密的前方突然一阵狂叫与震动,动物明显感到有敌入侵,发出呼叫与逃跑。
原来是鹿群,大概也有十来只,由于月光下追击有视觉上的误差,他们连鹿毛都没摸到。
高翔镇静下来:“这样是抓不到,必须搞个诱饵。”两人干脆去打了只兔子,在一个低洼的地面用树枝挖了足以让大型动物摔倒的坑,把兔子剥开,让血腥味弥漫着四周,两人静静的拿着尖锐的棍子等在两边,坑上面挂着血淋淋的兔子。
良久,没什么动静,他们很有耐心。闭目养神的等待。
又过了很久,快午夜了。终于听到路上有声音了,慢慢的,近了。原来是一头野猪,一边拱着泥土,一边往前走。
高翔道:“目测一米五左右,两百来斤。你往肚子刺,我刺头部。”孙一棠默许点点头,准备动手,后方突然跳出两头狼,眼睛散发着蓝色的幽光,獠牙尖锐,面目可憎。
一头一般的狗大小,但是另一头却很大,站着比野猪还高,它施展着锋利的爪子,张着血盆大口,看着野猪。
野猪遇强敌,想退缩。狼又岂会让它跑掉。它们就如一对父子,老狼一个纵身攻击野猪的头部,小狼攻击野猪尾部。
野猪逃跑无望,奋力反击,后退一脚把小狼踢飞出去,老狼见此,愤怒的嚎啕着,咬掉野猪的一只耳朵,顿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声音很快消失在广懋的丛林。
野猪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居然也不甘示弱,它咬不到狼,却用它笨厚嘴和尖锐的牙齿有力的撞向老狼的腹部,老狼没有叫,滚出了2米。
又迅速爬起来看着野猪,小狼看来情况不好,但还是用那轻蔑的眼神看着野猪,二对一,耳朵的疼痛让野猪再次想逃离这两个杀手,老狼围堵着它的去路,尽管腹部被刺伤,它还是没有放弃。
它就像一个父亲,在儿子面前怎么能半途而废呢?野猪喘着粗气,终于动作稍微停顿下来,脖子太粗,狼始终拿它没办法,反到停了下来,仔细看着野猪。
小狼也重视着野猪的后方。终于野猪以为老狼停下来歇气的时候。老狼一个纵身扑过去,它看准了野猪的腿,只听‘咔擦’一声,野猪的左前腿骨头断裂。
发出愤怒而凄厉的叫声,小狼也就势咬着一条后腿。野猪无法站立,疯狂的挣扎站想起来,老狼找准时机,很快咬断它的喉咙。两人再一次见证了丛林的生存法则。
他们紧握着尖锋的棍子,身体就像一只紧绷的弓。孙一棠打手势问:“干不干?”
对于这种弱肉强食的地方,你不杀它,等它腹满以后它必是大患。高翔观察狼所站的地方,就近原则。
回应着手势:“你杀小的,我杀大的。”两人跳出来就攻击,不管是老狼还是小狼,惊愕的含着食物,迅速的想后退,却已来不及。
高翔手里的棍子瞬间已刺穿了它的身体,巨大的力量使棍直接插进了泥土,本已受伤的老狼,血流如泉,流淌了一地。
它挣扎着,悲泣着,幽光的眼神此时充满委屈,乞求,嘴里发出呜咽声.
高翔大喊一声:“不要杀小狼。”但,已晚了。
孙一棠难以收回全力的一刺,手抖了一下,还是穿过了小狼的臀部。小狼发出凄惨的叫声,看着血流一地的老狼。
同样生出乞求的目光,它没有动,年幼的它从未受过这种痛苦,只是趴在哪里看着老狼。老狼垂死叫着,像似交代什么,传递什么。很快因为流血与内脏的损坏而闭上了眼睛,孙一棠拔出木枝,小狼又是一声尖叫,它没有泪,只有哀怨与悲伤,它艰难的站起来,看了一眼老狼,决然的转身离去。
两人无限的感慨,什么话也没说,高翔想起老狼那祈求的眼神,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慈爱。它在请求不要伤他的孩子。它传递给孩子的信息是督促它快跑,不要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