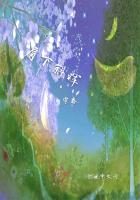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帝求能治水者,群臣皆曰鰥可治水。尧帝听群臣,用鰥治水,然九年而洪水不息,鰥未能治水。于是尧帝乃更求他人,得舜。及舜用事,摄行天子之政,巡狩天下,见鰥治水无功,诛鰥于羽山,举鰥之子禹,续鰥治水之业。
禹思父鰥治水无功而受诛,乃劳心劳力,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其曰: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九州既平,四海会同,民众安居,华夏乃成。
禹既治水,帝舜荐禹于天,帝舜崩而禹立,国号曰夏,传至太康。太康巡游天下而至豫州,只见境内山川纵横,其地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南望伏牛,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且九州之地,豫居其中,更有有伊、洛二水贯通其间。太康一阵感叹,且思:“若定都于此,正好监临诸国,万世永继。”于是发兵逐斟鄩部,定都洛水之北。古时水北为阳,都城在洛水之北,乃称为洛阳。
夏亡之后,商周代立,亦定都洛阳,而秦汉定都长安,至东汉时复定都洛阳。东汉末年,十常侍作乱,大将军何进招董卓入京,董卓率军自并州入洛阳,旋即掌控朝中大权。是时洛阳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董卓放纵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掠资物,此乃洛阳第一劫也。
董卓暴虐,激得各州郡义兵进逼洛阳,势甚浩大。董卓惧怕,乃劫持献帝迁都长安。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卓留屯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此乃洛阳第二劫难也。
后来三国鼎立,曹氏篡汉立国,文帝营建洛阳,黄初二年正月,迁都洛阳。其实当时有五都,洛阳、长安、谯、许昌、邺合称五都,而洛阳号中都,位居五都之首。此时洛阳尚未恢复东汉规模,且人口单薄,文帝乃下令天下内徙,徙冀州士家五万户于洛阳;明帝时大治洛阳宫,历时五年之久,洛阳乃恢复旧日气象。
晋代魏立国,一统天下,当然定都洛阳。那洛阳城自汉末损毁以来,历经魏、晋二代戮力营造,比前代更显宏阔富丽: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一楼,外有沟渠,西北角为金镛城,洛阳宫在城北略西,东北角为魏文帝时造的百尺高楼,其余云台高阁不可尽叙。那洛阳宫乃是南北两宫对峙,南北两宫俱皆宫观巍峨,殿宇轩昂。
洛阳南宫金马门外有一街,名曰铜驼街,相传汉时铸铜驼二枚,长一丈,高一丈,在宫之南会四道,夹路相对,铜驼伫立之处便被称为铜驼街,当时俗语曰:“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街上集少年”,可见铜驼街之繁华。
北风紧吹,已是深冬时节,铜驼街春风院二楼的一间雅室之中,却是暖意融融。雅室中间摆着一个大火盆,一群锦衣华服的少年公子分坐两桌,正自猜枚行令饮酒作乐,场面热闹非凡。
这些少年公子大多出身都中权贵之家,些许读过几本书,便自命风流,书中的至理名言仕途经济一概不学,单把些风花雪月春愁秋悲学了个精通。机缘巧合之下一见如故,彼此相见恨晚,引为平生至交,自此你引我荐,结识了好些个无聊子弟。于是结下诗会,定在每月十五日,或至长堤踏青,或至野寺赏梅,或至别院玩月,或至校场射覆,凡是才子风流雅集之事,总归是要玩一玩的。事后则作两首歪诗,掉两句酸文,也就算是全了诗会之意,其实不过借此机会玩乐罢了。
正在喧闹之际,坐在窗边的一个少年忽地推开窗户,大声叫道:“了不得了,你们快看!”众人放下酒杯,一起拥到窗前,向外一瞧,不由得惊喜连连:却见天气阴沉,大雪如鹅毛般沉甸甸的往下直压,近处的房屋和远处的道路都被大雪覆盖,不一时便是一个白茫茫的世界了。
众少年玩心正炽,哪里在楼上待得住,于是纷纷奔下楼去,捏了雪球互相抛掷,疯疯癫癫的玩了一时便禁受不住,仍旧回到房中。此时关了窗户房中昏暗,这个大呼掌灯,那个又令人加碳,待重新温了酒,更把两桌拼作一桌,又复行起了酒令。
座中有一少年,亭亭秀立,容貌都丽,姓裴名玉,字扶危。裴氏乃河东望族,魏文帝时从诏内徙至洛阳,裴玉父亲裴頠,已亡,其兄裴嵩袭父爵位,在朝为官。昔日裴頠有功,受封武昌侯,裴頠固辞不受,朝廷感念其德,乃授其少子,便是这裴玉了。
裴玉既出名门,又受封侯爵,此时却不过十六岁,其兄裴嵩日日忙于朝政无心管束,裴玉便与一班都中少年整日里斗鸡走马,宴游不休,所谓“金鞍美少年,去跃青葱马”,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裴玉连输了三局,已不胜酒力,心生一计,遂拿起筷子在桌沿上敲了几下。众少年都转过头看他,裴玉笑道:“诸位,似这般牛饮有什么趣味?倒可惜了这些美酒。”众少年皆道:“依你说,倒怎么喝才有趣?”裴玉道:“今日既然是小弟做东,我便要改一改这酒令。”众少年又皆道:“依你,依你!”
那裴玉于是站起身来,又笑说道:“我这个酒令还需两物,诸位少候,待小弟取这两物去。”说罢匆匆跑下楼去。不一时,却见他手上拿着一束梅枝,身后跟着一个小丫头走了进来。
裴玉笑嘻嘻地道:“好了,两物都已齐备。我这个令儿最是有趣,叫作‘击鼓传花’,一会儿我们用手帕蒙住这小丫头的眼睛,叫她击鼓,也不限什么令儿,我们将这梅花依次顺递,传给旁座。这小丫头的鼓声一停,持花未传出的人便要罚酒一杯,诗就不作了,但要讲一则趣闻,叫大家乐上一乐,岂不比先前的酒令有趣?”
众少年都觉有趣,便催促行令。那小丫头从背后解下一面小鼓放在桌上,旁边一个少年急忙拿出自己手帕,蒙住了小丫头的眼睛。裴玉叫一声开始,听得小丫头咚咚地敲起鼓来,急忙把手中梅花向旁坐传了过去,传了五六个人,小丫头鼓声忽一停,梅花留在了一个微胖的少年手中,还待再传下去,众人已是不依,直要他喝酒讲笑话。
那微胖的少年名叫王靖,字宏声,其祖父为司徒王戎,其父为王勉,亦是名门之后。王靖身材短小且胖,但为人圆滑,言辞风趣,都中少年常以他逗笑取乐,他却也不以为意。
王靖喝了罚酒,求饶道:“小弟认罚,但却实在没什么趣闻可讲,饶了我罢!”裴玉佯怒道:“表兄,你若是没笑话可讲,那就要取大杯来,连饮三杯,罚下场替大家斟酒,方可饶你!”
王靖心有不甘,笑道:“扶危,你这罚的也太狠了吧?”裴玉笑道:“快想,快想。”王靖急得抓耳挠腮,眼珠子滴溜溜直转,过了好一阵子,忽然大叫一声,说道:“有了,有了!”
众少年忍住笑意,凝声静听,却听王靖道:“话说某县中有一个姓李的乡绅,家中富裕,有一个儿子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也是个读书人。不想那乡绅忽得病死了,给他家儿子留下了好大一处家产。那李公子年近弱冠,尚未娶妻,平时淡然自处,只知吟课读书,也没什么可说。族中几个叔伯却都眼红他家财产,意欲夺取,只苦于无计。偏有一个极狡黠的老族叔,掀髯谓诸族人曰:‘余有一计,若能行之,管叫汝等尽得他家财产’。几个叔伯乃大喜,问曰:‘计将安出?’,那老族叔目视族中一妇人而笑,谓族人曰:‘吾计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族中妇人乃是李公子的一个婶母,寡居已久,日甚贫窘,平日里妖妖娆娆,颇有几分姿色。”
他一边讲一边极力模仿,讲到“掀髯谓诸族人”数语时,伸出一手在颌下虚抚,眼睛微闭作思虑状,待讲到族中妇人时,在颌下虚抚的那手又作兰花指横在胸前,另一手挡在脸前半开半掩,神态扭捏作娇羞状,众少年都被他逗得大笑不止,却听王靖又道:
“一日清晨,那妇人收拾打扮一番,进了李公子卧室,几个叔伯却都远远地跟在她的身后。李公子正在诧异,不料那妇人大叫一声非礼,不待李公子反应过来,诸叔伯们已拥将进来,拘住李公子,大骂道:‘好啊,小子,竟敢非礼起婶娘来了!’又押着李公子到了县衙,诬以强奸婶母之罪。原来那老族叔使得却是一个美人计。”
“那李公子为原告,诸族人为证人,证据凿凿,李公子即喙长三尺亦无从辩解。县令素有清声,当下也有几分疑惑,但证据确凿,况事关风俗教化也不敢大意,于是就将李公子暂拘于牢中。李公子无端遭此诬告,整日里唏嘘长叹,几不羞愤而死。他却不知来了一个大救星,要救他于水火之中呢。”
“要说这个大救星也是个读书人,只知道他姓名叫做刘好放,最是个好打不平,机智多谋的人,他在酒肆中听闻此事,心中已知道李公子乃被人陷害,于是便问旁人:‘县令清明乎?’旁人便答:‘本县县官素来清廉,良吏也。’刘生心下窃喜,当下结算了酒钱,假托李公子朋友,去县牢中探望。那刘生便道:‘君欲出狱乎?’李公子默然良久才道:‘君何人,而能解我于缧绁之中?’刘生道:‘我道经贵县,听闻君含冤入狱,不忍君受此冤屈,故来相救。’那李公子感激涕零,说道:‘君果能救我,我愿半分家财于君。’刘生笑道:‘我岂贪君之财产?事不难也,他日县令重讯时,君只言:婶母,不过强奸一次而已,何故下次毒手?’”
讲到这里,座中一个少年忽大笑道:“胡说胡说,强奸婶母已是大罪,那李公子既然含冤,何故自己承认,还不止一次,可见这刘生是个狗头军师了。宏声你快莫要瞎编了。”
王靖摆摆手忙道:“是啊,李公子何尝不与诸位想的一样,当下便道:‘君何故戏我?’刘生道:‘君欲洗冤,非此言不可也,何敢戏君,君只管依计而行。’李公子见刘生说得慎重,心下却也将信将疑。”
“过了几天,县令升堂审案,刑仗森列,观者如潮,李公子依刘生计语其婶母,他婶母听了即道:‘何止一次,何止一次?’”
讲到此时,座中少年击案大笑,却又听王靖讲道:“县令闻言大怒,拍案叱日:‘胡说,强奸有几次可强?尔等利其家产,污控李生强奸,情节显著!尔侄既屡次强奸,尔尚再至其室,是尔诱其强奸也,如不实供,大刑伺候!’妇人大惧,讲出实情,李公子即无罪释放。回至家中,李公子到处寻访刘生,不料那刘生却已鸿飞渺渺,李公子也只得作罢。嘿嘿,诸位我这一段故事却有趣也无?”
众少年啧啧称奇,连说有趣,均叹刘生高义,又笑那妇人愚笨。裴玉笑道:“表兄凭此故事也解了大难了!”
嘻嘻哈哈的笑了一回,众少年又行起令来,鼓声响起,梅枝传四五圈,又停在了一位少年手中。那少年见梅枝停在了自己手中,忙将梅枝硬向旁座少年塞去。旁座少年甚是机灵,忽地跳开座位远远避开,梅枝“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众少年大笑,原来这输了的少年名叫陆宏,字敏思,素有口吃之症,平日里少有言辞,不过随着其他少年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现在忽要他讲笑话,却不要了他性命?
陆宏红着脸分辨道:“这局……局不……算,梅花应该是……”旁座少年忙道:“怎么不算,鼓声停时,梅枝就在你手,你可不要耍赖。”陆宏手指众人道:“你们……你们……合伙欺我,今日……”他急怒之下,话就更说不清了,王靖学他语气道:“今日……今日,你……你就……就要如何?”
众少年哈哈大笑,陆宏脸上涨红,怒目相视,过了一时,乃颓然坐下说道:“罢……罢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吧!”
众人知他平日不甚言辞,还要取笑于他,裴玉道:“好了,诸位不要取笑敏思了,听他讲笑话吧!”众少年忍住笑噤住声音,却听陆宏大声道:“我这则笑话,乃……乃都中趣闻,也不知真假,说起来还出自……出自宏声家里呢!”
王靖皱眉道:“出自我家里?我家有什么趣闻?”转过头瞧了裴玉一眼,却见裴玉也是一脸疑惑。众少年被勾起了兴趣,忙说:“快讲,快讲!究竟宏声家里有什么趣事?”
陆宏道:“诸位都知道宏声祖父王戎王司徒任职尚书左仆射,历仕魏、晋,也算得一位老臣了。王司徒长于玄理,评论精辟,识鉴闻名,我佩服得很。”此时他冷静下来,言辞又颇通畅了。众少年都点头称是,王靖见他谈论起自己的祖父,也不敢再取笑他。陆宏又对着王靖道:“尊祖父雅量识人世所皆知,我就不多说了,但王司徒还有一个绝技大家却有所不知了。”
众少年心中好奇,纷纷问道:“什么绝技?”那陆宏笑道:“诸君岂不知王司徒精于算筹么?王司徒虽富甲天下,但为人吝啬,每与夫人灯下算筹得失,若是盈利便喜笑颜开,若是亏损则终日不悦,久而久之自然精通算筹之学了。”众少年想笑又不敢笑,王靖脸上很是尴尬,那陆宏见众人都忍笑不语,知道他们是碍于王靖的面子,但他恼怒王靖学他口吃,有心叫他脸上无光,便又道:“司徒家有一李子树,夏天时结的李子脆嫩爽口,司徒却舍不得吃。司徒想我家李子如此好吃,若是自己吃了,岂不可惜?于是便吩咐下人将李子摘下,准备出售,但又想若是他人得李子核留种,后来长成,岂不跟我竞争。司徒又复下令将出售的李子核剔除,才敢将李子出售。”
一少年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口中道:“这件事我也曾听闻……”他这一笑,带得其余少年也都笑起来,再也顾不上王靖的面子。王靖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大是窘迫,裴玉面上也不好看。
陆宏看王靖尴尬,抱拳一揖,笑道:“靖兄,得……得罪了。”王靖鼻子哼了一声,也不说话,陆宏心中大呼过瘾。忽末席一少年抢道:“我还听得一则,也说给大家听。且说王司徒有一女出嫁,嫁妆不菲,司徒终日哀叹,其女忙问父亲何故哀叹?司徒说汝今出嫁,费我好大资财。司徒女素来孝顺,当即说道父亲不必忧虑,嫁妆之资全当女儿借贷,待至夫家悉数奉还,司徒乃大喜。已而妻女归宁,司徒脸上不悦,其女忽想起昔日之言,急忙至家将旧日嫁妆所费之资装载马车,急驱至司徒家,父女二人才复归于好呢!”
众少年又是一阵大笑,裴玉铁青着脸,忽从从座中站起,指着刚才那少年喝道:“孙会,你竟敢戏弄于我?”原来裴頠取妻王戎之女,裴玉的母亲就是刘侃刚才所讲的司徒之女。裴玉性情乖僻,此时见孙会调笑外祖父和母亲,焉能不怒?
孙会刚才只顾取笑大家,怎想得此节?此时见裴玉发怒,本来想道歉谢罪,但此时众少年都聚集在此,若是谢罪岂不是显得自己胆小,于是指着陆宏道:“偏他说得,我就说不得?”
众少年纷纷解劝,裴玉却哪里忍得住心中的一股怒火,顺手抄起酒杯就扔了过去。那酒杯不偏不倚正中孙会的额头。那孙会平日也是嚣张跋扈,那肯受此大亏,举起酒壶便还击了过去,偏偏失了准头,砸在了王靖的怀中,洒了他一身酒水。
王靖趁势站起,怒道:“好啊,孙会,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欺负到你靖爷爷头上了。”他刚才忍住不言,此时见裴玉动手,便要助他声威,更何况他和裴玉还是中表之亲。
王靖一边说话,一边举起凳子朝刘侃扔了过去,那凳子沉重,中途便落下,砸在了酒桌上,溅得众少年满脸酒水。众少年纷纷离座擦拭,顿时一阵混乱,陆宏素恨裴玉王靖二人常常取笑自己口吃,此时怎能错过机会?端起一盘菜藏在背后,慢慢走到王靖身后,乘其不意,兜头扣在了王靖头上。
王靖怒叫一声,头上菜汁流将下来,不敢睁眼,口中大骂。裴玉忙取了手帕帮他收拾擦拭。待睁开了眼睛,却见众少年站在一旁笑个不停,也不知是谁动的手,当下恼羞成怒,也不管是谁动手了,胡乱将桌上的菜盘乱扔。几个少年中招,也发起火来,纷纷还击,裴玉自然帮助王靖,但二人势单力薄,只见数十个盘子砸了过来,弄得全身湿透。那些盘子飞来飞去,也有误伤的少年,加入裴玉阵营,一帮少年打作一团。
桌上的盘子已被众人扔在了地上,更有那胆大的少年掀翻了桌子,举起凳子混战了起来。那春风院老板闻得楼上异响,急忙带了伙计上楼查看,却见室中狼藉不堪,众少年厮打在一处,也不听他解劝。
老板急得无法可想,急忙命人报知洛阳令。洛阳令带了一队官兵急忙跑了过来,一见众少年都是名门之后,不敢贸然拘捕,只得命令军士将打做一团的少年分开,彼此解劝。众少年见引来了官兵,怕事情闹大,便都罢了手,携带了仆人各回各家了。
一场诗会不欢而散,老板也不敢讨要酒钱。裴玉从怀中拿出一串钱仍在地上,也扶着王靖走出了酒楼。
此时天已大黑,宵禁也已经开始。裴王二人到了楼下,却不见自己的仆人,连马车也不在。原来两家仆人都相识已久,他们知道诗会非至半夜不能结束,都自己架着马车耍乐去了。裴玉骂道:“仆人懒惰,回去非打断他们的狗腿不可。”
王靖道:“扶危,今日多谢你出手助我。”裴玉狠狠道:“可恨陆宏,孙会二人竟敢辱我两家尊长,总有一日要叫他二人吃吃苦头。”王靖点点头,道:“今日你打断了孙会的狗腿,也算是出了我们心中的一口恶气!扶危,我就此别过了,请明日务必到府中一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