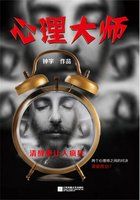今天罗伟林回来得很早,他特意买了梅一朵喜欢吃的鲜辣口味虾,估摸着梅一朵快下班了,便将口味虾从一次性饭盒里倒腾到小锅子里,放到液化气灶上,开着小火,熬着,好将汤汁佐料的味道,穿透坚硬的虾壳,更深入地熬到细嫩的虾肉里去。
他想精心备好的晚餐能出点气氛,便下楼去传达室旁边的小店子里买啤酒。
传达室的保安老刘正跟守店的老板娘嘻嘻哈哈,看见他往里走,就切断那边的话尾调侃罗伟林:罗老师,昨晚那个时候你还在杂屋里搞么子鬼哦?
罗伟林心里一惊,嘴上却抵赖。
老刘打着哈哈道:还不好意思承认?那彬伢子猜对了。
罗伟林没想到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还不止被一个人看见。他知道,传达室传达室,不仅传达物件信件,更能够传达各路消息,这事情现在还不知道传达到了怎样的广度和深度呢,心里就鼓一样的擂开了。
他问:彬伢子?怎么—什么意思?
老刘得意地说:不是我拉住他,昨晚上他就冲过去把你做贼捉了!老实交代,你那衣服上被什么人搞了什么顽固不化的家伙?
罗伟林装作刚明白过来,淡淡地回答道:哦,我自己外头没搞好,搞了些油漆。又转对老板娘说:买四瓶啤酒。
提着啤酒回到屋里,他意识到上午李璐的劝解正在丧失作用,重又变得烦躁起来。
上午,俩人再次细细地温存之后,李璐就趴在他的肩膀上开始劝说,她说他娶了个好老婆,要他还是好好地对待梅一朵。他觉得李璐确实是个好女人,梅一朵也确实是个好女人,自己碰到的都是好女人,可是为什么这些好女人都不能给自己一个好的生活呢?
梅一朵也许正怀着兴师问罪的雄心在回家路上,讲不好传达室这两个向来多嘴的保安已经将昨晚自己反常举动尽职地传达到了她的耳里。难怪她会在上班之后,反常地打来电话追问。
关于昨天深夜梅一朵电话进来时不巧自己正在跟李璐打电话这件事情,罗伟林已经跟李璐商量好了,李璐的手机现在已经放到了罗伟林的一个哥们儿的手里,如果梅一朵回家后再提到这件事,罗伟林就会用自己的手机按着昨晚那个号码打过去,说是昨晚跟一个兄弟商量事情,梅一朵只要听到电话那头的确是个男声,一切问题就会随着她那丰富而飞快的联想得以澄清。
而现在,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昨晚自己告诉梅一朵说是车漏油弄到衣服上的,今天才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落入了还不止一个人的眼中,梅一朵肯定也在猜想谎言背后的真相,而自己半夜跑步的不堪,还不知道有没有传到梅一朵的耳中,这种事情,问又问不得,真是烦人。
心烦意乱的罗伟林,望着桌上为梅一朵精心准备的口味虾,心里越发蔑视和可怜自己。他拿起筷子,撬开啤酒瓶,打算将这些东西吃到只剩残骸,来显示自己的自私,用自私来表达对梅一朵的漫不经心,用这种漫不经心来维护自己男子汉的尊严。
梅一朵带泪带伤地一路回家,心已被痛苦揉搓得疲倦不堪,掏钥匙开门那会儿,她改变了跟罗伟林大干一场的初衷,她明白自己心里的痛苦不只是罗伟林一个人引起的,罗伟林对她的伤害,被刘冬明起初的爱慕和亲昵举动暂时按捺下去,现在刘冬明又给她新添了伤害。回来的路上,她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找罗伟林吵,她不能破釜又沉舟,虽然破掉的“釜”只是初具形状,快要沉掉的“舟”也千疮百孔,但是有甚于无,所以进门之前,她准备回家就睡觉,她只想睡觉,也只能睡觉,无论怎样,睡饱了明天才有精力面对一切。
可是,开了门,所见的情景又刺激了梅一朵。
桌子上坟冢一样堆着红红的虾壳,虾的“衣冠冢”旁边是一只大碗,筷子横搁在上面,像通往地狱的奈何桥。
她想起刘三姐的歌—“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罗伟林举起酒瓶,正仰头喝着,见她进来,还特意咂嘴品酒,发出刺耳的声音,眼睛里满含着讥诮的挑衅。
梅一朵应战的力气忽然从全身各个角落缝隙里苏醒,并且像士兵半夜听到了冲锋号,斗志与斗力迅速从沉睡中跳起、集结,她心里的声音先喊道,离婚!这次一定要离婚!
她把刘冬明派人给她找的主题队会的资料往客厅中间一扔,瞪着四散的纸页咬牙切齿喊,喊出来的字眼却只是:分开吧!分开吧!
喊完之后,梅一朵诧异自己到了这一步为什么连“离婚”两个字说出口还会走样,便鼓足勇气将眼睛瞪向罗伟林,想用眼神来为怒气和决绝做补充说明,哪知眼睛却不配合、不争气地连眨了两下,不坚定、没底气泄露无遗。
这点被罗伟林看在眼里,本来被梅一朵首次摔东西弄得受惊的眼神,也因此平复下来,这时他连身都不起了,仰头咕咚喝了两口酒,才慢条斯理地说:分开?你的意思是离婚吧,离就离吧,别这个样子,注意你的形象。
梅一朵的形象却不是她自己能注意得了的,这时,失控了的鼻涕、眼泪都背叛了主人端好的形象齐涌上来,她跌坐在沙发上,只饮泣了两声,号啕就像骤然拉响的防空警报,充满了整个房间。
罗伟林听到这声音,有些得意,有些心软,又有些烦躁,他知道梅一朵爱面子,就走过去打开窗户,故意夸张地把头伸出去:咦?天没塌下来啊?
梅一朵气恼又奇怪罗伟林这时候还有心开玩笑,就强收了哭泣,压了声音怒道:我虽然没你有心计,起码的辨别能力还是有的,有些事情,你做了,它就在那里的,你别以为你这样那样的就可以装傻装掉!
这个问题罗伟林在吃虾喝酒的时候就替梅一朵问了自己一万次,所以这时候按照排演的那样,他轻描淡写地说:我装什么傻?不就是昨晚那时候还打电话吗?
说着他就像三国那会儿正在城墙头上弹琴摆空城计的诸葛孔明,镇定地捏着手机过来挨梅一朵坐下,飞快地翻到通话记录:你看好了啊,已接电话,九月十四号,零点过一十七分,这个是你打的;已拨电话,零点过一刻,你看好了啊,我打过去。
电话通了,他对着早已备好了底的哥们儿说:是我呢,今晚上你们在哪个屋里玩?
问了这句之后,他马上把手机放到梅一朵的耳朵边,手机那头传来的男声说:玩什么玩!三缺一,你又不来,玩不成啊。
罗伟林就此挂断电话,胜利地盯着梅一朵问:你觉得还有必要再追问别的吗?我告诉你,你那编剧的工作已经把你的脑子搞得远远地脱离现实了,你那所谓的猜想一万个是不存在的。要眼见为实。
罗伟林把工作做到这个地步,要在平时,梅一朵会马上伏贴,可是今天梅一朵受到的是复合型伤害,好比断掉的两根胸肋现在只接好了一根,另一根还隐在哪里生生地刺得发痛。她挣扎着继续发难:什么我眼见为实,别人眼见就不为实了?我问你,你衣服上到底搞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家伙,要撒谎,要搞阴谋掩盖!
这个问题,罗伟林在喝酒吃虾的漫长过程中,也已经想到了应答的方式和内容,虽然背上汗湿,也没有鹅毛扇摇,他面上却比当年的诸葛孔明更镇定,他叹口气靠向沙发,眼睛望着天花板说:怎么跟你说呢?其实很久以来,我就担心会出事,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该不该向你坦白—
说到这里,罗伟林就故意把话掐断了,果然,梅一朵的口味被吊起,她紧张地问:出事?出什么事?你—
罗伟林又叹了一口气,叹出来的真诚度让他自己都受感动,他显得很艰难地表白:我们学校有个音乐老师叫孙瑟,去年分来以后,就开始对我好,前一阵还说要找个时间跟你谈判,当然这个也许半真半假啊,反正学校好多同事都知道,我说不可能,总是拒绝跟她单独在一起,这个学校同事也知道,可是她不甘心,总在纠缠,昨晚我们几个同事在打麻将,她也在旁边陪着看,临走的时候,她拿了瓶香水过来偷偷喷了好多在我衣服上,还说,“要是你老婆连这个也能忍,我就服了她,把你让给她”。
说到这里,罗伟林又故意停下不说了,只望着梅一朵。
梅一朵果然又掉到了陷阱里,她伸出食指,指指罗伟林又指自己,冷笑道:你到底是谁的?她把你让给我!
罗伟林也冷哼道:哼!是啊,你看这样的神经病谁敢惹?本来我想昨晚就跟你讲明的,又怕你连夜找她吵,那就中她的计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男子汉嘛,应该多承担一点,不过今天你既然问了,我就说了吧,免得你猜来猜去更难受。诶?你怎么知道我是故意搞汽油的呢?你长了透视眼,能够穿过层层楼板看到杂屋里去?
本来到这个时候,梅一朵已经被罗伟林的瞎扯完全扯“瞎”,心灵的眼睛完全被蒙蔽,死心塌地、感恩戴德地准备把疲倦的身心投向罗伟林的怀抱,谁知潜在手机里的罗伟林的“情敌”适时抢救喝止。
梅一朵看了眼手机,是自己倒背如流的刘冬明的号码。罗伟林就在旁边,是接还是不接?
刘冬明肯定以为现在自己还在学校,还不知道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手机又如此漏音,不接,不能接,可是如果不接,罗伟林又会怀疑的。
正是她犹豫的眼神和陡然涨红的脸提醒了罗伟林怀疑,他像要求证似的催促道:你接啊?怎么不接?你怎么回事?
梅一朵越发不敢接了,心跳的声音自己都能够听见,她在想怎么向罗伟林解释呢,忽然急中生智道:接什么?一个给我推销保险的,我都烦死他了,你说我们哪有闲钱买保险呢?说完后无限佩服自己,同时想弗兰西斯?培根讲“爱情是愚蠢的儿子”,其实爱情也是“谎言的母亲”啊,她那时却没有推己及人地想到罗伟林的谎言。
也许是伟大的哲学家培根在天有灵,不同意梅一朵的论断,要戳破这谎言证明自己的权威性,梅一朵的手机里接着又跳出一条短信。
罗伟林并没有相信梅一朵的解释,短信声“噔”地响起,他抢先拿了手机翻看,短信的号码就是刚才的号码,内容是:
还在生气啊,我刚出来送李老师回家,毕竟引起她的怀疑对我们以后的交往不利,你理解一下,早点休息,明天到单位再给电话。
罗伟林捏着手机,不断地冷笑着,鼻腔里一顿一顿地发出“哼!”“哼!”“哼!”的气声,哼的时候双肩也随之抖动,频率和力度都像点了火却发不动的柴油机车。
他这时眼睛望着天花板,惨白的天花板上先是出现短信里文字,接着出现的却是他和李璐缠绵缱绻的情态,有个酷似自己的声音在他心里感慨:好笑!太好笑了!罗伟林,你笑啊!不好笑吗?太好笑了!真他妈的太好笑了!
梅一朵被罗伟林的神态吓住了,她猜到可能是局长刘冬明的短信,她很想去看看内容,可是她又怕去罗伟林的手里拿手机,她怕自己的手一碰那手机,现场就会爆炸。
梅一朵正惴惴不安地看着罗伟林狰狞的表情,罗伟林却转头朝自己笑了,递过手机说:你自己看吧!卖保险的,哼!
梅一朵飞快地看短信,边想着怎样来解释这个短信会对自己更有利,还没想明白,就听到“嘭”的一声巨响,罗伟林摔门出去了。
“嘭”的声音在她耳边久久回荡,梅一朵捏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后来她又像罗伟林那样“哼”起来,哼着哼着,也像罗伟林那样笑起来,她笑着笑着,就起身到抽屉里去拿5毛钱一本从地摊上买来的红封皮黄历,她要看看今天吉神在哪方,喜神在哪方,她要看看今天到底是什么冲什么的日子,现在她挑不出罗伟林错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她只好怪今天日子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