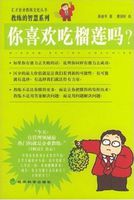火车,汽车,终于走进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晚上十点差十七分,楚卫新推开红色的木门,砖瓦房并没有装修,脏乱丛生。
“进来啊。”
顾蓉站住不动,牙齿咬住下唇,放开,“等一会儿。”
“要不我先进去?小叔不知道我回来呢。”
“不要。”
顾蓉阻止踏进门的楚卫新,“我还没有准备好,你说的是楚连承吗?”
“进去看就知道了。”楚卫新反握顾蓉的手,“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的。”
进到里屋,楚卫新熟练的打开灯,躺着的楚连承翻过身来,看清楚来人,笑着说:“小新回来了,你爸刚走,没遇见他啊?”“嗯,小叔,身体好点了吗?”楚连承撑着身体坐起来,看见一旁阴影里的顾蓉,舒缓的眉头不自然的蹙在一起,“小新带朋友回来,怎么不先招呼呢,我身体都老毛病了,早一天看晚一天不会出事的。”“小叔,这是我同学。”楚卫新把顾蓉拽到面前,“她来我们这里玩几天。”顾蓉绷紧面部,刚才的打量没有让她惊慌失措,反而镇静许多,她礼貌而僵硬的说:“我叫顾蓉。”楚连承拉近被褥,一笑示意,对楚卫新说:“小新,你们做了一天的车,先带你朋友去休息吧,明天再来玩。”逐客令,楚卫新看了一眼顾蓉,说:“嗯,那我们明天再过来。”
走出红色的门,楚卫新急忙问:“是吗?”顾蓉撇了他一眼,“你家在哪里?快点去睡觉。”“是还是不是?”楚卫新不依不挠的问。顾蓉却说:“手机没电了,快点带我去充电。”五六分钟后,楚卫新的家便到了,楚父还没有睡觉,简单的打招呼,楚父便回了房间,顾蓉站在原地,震惊难醒。火车上,楚卫新就已经说过其父与叔相貌极像,见到之时才有感觉。躺在床上的楚连承久病不举,早年的潇洒英气消失殆尽,楚父身体健硕,眉宇之间是全然不同的感觉,甚至几分威严下还有易怒的神态。
楚卫新已经把床铺弄好,顾蓉的手机也连接电源,几乎没有表情的顾蓉没有洗漱便倒在床上,无暇顾及其他。
“楚卫新。”顾蓉叫住交代好一切的楚卫新,“你说他是真的认不出来我,还是故意认不出来。”“小叔身体不好,可能????????”“我也差点认不出来他,他变化好大,我的记忆停留在他的黄金时代。很明显,前面的问题顾蓉并没有一定要一个答案。“他真的快死了吗?像开玩笑一样。”顾蓉喃喃自语。
“明天起来再想,关灯了。”
楚卫新关掉灯,走开。
当他第一次见到顾蓉手里的照片,一直没把照片里的人和小叔连在一起,毕竟小叔已经卧床多年,不敢直白的问父亲,只能揣测独自生疑,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曾经有一段不羁的年少,仔细想来从小到大,父亲从未出过远门,并没有长时间在外的时间,所幸不久前见到小叔的某封信笺上落款为“楚连承”,问及母亲才知小叔年年月月里的经历,如今,小叔被检查出淋巴癌晚期,楚卫新擅自做主带回了顾蓉,也许是还顾蓉的人情,也许是感激小叔的疼爱,究竟做错没有,他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谁又知道呢?
也许是在他家的缘故,早起,山里的空气新鲜爽人,摸寻着昨晚走过的路途,天刚刚亮,顾蓉就已经站在红门前,进去或者不进去,犹豫不决。
屋里的咳嗽时有时无,顾蓉推开门,直接走进房间。楚连承坐在床上,身子倚靠在床头,床头地上堆满烟头,指尖夹着的烟还冒着白烟,看见顾蓉的那刻,烟被扔到地上,眸子里迷蒙,看不见任何。
“对不起。”
楚连承开口只剩下这三个字。昨晚楚卫新在场,他对记忆有所保留,果然是故意认不出来她。顾蓉站在那里,看着精神萎靡、一脸胡渣的楚连承,心里说不出来的感受,她以为她会哭,她以为她会恨,可是真正见到的时候,心里就空了。
“我还以为你忘记我了呢。”顾蓉站着,“真是好巧,认识你之前我们竟然隔得那么近,认识你却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越来越远。”顾蓉走过去拉开窗帘,鱼肚白越于屋内。
“要不要出去走走?”顾蓉回头问楚连承,然后把靠在墙上的拐杖拿起来,替楚连承掀开腿上的被子,扶他下床,看着他吃力的走每一步,顾蓉跟在后面,红门前的阶梯,顾蓉扶着他摇摇晃晃走完,走出马路,质朴的乡村感得到凸显,鸡鸣狗叫,炊烟缭绕。
“要休息一下吗?”
楚连承点点头,二人在水泥马路的尽头坐下,一棵苍天大树苍劲挺拔,树根拨出土地,盘旋错乱,冷风萧条。
“对不起,我失信了。”楚连承没有多余的话,他甚至都没有开口解释过为什么没有回去找他,他只是说对不起。
“没关系。”顾蓉没有看他,“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所以想来想去,你应该很希望听到说没关系,我不在意之类的话吧。”她继续说,“其实我们那么多年没有见过,没有联系,事情早就不重要了,谁会记得那些东西?要不是认识楚卫新,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见不见还不是就那样了。”
“你好吗?”
“你是问我以前好吗?还是现在好吗?还是以后好吗?”顾蓉看着他,“当然都好,一直都很好。”
楚连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邹巴巴的纸,放到顾蓉手上,“我的一辈子马上就结束了,见到你就一定要问问你好不好,不见到你就算了。我回来六年,没多久就检查出淋巴癌,还能活到现在都是神眷顾,以前的就不会想了,以后更不会想了。”顾蓉右手杵在脸上,拦住了眼睛里的水分,这个解释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也不得不接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