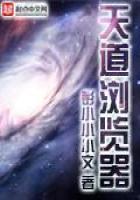看着眼前古香古韵的房间,杨思思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了,房间四角立着白玉似地的柱子,四周的墙壁全是白色石砖雕砌而成,黄金雕成的兰花在石柱之间妖艳的绽放,青色的纱帘飘飘渺渺随风而漾,家具全是原木色的。
淡淡的檀木香充斥在身旁,镂空的雕花窗桕中射入斑斑点点细碎的阳光,细细打量一番,身下是一张柔软的木床,精致的雕花装饰的不凡,身上是一床薄被,侧过身,一把古琴立在角落,满屋子都是那么清新闲适,如果不是足够清醒,她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古代。
昨晚的事发生的顺理成章,也许是太思念,也许是放不下,她并没有挣扎,明知道这样不可以,还是给了他,一夜的疯狂唇边还残留着他炙热的吻,身旁的位置空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轻轻动了动手指头,右手钻心的痛,包裹着纱布有些肿,耳边忽然响起询问声:“杨小姐醒了,现在起床吗?”
一位五十多岁的清瘦妇女站在床边,不卑不亢的神色。虽然声音不大,杨思思还是被吓的不轻:“您是谁?这是哪里?”
“杨小姐以后叫我李嫂就好,我是这栋别墅的保姆。”妇女边说边拉开纱帘,语气很公式化:“这是牧先生名下的别墅。”
还真是问的傻,这算是被包。养了吗?
心口微微扯的发疼,准备下床自己洗漱,李嫂急忙扶住了她,扶她到浴室,挤牙膏,拧毛巾,找好换洗的衣服,照顾的无微不至。看李嫂淡然的神色,这栋别墅不知道她这样伺候过多少人?
左手进餐不灵便,也是李嫂喂的,她只是木讷的配合着,思绪很混乱,脑子里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前妻?二。奶?情。妇?我算是哪个身份?好像每个都沾边。
趁着李嫂收拾厨房,她自己动手换了纱布,见厨房门口有一大袋垃圾还没来得及扔,顺手拿了换下来的纱布准备丢进去,却被垃圾袋中的东西吸引了眼球,半瓶指甲油、半瓶香水、各种护肤品、丝袜、内衣裤等等。
“你来的匆忙,房间还没来得及收拾。”李嫂从厨房出来见她愣在垃圾袋旁,坦坦荡荡的语气并没有隐瞒的意思,提上垃圾袋出了门。
看来身份还不止是那样,也许是三奶、四奶依次往上加了。
杨思思惨然的笑笑,拼命逼着自己不去在意。
待李嫂丢完垃圾回来,试探性的要了李辉的电话,没想到李嫂还真有他的号码,作为他的情。妇之一,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保姆肯定得联系他,情。妇不是多重要的人,电话肯定不会是他本人的,多半是李辉口传给他。
给李辉通了个电话,李辉对她成见不小,电话里面说了几句风凉话就挂了,约了见面的地点。
下午四点,小区外右转有个咖啡馆。
李辉风尘仆仆的赶来,她正喝第四杯卡布奇若。
李辉的眼神像带着刺儿,坐在她对面上下打量了她几眼,开口满是讥讽的语气:“真是,这个世上很难找到比你还下作的女人了。”端起咖啡对着她扬了扬:“我敬你。”
杨思思有些难堪的捋了捋垂下来的几丝头发,不想跟他斗嘴:“我只想知道,他过得好吗?幸福吗?”
和他现在的太太感情好吗?这句话实在问不出口,昨晚发生的事,说没有良心不安是假的,虽然跟牧景成从小在一个被窝里长大,可不得不逼着自己承认只是他的过去式。
她想了解他太太的情况,又害怕听到关于这个女人的一切。
听她这样一问,李辉喝了口咖啡,语气和神色变得很认真:“我不知道像你这种女人是如何来衡量幸福的,不过,我敢肯定的说,景成哥,他很幸福。那个女人不像你,她温婉懂事,在你走后一直陪在他身边,给他生儿育女,对他没有任何奢求,安静的守着他们那个家。”
李辉寥寥几句说的全是那个女人的好,一字字震得她心口血淋淋的痛。
是啊,景成值得一个女人对他这么好,可是为什么你的女人那么多?
耳边李辉的话还在继续:“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杨思思,你还是拿了钱走吧。不要为了你儿子伤害无辜的人。玲玲很懂事,才比你儿子小一岁,她妈妈生她的时候差点命都没了,景成哥很爱玲玲,他跟依研不会离婚,也离不了婚,你们,已经过去了。”
玲玲,他的天使女儿原来叫玲玲。依研,他的太太叫依研,光听名字她都被压的喘不过气了。一定是个美丽动人的女人。
李辉招手叫服务生帮她续了杯咖啡,从裤兜里套出钱夹,取出一张卡推到了她的面前,定定的看着她说:“作为一个母亲,你没有错,我这儿也有点钱,拿去给孩子用。”
“不,我怎么能要你的钱…”杨思思是真的体会了什么叫做哭笑不得,甚至感觉自己连个乞丐都不如,知道李辉是一片好意,还是难受的无以言语。
李辉眉毛一拧,火爆脾气就上来了,卡往她左手一塞:“叫你拿上就拿上!难不成你怕我像牧景成一样睡你?不好意思,哥没那兴致!”
杨思思面色一僵,准备推回去的动作也僵住了,嘴张了张,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跟牧景成从小一起长大,你现在这个情况他是绝对不会撒手不管的。我说你就干脆点儿,直接狮子大张口找他要一大笔,或者偷一笔,抢一笔算了。他是不可能离婚的,你跟他离婚走的那天,他喝成那样还开车去追你,要不是蒋依研用身体护住他,他早就死了,依研在那场车祸中截了下肢,就算牧景成失去理智真忍心甩了她,你觉得法律会站在牧景成一边,还是会站在残疾人一边?”
“好了,我今天是背着他过来的,给你透露了这么多,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就不要让它不安,人活着也就短短的一辈子。”李辉再次招手叫来服务生,给了足够多的咖啡钱,起身先走了。
“小姐,您…您不烫吗?”服务生一脸慌张的盯着杨思思。
杨思思后知后觉的低头看,左手端的刚续的咖啡大半杯泼在了受伤的右手上,纯白的纱布染黑了,桌上衣服上一大片黑渍。
没有心口疼,所以反应迟钝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