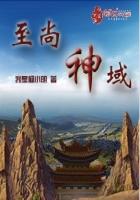苏延峰看了一眼已经很旧的老人机,当初买的时候可是用了两百块呢,现在估计二十都要不到了吧。把老旧手机扔向远处,眯起眼睛看着不远处停下的已经追了一晚上的吉普。
望着吉普车前那个清秀消瘦的身影,苏延峰不清楚这个叫屈炘的男人有什么背景,也不清楚这个男人是如何得罪了那些人,不过,这些也不重要了,正如之前所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他既然已经接受了任务,钱也已经到账,也只清楚自己只需要拿命去填上,拿掉那个与自己无冤无仇之人的命,或者送出自己这条贱命,仅此而已。
苏延峰突然想起了娘以前常告诉自己说的话语,娘没上过学,自然说不出与人为善就是于己为善的话,她只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着自己儿子,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干杀人放火的事情是会下十八层地狱的,您这不孝的儿子现在不仅要杀人,而且还是杀一个无冤无仇的人,该是永生永世不得超生了吧。
苏延峰再次咧了咧嘴,重新发动车子,将油门一脚踩到底,等到加到一定速度的时候,车子便会如离弦之箭一般冲出去,他仿佛已经看见了那个清秀男人被改装过的大众撞飞的画面,血肉横飞,也好像看见了自己在十八层地狱中的话面,同样是血肉横飞。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男人不仅没有在车上,反而是在车外向自己走来。早在看见吉普车停在路边的那一刻,苏延峰就已经知道了自己早就已经被对方发现,想着不愧是那些人想要除掉的人,的确够警惕。
吉普车前的屈炘双手插兜,眯着眼睛看着停在不远处的那辆黑色大众,只能隐隐约约看见车里面男人的一个轮廓,中等身材,面容方正,一步步慢悠悠向前走去,像个无所事事的游人,
他同样不明白为什么那个男人为何会停在车里,既不下车,也不动手。只不过,这也不重要,等到逮住出来的那人一切就都知道了。
苏延峰胸膛急剧起伏,窗外是一瞬倒退数米的景象,车前是几秒之后即将被撞上的男人。这辈子还没干过杀人放火之事的他终究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感觉的男人,做不到杀人如宰鸡仔一般平静。也不是如平常赛车那样,只是纯粹为了赛车而赛车,有危险,可最起码不像现在这样动辄生死攸关。
在即将撞上的前两秒,屈炘双腿弯曲,从小在山林里与畜生为敌而锻炼出来的爆发力在这一刻展露无遗,向旁边猛然一跃,一瞬间便脱离了黑色大众前进的轨迹,再一跃便在了五米开外的地方。站定,转身,定睛看向前方,面容平静。
苏延峰瞳孔剧烈收缩,实在没有想到男人的身手如此之好,爆发力是如此强悍,想也没想便猛打方向盘,要改变方向撞过去,意料之外的是,对面那辆从停下便再也没有动静的吉普猛然撞了过来,当正面面对时,苏延峰才真真切切感觉到来自厚重吉普的强大压迫感,就好似整个人手无寸铁面对巨型犬类一样,再也没有时间想其他的苏延峰只来得及双手紧紧抓住方向盘,身体紧绷,来缓解自己的紧张。
两辆车毫无花哨的撞上,几米开外的屈炘眼中,就好似吉普一口吞下了半个大众的身子,又好似直接骑在了大众身上,屈炘只听见砰的一声响,而后便看见了冒出的袅袅青烟。水流从吉
普车上跳下来,面无表情向已经熄火的大众走去,屈炘亦走去,每人一边,站于车窗之前。
斯文做事,温柔待人就从来不是水流的风格,况且他也不以为自己需要为了任何人而改变什么,屈炘不会去在意这些,宋邯郸是没那个脾气也没那个胆气去在意,赵一是管不了更加懒得管,而在屈炘他们眼中的舒珊儿或许以后能够改变水流待人温柔,可最多也只能是对自己人温柔,对外人还是没戏,更何况现在的舒珊儿还没有上升到那个可以管水流的高度。水流手握成拳,收在腰间,再快如闪电一样猛然出拳,车窗玻璃便应声而碎,同一时刻,车内的苏延峰手中一把匕首宛如毒蛇吐信,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刺向水流胸口,后者似乎早有所觉,另一只空着的手在匕首即将刺碰到自身衣服的刹那,抓住苏延峰紧握匕首的那只手,最初那只手拉住后者的手臂,双手同时用力,便将后者从车里扯了出来,一扯一带,苏延峰便如沙包一样被扔向了三米开外的地方。
水流没有再动手,从地上爬起来的苏延峰甩了甩肩膀,同样没有再动手,只是眼神阴狠地盯着两人,屈炘绕过车头叠车头的两车,走到水流旁边站定,定睛望着那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粗犷国字脸,八字胡,精炼短发,一身廉价衣服,从头到尾,都看不出来是一个成功人士,一眼望去,联想到的便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屈炘皱了皱眉,总感觉这人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又是在何处见过。
屈炘揉了揉眉心,甩去这些想不起来的问题,等把人抓住了还怕问不出来吗?望着对面跟了自己一个晚上的男人,开门见山道:“说吧,谁排你来的?”
相反,现在却平静下来的苏延峰虽然眼神依然阴狠,却仍是挤出一个笑脸,摇了摇头,并不说话,大概他自己也知道了自己今夜是办事成功无望,逃命无望,小命要保无望。只不过这在他看来也好,这下进了阎王殿,不用担心下油锅、进十八层地狱,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胎当个人,就算是做牛做马也行,才能报了这辈子自己欠下的恩情。
这个从山里走出来的男人,给别人拿酒灌进过医院,也给别人拿酒瓶子砸进过医院,给别人拿唾沫唾过脸面,也给别人拿手掌扇过脸面,玩过扬州瘦马,也干过街边发廊,流过血,流过汗,就是在这里没流过泪的粗犷汉子认清了太多事实,可不代表他认了命,会这样束手就擒。如果是那样,那也太对不起自己从小到大,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踢坏的,打坏的一个个木桩,太对不起那面留下太多拳印的泥墙。
尽管从来没有人教导过自己一招一式,他也相信自己的骨头肯定也要比普通人的骨头硬上不止一个档次,这是他的自信,来自一个个木桩,一堵堵泥墙的自信。从之前一接触苏延峰便明白自己不是对面那个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面若寒霜的男人的对手,可他还是想试试,最好还是能让那人骨头感到疼痛。
屈炘转头看向水流,跃跃欲试,轻声道:“小流流,让我来?”
水流头也没回便向对面男人冲去。
屈炘瘪了瘪嘴,冲水流喊道:“小流流,别打死了,记得留活口。”
听见这句话的水流无动于衷,而苏延峰却是欲哭无泪,虽然,尽管自己会输,可你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嘛,俗话都还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嘞。
屈炘靠在吉普车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瞥了一眼一边倒的局面,收回视线,眯起双眼,陷入沉思。他在想是谁会这么急着对自己下手,方琦天?二爷?或者朱八百?还是其他不嫌事大隔岸观火,想坐收渔翁之利的那些家伙?屈炘手一抖,回过神来,他依然没想通是谁会做这些事,却无意间想起了那个粗犷男人是谁。
出乎苏延峰意料的是他太小瞧那个不言不语的沉默男人了,事实上并没出现他想象中那种你给我两拳,我就能还你一拳的画面,而是十几二十个回合下来,他才能找到一个空挡打上一拳或者踢出一脚,却还是没有多大效果,频频处于防守状态的他只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骨头都生疼,以至于后面都渐渐麻木,连带着手上本就疲于应付对手迅猛攻势的动作都慢了下来。
气势如虹的水流找准一个空隙,收在腰间的右手猛然击在对手肋骨上,寸劲瞬间爆发,忍住剧痛的苏延峰一个踉跄,却骇然的发现对手又进到了跟前,最终一退再退的苏延峰被一记刁钻的窝心拳打在胸口,再也没有力气的他躺在地上,胸口剧烈起伏,大口喘息,嘴角挂着溢出的殷红血迹。
本就没有经历过正规训练的他是车头彻底的野路子,对上十几个普通人,没问题,一拳换一拳,他能扛住别人一拳,别人却未必能扛得住他一拳,面对这个从小到大同样一天不间断,训练强度比之不止多一倍的男人,他毫无招架之力在水流意料之中,在屈炘答案之内,却还是让屈炘感到惊讶,竟然可以和水流打这么久才倒下,那是相当不错的。
不同于苏延峰,屈炘作为最亲近水流的一拨人,自然知道水流武力值是有多恐怖,反正他自认就是两个他也干不过水流那个疯子的,在他所亲近的人中,恐怕目前便只有一个南宫庭能力压水流一头,可要知道,南宫庭要大水流十岁以上,就算是赵一,与水流也是半斤八零,在伯仲之间而已。
苏延峰挣扎着坐起身,狠狠吐出一大口带血的唾沫,却因为用力过猛,而牵动断裂的肋骨,倒吸一口凉气。看着若无其事地站在身前的男人,似乎将自己打成这副摸样的并不是他,苏延峰摇头苦笑,自己的确输的不冤。
水流看着坐在地上苦笑的八字胡男人,依然面无表情,没有胜利后的喜悦,平平淡淡,却像一个黑夜中审视自己猎物的高傲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