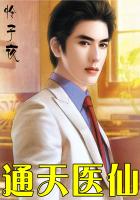SX地下今夜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个心狠手辣的虎子被人一枪送进了医院,生死未卜。那条来自于川蜀道上的过江猛龙被人捅了个穿肠破肚,当场就死在了某个胖子的怀里。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的人,当然都是一些大人物,不至于傻到理所应当的认为过江龙便是死在胖子手里。所以,经过多方打听,就很简单的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缘由。其实,不用打听也能猜想到这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可是有些事是必须知道真相,而不能仅凭猜测的。所以今夜的SX在有的人眼中变得更加热闹、有趣了。当然了,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比如现在的二爷就有些忧虑。
二爷是个清瘦的老头子,上了岁数的脸上多了老年斑,多了皱纹,如果不是二爷身后跟着一位位面无表情的黑衣保镖,就与寻常上了岁数的市井老头儿是一样的不起眼。或许是上了年纪的关系,二爷现在最喜欢的事就是找个茶馆,与三三两两个不认识的老头子一起喝茶聊天,可二爷就是二爷,一辈子拼搏拼出来的二爷,整个SX地下最老最大的土皇帝,只要他不死不退,那便是一座年轻人或许永远也跨不过去的大山。
二爷不曾娶妻,所以没有子女,按他的话说,自己这辈子干的缺德事都把祖上积攒的功德花尽了,要是留下个一儿半女,让他们为自己还债,那就是造孽。二爷不怕报应在自己身上,可他怕报复在自己后代身上,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世上最后的亲人是他早已经断绝关系的侄儿。最后,二爷收了五个义子,陈虎生就是最小的那一个,正应了那句,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陈虎生也是二爷最喜爱的那位,因为他最像年轻时的二爷。
已经宠辱不惊了大半辈子的二爷此时有些忧虑,既忧虑正在抢救的义子,又忧虑这件这件不管如何处理的大事肯定是小不了了。这小子尽给自己找麻烦,自己只是让你把人带来,你不仅把人给捅死,还把自己送进了医院,你就不能干点儿别的,好让老头子我好好过些日子,难道不知道老头子我心脏不好?二爷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自己虽然不惧那条疯名广传的疯狗,可也忌惮那条疯狗真的发疯啊。
二爷招了招手,唤来大义子,吩咐道:“你去警局一趟,把阳局长叫过来。我有些事要给他说。”
大义子王勇点头,沉默出去办事。
二爷哼着小曲儿离开,像似个与任何事无关的闲散老头子,又去继续刚才那盘没有下完的象棋了。
······
一群人在大街上追着一个人,想不被发现那就是奇怪了,况且还闹出了人命。这样如果都不会惊动警察局,那这一片地区的治安可就已经糜烂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而在这里,治安从来不是问题。所以在第一时间内,阳康就知道了这件事。
阳康铁青着脸,听着下属的汇报,微黑的脸上青筋鼓动。下属说的什么他已经听不进去了,却还是大致了解到了,那个无法无天的陈虎生今夜捅死了人。你陈虎生无法无天,小打小闹,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小事处理,你竟然敢越过最后的底线,敢当街杀人,是不是太不把我阳康放在眼里了。真当我阳康不敢把你如何了?
局长阳康一拳打在办公桌上,桌上物品一震,拳下出现点点血迹。阳康抬手阻止准备冲过来的秘书,转身离开办公室。阳康记起向父亲的承诺,又记起刚进警校时看到的誓言,再记起包公,纪昀......
我阳康拼掉肩上的肩章不要,也要公事公办,拿你归案。
······
任晓丽揉了揉迷蒙的双眼,缓缓睁开,走到客厅拿起水杯喝水,似想起了什么,抬头看了眼挂在墙上的钟表,已经快两点了啊,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任晓丽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想要打个电话,却还是没有拨出去,肯定是有重要的事耽搁了!任晓丽放下手机,进卧室拿了件厚毛毯出来盖在身上,全身缩在厚毛毯里,就这样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没多久又睡着了,只剩下电视屏幕还兀自亮着。
······
王小攀看着躺在病床上眉头紧锁、不停冒汗的李子道,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扔进已经快要装满擦汗纸的垃圾桶内,看着李子道不停抖动的嘴唇,自己的嘴唇也跟着颤抖起来,似不知如何告诉病床上男子那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尽管他知道他在昏迷中也听不见,可就是不知该如何起唇。
“子道,你知道吧,在你昏迷前,他可是把你托付给我了,所以你以后就得跟着我了,虽然不一定会有跟着他那样精彩,可也不会让你跟着我吃苦,更不会让你吃亏。他以前告诉我说,十年前有个算命先生说你十年后病就会好了,现在算起来,就在近段时间就是十年之期了,所以等以后你好了,让你嫂子给你找个媳妇儿,也好给你们老李家传宗接代,也让我过过当干爹的瘾。”王小攀边给李子道擦汗水边说道,“你小子也别想着能找到有多漂亮的,就你这么大个,就算是有漂亮的也得给你吓跑了,再说了找媳妇儿是找个能过一生的人,又不是选美大赛,要那么漂亮的干啥,几十年后,还不是都一样的满脸褶子了。当然了,你要是能把江浙一带的美女蛇拿下,哥哥我给你包个大红包。所以啊,你好了以后就给我好好活着,安安心心的在这里打下手,别想其他的有的没的的玩意儿,其他事用不着你操心,自然有其他人办,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良久,王小攀从病室里出来,坐在椅子上,从抽屉里拿出红塔山来点上,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雾中的脸上写满了落寞与疲惫。
李子道额头上布满了汗水,两只手紧紧地拽着棉被,颤抖的嘴唇呢喃着没人听得清的话语。
其实他一直在重复着一个字。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