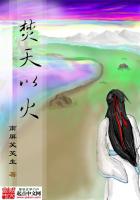噢,可怜的格兰古瓦!在这人心沸腾的庄严时刻,就算圣约翰教堂所有的特大鞭炮一齐炸响,纵使20张连弓弩一齐开火,纵使贮存在圣殿门的所有弹药一齐爆炸,也比不上从这个监门的嘴里掉出的“波旁红衣主教大人到”这寥寥数字,更强烈有力地把格兰古瓦的耳朵震聋了。
这倒不是皮埃尔·格兰古瓦畏惧或低看红衣主教大人。
他沉着冷静。正如现在人们所说的,“真正的折衷主义者”,为人崇高坚强,温和恬静,一贯恪守中庸之道,富于理智而又信奉开明的哲学内容,并非常重视七德。若是我们绞尽脑汁能恢复皮埃尔·格兰古瓦应得的名誉,他或许是15世纪哲人的楷模。
所以,皮埃尔·格兰古瓦对红衣主教大人出现的不愉快印象,既无仇视,也不轻看。与之相反,我们这位诗人对人情世故太重视了,自然会格外重视他所写的序诗里那许多暗喻,尤其是对法兰西雄狮之子——王储——的颂扬,能让万分尊贵的大人亲耳闻到。然而,在一切诗人的高尚心灵中,占支配地位的并非自私自利,而是那种虚荣心。现在,在那道门为红衣主教大人打开的空隙,格兰古瓦的那种虚荣心,被民众的赞誉之风一吹,一下子膨胀起来,浮飘起来,其迅速扩大的程度简直不可想象。话说回来,私利是无价之宝,由现实和人性融合的压舱物。要是没有这压舱物,诗人是无法脚踏实地的。且说每当剧中的婚庆赞歌各部分一出现无以伦比的宏论,全场观众——固然都是平民,但又有何妨!——无不为之瞠目结舌,如醉如痴。格兰古瓦感觉到、目睹到、甚至可以说触摸到观众的这种热烈的情绪,完全迷醉了。因此,红衣主教突然大煞风景的驾到给格兰古瓦造成的感想如何,我们现在便可想而知了。
他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主教大人一进场,全场顿时骚动起来。人人把脑袋转向看台,异口同声地接连着喊道:“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别的再也听不见了。可怜的序诗再次被拦腰斩断了。
红衣主教在看台的门槛上稍作停留,目光很是冷漠,慢慢地巡视着观众。这的确是个伟大的人物,看他比看其他任何戏剧都有价值。他,查理,波旁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和伯爵,高卢人的首席主教。他的兄弟皮埃尔是博热的领主,娶了国王的长公主,因而红衣主教的大人与路易十一是姻亲,他的母亲是勃艮第的阿妮丝郡主,因而与勇敢的汉查理也是姻亲。然而,这位高卢首席主教,独具一格的显著特征,还在于他那种朝臣的气质和对权势的顶礼膜拜。
入场这后,红衣主教脸上露出大人物与生俱来的对待平民百姓的那种微笑,向观众致意,然后似有心事地缓步向他的猩红丝绒坐椅走去。
红衣主教现在确实有着一件烦心事,这就是弗朗德勒使团。
不只是由于他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也不是由于他在操心表妹勃艮第的玛格丽特公主和表弟维也纳的储君查理殿下的这桩婚事会有什么结果。奥地利大公与法兰西国王这种名存实亡的亲善关系能维系多久,英格兰国王如何看待自己的公主被人低看,这些红衣主教大人并不放在心上,每晚依然畅饮夏伊奥的王家美酒,却没有料到正是这种酒(当然是经过库瓦蒂埃医生稍加检验并改变其成分),日后路易十一热情地赠送了爱德华四世几瓶,忽然某天早晨它竟替路易十一把爱德华四世除掉了。奥地利公爵大人万分崇拜的使团并没有给红衣主教带来任何这类的烦恼,而是从另一方面使他心烦。在本书的前面已约略提到,他,波旁的查理,却不得不欢宴和盛情款待这班毫无名气的小市民。凡此种种,叫红衣主教大人怎么能够忍受!诚然,这也是为了讨好王上,他平生最恶心的一次故作姿态罢了。当监门通报奥地利大公的特使大人们驾到时,红衣主教随即转身朝向那道门,摆出一副极其优雅的架势(这正是他的绝活)。不用说,全场观众也都回头望着。
这时候,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的48位御使驾到了,为首的是笃奉上帝的神甫、圣贝廷教堂的住持、金羊毛学院的学政约翰,还有根特的最高典吏雅克·德·古瓦即多比先生;他们一个一个走进来,个个都是一副严肃的神态。大厅里顿时一片寂静,但窃笑声随时可听见:这些宾客都一个个向监门自报姓名和头衔,监门再把他们的姓名和头衔胡乱通报一气,再经群众七嘴八舌的一传,就完全驴唇不对马嘴;大家一听到那一个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和种种小市民的头衔,忍不住都悄悄笑了。这些人都个个身体挺直,装出正儿八经的样子,每个人的额头上都仿佛镌刻着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连在谕旨中所说的话:他有理由完全信任他们,深信他们的理智、勇敢、老练、忠诚和高尚品德。
然而,也有一个人例外。此人长着一张睿智、狡诈的面孔,兼有猴子般的敏锐和外交家相貌的一种面容。红衣主教一见,马上上前三步,深鞠一躬。其实,此人只不过是根特市的参事和靠养老金过活的纪约姆·里姆。
此人是何许人也,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此人可是旷世英才,若处在一个革命时代,准会大放光彩,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在15世纪,只能是暗地里搞些诡计罢了,如圣西蒙公爵所说,在破坏活动中生存。此外,他很受欧洲第一号破坏家的赏识,同路易十一合搞阴谋关系密切,经常参与国王的秘密阴谋。这一切,当时的观众全蒙在鼓里,只是看见红衣主教对这个满脸病容的人物那样崇敬有加,感到非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