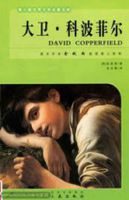“可耻而又讨厌,讨厌而又可耻,”聂赫留道夫一路上反复在想着。刚才他同咪茜谈话时的难过的心情到现在仍没有驱散。他觉得,他对她是没有任何的过错的:他从来都不曾对她,从来也不曾向她求过婚,但是事实上他觉得他们已经拴在一起了,他已经是答应她了。但是今天他却从内心感觉到他不能跟她结婚。
“可耻而又讨厌,讨厌而又可耻,”他还在不停地对自己说这样的话,这不仅仅是指他和咪茜之间的关系,而是指所有的事情。“一切都是讨厌而又可耻的,”他来到自家的大门口时,又暗自重复了一遍。“我不吃晚饭了,”他对听差柯尔内说,饭厅中已经摆上餐具和茶了。“您去吧。”
“是,”柯尔内说,开始去拾掇饭桌上的那些餐具。他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来打扰他,让他独自清静一下,不过他感到大家似乎又都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偏偏要纠缠他。等到柯尔内走开以后,忽然听到阿戈拉菲娜·彼得洛芙娜走路的声音,他赶紧匆匆进了客厅,又顺手带上房门,免得看见她。这会儿,这个被灯光照得明亮的房间,有两盏装有反光镜的灯,一盏照在他父亲的画像上,另外一盏照在他母亲的画像上面,于是想起了他同母亲在最后那段时间情形,他觉得他们关系很是不自然、令人憎恶。同时也是讨厌和又可耻的。在她生病的最后那些时间里,他真恨不得她死掉。他也曾告诉自己,想让她死掉是为了叫她早日摆脱那疾病的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免除他自己的痛苦。
他希望能在自己的心中唤起有关她的美好的记忆,他瞧了瞧她的那画像,这是花了五千卢布请了一位著名的画家画的。在画里,她身穿着黑天鹅绒连衣裙,裸露着前胸。这显然特意要充分描绘两个乳房中间的胸部和美丽迷人的肩膀和脖颈,这是非常可耻而又讨厌的。他把他的母亲画成半裸美女,这真叫人憎恶。更令人难堪的,是三个月前,这女人就躺在这间屋子里,干枯得像木乃伊一样,整个房间都充溢着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他甚至在此刻还闻到了那种讨厌的味道。她临终前一天伸出那只枯瘦的、发黑的手来,抓着他盯着他的眼睛说:“如果我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别怪罪我,米佳,”她那因为痛苦脸上竟涌出了泪水。
“多么讨厌!”他望了望那个半裸体的女人,及十分美丽的、像大理石一样的双肩和胳膊、得意的微笑,自言自语地说。画像里裸露的胸部又让他想起了另外的女人,她也这样裸露过自己胸部,她就是咪茜。有一天黄昏她要他到她的屋里去找她,让他去瞧一瞧她参加舞会时服装的样子。他怀着厌恶的心情想到了她那白嫩的双肩与胳膊。另外还有那个粗暴的、像野兽一样的父亲及其经历和残酷,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人反感,可耻、讨厌、耻辱。
“不行,”他暗自想道,“一定要摆脱掉这一切,摆脱掉所有这些虚伪的关系……是的,必须自由自在地呼吸。我到国外去,到罗马去,从事自己的绘画……”,“先去君士坦丁堡,再去罗马,必须尽快地辞去陪审员的职务,同时和律师把那个案件商量妥当。”
突然间,在他的想像之中那个女犯的影子和那双稍稍有点儿斜视的黑眼睛又浮现出来。在法庭上,她哭得是那么伤心!在他的脑子里,他和她们一块儿度过的那些景象,又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呈现了出来。紧接着他想起自己当时是个焕发着朝气、风华正茂、生活充实的年轻人,他情不自禁地难过极了。
那时的他与如今的他,判若两人。怎样来了结他和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之间的这层关系,他和她的丈夫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他不至于害臊得没有勇气去正眼瞧那个丈夫和他的孩子们?怎么才能不用做假的方式结束他和咪茜的关系呢?怎样才能从这些矛盾中解脱出来呢?应当怎么做又才能在卡秋莎面前补救他的罪过呢?“我不能抛开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把她从原本就不应该承受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我不能仅用金钱赎罪,不能像我当年给她那笔钱时,自以为干了一件应当干的事一样。”
于是他想起当初他在过道里追赶上她,将那笔钱硬塞到她手里,接着从她身边跑开的情形。他也像那个时候—样高声地叫了出来。“只有流氓、无赖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来!我,我就是那种无赖呀!那种流氓!”他大声嚷道,他止住了脚步,“难道我确实是无赖吗,难道我的的确确是无赖?但如果不是我,那又是谁呢?”他自问自答。“难道你和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还有她丈夫的关系就不卑鄙,不低俗吗?你对财产的态度呢?你觉得拥有财产不合理,但是又借口说钱是你母亲遗留下来的。还有你那无所事事的、卑鄙无耻的整个生活。你这个无赖,流氓!随他们怎么评论吧,我可以欺骗他们,但我无法再欺骗我自己。”
他恍然大悟,原来他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对所有人所产生的厌恶,事实上就是对自己的厌恶。
聂赫留道夫生来曾多次发生过所谓的“灵魂的净化”。
这样的情况,已经有过很多次了。那年夏季他在姑姑们家,是他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那曾是一次最生动、最令人兴奋的觉醒。那次觉醒一直持续了很久。事后,在战争时期,他放弃了文职,参加军队,在不惜牺牲生命时候,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觉醒;但是,这一次他的灵魂不久就被污垢所积满了。以后还有过一次,那是在他退了伍之后,出国从事绘画的那时。
从那以后,他已有相当长时间没有净化灵魂了,因此他从来都没有像如此肮脏过,他的生活之间也从来不曾像这样不协调过。这使他常常心惊胆战。这差距这么大,积垢那么严重,他丧失信心了,觉得再不可能洗干净了。
“无论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也得把束缚着我精神的虚伪给撕破。我要对所有的人都说实话,做老实事,”他下定决心对自己说道,“我必须对咪茜讲出真话,说明白我是个放荡不羁的人,没有资格娶她,给她添了麻烦。我必须对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也讲真话。我必须对她的丈夫说,我是个无赖,我曾骗了他。对于遗产,也必须处理得合乎真理的准则。我一定要对卡秋莎说,我是个无赖,是我对她犯了罪,我必须尽我所能来减轻她不幸的命运。是的,我必须去见她,请求她的原谅。”
“是的,我必须像个孩子一样请求她的宽恕,”他停住了脚步,“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干脆和她结婚。”他,像他小时候的那样,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抬眼向上看,对上帝说:“主啊,帮助我吧,引导我吧,到我的心里来住下,清洗我身上所有的污垢吧!”
存在于他心中的那个上帝,已经在他的意识里又苏醒了。他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所以不仅感到自由、胆量、生活的乐趣,而且感觉到了善的力量。此时,人们能够做的一切最美好的事情,他感觉自己如今也有能力做到了。
他眼中噙着泪。他即喜又悲:之所以喜,那是由于精神上的上帝如今却在他的心中苏醒了;之所以是悲,那是悲伤的泪水,被自己美好的品德所感动了的泪水。
他感到了全身发热。他来到了一个已经卸掉冬天套窗的窗口,打开了窗子。
他望着月光下的花园和屋顶,望着杨树的荫影,吸进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
“太好了!太好了,我的上帝,这太好了!”他说,这是指他内心深处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