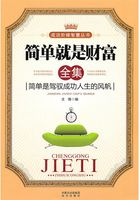夏天的晚上,月光总是十分明亮,照在湖面上,树梢上,草尖儿上。草丛里的虫鸣,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种、多少只,长一声短一声,不肯或歇。那也许是因为,它们所有的生命,长不过这一夏。
嘉敏也不知道这一觉睡了有多久,像是很久很久,久到人生出怠惰之心,不愿意醒来。
迷迷糊糊中,恍惚有人在说话,只是那声音时远时近,倒是空气里的甜香更为清晰,死死地,有些陌生,有些熟悉。
是……什么香呢?沉香?不不不,比沉香要轻;龙涎?不不不,没有龙涎的腥;龙脑么?又不及龙脑悠长,反而微微的涩。也许是一种花,或者草。
白昙两个字,突兀地冒了出来。
是它、就是它!嘉敏皱了皱眉,原来是白昙香。她已经很多年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它让她觉得烦恼,还有隐隐的恐惧。应该叫曲莲换掉它,马上、立刻!这个念头这样强烈,奈何出不了声。
——人在半睡半醒的时候最为软弱,软弱到不能动弹,不能言语。
“阿蛮,这次王妃住得可久!”清清亮亮,像是一汪水。谁在说话,这个声音,像是在哪里听到过。是谁呢?更耳熟的是“阿蛮”两个字,那像是一个曾经在她身边出现过,而且颇为亲近的人。
那又是谁呢?嘉敏苦苦地想,苦苦地抓不到风的尾巴……如果记忆是风的话。
“可不是!”阿蛮的声音有些软,许许叹息:“有半年了吧。老往宫里跑,府里的事全然撒手,难怪王爷不喜。”
南平王妃进宫的次数确实不少,但是父亲可没有抱怨过。当然咯,他常年在外,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嘉敏想,何况进宫,意味着有宠于太后,那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不喜?
这到底是哪家的婢子,说话这么奇怪——曲莲呢?
“你家王爷还能对王妃不喜!”之前说话的人笑了一声:“我虽然不常出门,也知道南平王父子如今权势熏天……”
怎么又扯到父亲和哥哥了,嘉敏混乱地想,倒没觉得别人说她父兄权势熏天有什么不对。
“话不能这么说,”阿蛮叹了口气:“不然你倒是替我想想,我家王妃到底为什么见天地往宫里跑?”
“那还不是皇后!”那人笑道:“皇后和你家王妃可是打小一块儿长大的。皇后又没个得力的娘家。这洛阳城里哪个不知道,皇后是把你家王妃当亲妹妹待,就、就和当初太后待南平王妃一样罢。”
“不、不、才不一样!”迷糊中的嘉敏并不知道皇后是谁,王妃又是谁,却是本能地在心里大声驳斥。
但是要她去想什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却是想不出来。
而那个叫阿蛮的少女却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应了一声:“……那倒是。”
夏虫又响了起来,一些悉悉索索的声音,支离破碎,支离破碎的还有月光。阿蛮忽然又叹了口气,心事重重地:“进宫里来也好。”
宫人竖起了耳朵:“你不是说,你家王爷不喜?”
阿蛮婉转看了她一眼:“你没听说么?”
宫人娇笑着推她:“我们宫里人,哪里能知道外头的事儿,从前倒是听人念叨过,说你们王爷和王妃成亲,可动了老大阵仗,整个洛阳都轰动了,说是南平王倾其所有,把王妃给气了个够呛。”
“那有什么用啊,”阿蛮仍是在叹息:“你难道没听说过,我们府上有个苏姑娘么?”
“苏姑娘”三个字,其实阿蛮说得比哪个字都轻,哪个字都远,远得就像是虚无缥缈一把星光,但是嘉敏偏偏就听清楚了。
那像是魔咒解除,又像是新的魔咒,从心口那个位置瞬间蔓延到四肢。她动不了,她哪儿都动不了,包括她的脑子。但是偏偏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她们说的那个王爷,是宋王萧南,那么王妃——王妃是谁?
“皇后和你家王妃可是打小一块儿长大的”——打小一块儿长大的,又是谁?
是、是、是她。
嘉敏觉得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当然那不是真的,但是口鼻间确然充斥着白昙花的香。她讨厌这种香,因为从前她每次进宫,贺兰初袖都会为她准备,她说白昙香甜暖,能让她睡得安稳。
那倒是真的,所以……萧南送她进宫的那些时候,她沉睡的那些时候,这个世界到底发生过什么?
“曲莲!”嘉敏用了全身的力气,只为迸出这两个字:“曲莲、曲莲!”
起初只有虚软的气息,到后来微弱的声音,再后来……终于惊动了人:“王妃?”那个叫阿蛮的少女的声音。
嘉敏慢慢睁开眼睛,近在咫尺,是个十五六岁的小丫头,乌油油的头发,梳的双鬟,鬟上斜插一支小鱼衔玉钗,倒也别致,肤色干净,眉目生得十分俏丽,并不美艳,像是个小家碧玉的光景。
像是在哪里见过……她一定是见过的,就像阿蛮这个名字一样熟悉,嘉敏恍惚地想,就听阿蛮问道:“王妃要喝水么?”
话音才落,手腕上就是一紧,阿蛮吃痛,几乎没叫出来。待看到女子眼睛里凶狠的光芒,连腿都一些发软:“王、王妃?”
“你叫谁王妃?”嘉敏粗声问。
“王、王妃你怎么了?”阿蛮声音里带出哭腔:“王妃是、是魇着了么?”
门外宫女听到里间有异,微提了声音问:“阿蛮?”
红罗云金帐中阿蛮与嘉敏大眼瞪小眼,好一会儿,听外间催问得急了,方才怯生生应道:“无……无事。”
“无事就好。”宫人自言自语道。
阿蛮已经急出了一身汗,低声又问道:“王妃是魇着了么,还、还是……”可千万莫要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
嘉敏看懂了她的这个眼神,心里却是想道:可不是魇着了,她好端端的进宫赴宴,好端端地夜宿玉琼苑,曲莲守着她,怎么就到了这里——这是哪里?她到这会儿才想起来打量四周。
这是宫里,无论头顶精描细绣的红罗帐,还是帐中垂下来幽幽吐香的缠枝镂花银熏球,还是帐外婆娑的灯树,隐隐可见的美人屏风,每一样东西,都在暗示她,提醒她,这不是别处,就是宫里,就是……她曾经长住过的地方。
在前世。
岁月是条奔腾的河流,记忆是河底的沙,有时松软,有时坚实。松软到不经意间,一个眼神,一缕风,记忆就翻腾上来,历历在目;坚实到你上穷碧落下黄泉,有时候也想不起,何时初见。
嘉敏前世最后一次进宫,距离如今,参差有十年。
嘉敏到她身边要更早一些,在甘草、竹苓、半夏、曲莲几个先后离开之后,苏仲雪挑过几个婢子送来,模样、性情都很看得过去。但是嘉敏不信她,原样又送了回去,她后来的侍婢比如阿蛮,是贺兰初袖从宫里给她挑的。
贺兰初袖挑的人,自然千伶百俐,无不顺心的。
后来……忽然就不见了。
嘉敏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是跟贺兰初袖南下了,这个可能性并不大,贺兰初袖仓促南下,不会带太多的人,论心腹,还轮不到她。所以大概是死了,或者自己走了。嘉敏没有看到她的结局。
如今,却还活生生地跪在面前,满目惊惶:“王……妃?”
那都是前世的事了,这一世,一切已经不一样了,她为什么、为什么还叫她王妃?曲莲呢?
“曲莲呢?”嘉敏问。
“曲……曲莲姐姐?”阿蛮吃力地吞一口唾沫,目中惊惶之色愈浓:“曲莲姐姐犯、犯了事,被逐、逐出府了,王妃、王妃要见曲莲姐姐么?”
曲莲已经被逐出府了,那半夏呢,甘草呢,竹苓呢,还有……嘉言呢?嘉敏脑子里有些混乱,不知怎的,忽然就跳到了嘉言、还有王妃,还有……父亲和兄长,一阵绞痛:“几月了?”她忽然就喊了起来。
几、几月?阿蛮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八、八月了,王妃要喝点水么?”
八月、八月了。
“几年?”嘉敏一把揪住试图后退的阿蛮:“现如今是正光几年?”
“三年。”阿蛮抖抖索索地回答:“已、已经不是正光年了,如今年号是孝昌。”
孝昌三年,八月……孝昌三年,八月,孝昌三年,八月!六个字在脑子里轰隆隆地,轰隆隆地响,碾过来又碾过去,把所有,所有的东西,时光,记忆,命运,都碾了个粉碎,冷汗从额上滚落下来。
手上不知不觉地松懈,阿蛮趁机退了几步,说出最后一句话:“今儿十七。”
嘉敏猛地站了起来,下了榻往外走。
“王妃哪里去?”阿蛮在背后喊。
嘉敏没有应声,她像风一样,没头没脑地往外走,才走了不过三四步,就听得一声悠长的通报:“皇后到——”
有人跪下去行礼,有人打起帘子,有人抬起头来,映入她眼帘的,是个二十出头的丽人,白衣红裙,鹅黄色披帛,帛上牡丹花开,裙底金丝银绣的百蝶翩翩,梳的灵蛇髻,髻上金钗十二行,行行有不同。
然而嘉敏只看到了她的脸。
再过三生三世她都不会忘记的一张脸。
“三娘这是怎么了?”她说:“又和谁怄气了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