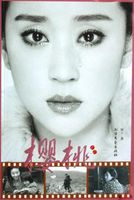春末,在小俏的梦境里面开始经常出现丁城城消失的那个十字路口,常常是红绿灯已经灭了,只有黄灯在独自闪着,有时候路口也没有人,只是长时间地闪着灯。然后小俏就会突然醒来,在潮湿的被子里面喘着气,注视着外面将要亮起来的天空,麻雀在叫了,她极度地怅然若失。
她总是反复地想起那些夜晚,丁城城消失在十字路口的样子。
傍晚临近的时候,天空散发着沉闷的红颜色,丁城城从老虎窗里爬了出去,爬过瓦片搭起的屋顶,坐到房梁的上面,抽烟。从屋顶上望出去,远处是一片连绵的低矮的红砖房子,下午晒着的棉花胎被陆陆续续地收了回去,一些水淋淋的衣裤晾在竹竿上,被风吹得动来动去,下班的人拎着装蔬菜和鱼的黑色塑料袋从自行车上跨下来,丁零丁零的铃声从这一头响到那一头,接着就是哗啦啦的淘米声,一会儿油煎带鱼的香味就从一些颜色模糊的窗户里冒了出来。向远望去,高楼上玻璃的反光在傍晚变得柔和而悦人起来。
再遥远一点的地方,一些不知道名字的鸟在昏红的天空里紧贴着树林呜叫。再再遥远一点的地方,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明,食草恐龙在缓慢地步行。
这一片的房子是已经划入市政规划的范围内的,就快要被拆掉了,拆迁的通知已经下来两年了,到了这一年估计是拖不过去了。那些阿婆们每天都坐在弄堂里面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说着搬迁的去向,年轻人都在心心念念着想要快点离开这一片潮湿、容易发霉、又容易生长虫子和老鼠的石库门房子,而老人们都是在这里生活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所以白天他们坐在房门口的时候,被太阳晒着晒着,眼眶也会湿润起来。
这片房子也呈现着一种心不在焉的状态,电视台过来拍摄过几次,说是要做一个跟踪采访的纪录片,想来也是一个骗人泪水的东西。丁城城家将要搬去的地方是地铁的最后一站,坐地铁会经过锦江乐园,看到巨大的摩天轮。
“城城,死到那里去了,有电话找。”
丁城城迅速地揿灭手里的烟屁股,把半包瘪塌塌的牡丹塞进了牛仔裤的口袋里,从老虎窗重新钻进了自己的房间,接起电话。
“喂,晚上出来吗?”是二乔。
“嗯,老地方。”
咸肉冬瓜汤的味道从煤气上慢慢炖着的煲里面漫溢了出来,丁城城从床底下抽出滑板,用棉布缓慢地擦拭着,然后又从抽屉里面找出护腕和护膝塞进包里面,再从架子上抽出一张收音机头乐队的唱片放进随身听一起塞进了包里,滑板夹在手里面,重重地踩着潮湿腐烂的楼梯下楼去。走进厨房,随便盛了碗饭,把冬瓜汤倒在饭里面拌了拌,呼噜呼噜几口吃完,说了句:“出去了。”就闷声不响地走了。
背后母亲的骂声已经完全隐没在唇齿间一股清爽的冬瓜味道中。
这会几天色渐暗,长长的弄堂呈现出一种晦涩的灯光,但空气清新潮湿,眼看夏天日渐日近。丁城城只穿了白色的长袖汗衫和一条日本裤型的小宽松牛仔裤,仿制阿迪达斯的复刻版运动鞋,这是他出去玩滑板的行头。玩滑板的聚集地是在中心广场,那里场地宽阔,又有台阶和栏杆这样练习技巧动作所必须的东西,而且每到晚上总有三三两两的女孩子在那里观看,某人很有可能在某天晚上成为某人的女友,这种事情总是年轻人所热衷的。
而丁城城想做的只是在夜晚的广场上,急速地穿行,跳跃,跌倒。
他是熟悉跌倒的,在暗色里骨头迅速地与地面碰撞,渐渐地他就不再恐惧了,他能够充分地享受跌倒前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好像所有的细小的血管都摔裂了,爆炸了。
“嘿,最近没怎么见你,在做什么?”二乔走过来递了根烟给坐在台阶上的丁城城。
“我快要期末考试了。”
“咳,你能毕业吗?”二乔笑嘻嘻地拍拍他肩膀。
“我没想过。”
“你还在想着摩托车呢,别做你的车手白日梦啦。”
二乔躺下来,靠在台阶上玩弄着一次性打火机。
“去你的!”丁城城有点激动。他站起来,跨上滑板,加速加速,然后跃上台阶,轮子在夜色里摩擦水泥地的声音孤独而脆弱。他知道那种感觉,在夜晚的马路上面,耳朵在头盔里面听不到轰鸣的声音,身体和速度是一体的,身体就是速度,完全合二为一。
眯子已经买了两瓶矿泉水坐在边上的台阶上等待丁城城,她就和在这里坐着的少女一样,染着淡黄颜色的长卷发,蓝色的眼影和食指上面硕大的葵花戒指。
她把水瓶的盖子拧开,安静地坐在一边,心满意足地看着滑板上的男朋友。他们就是在这里认识的,认识了以后就很快地开始了恋爱,眯子每天都会捧着矿泉水的瓶子坐在这里等他渴了过来喝一口。
而当丁城城像往常一样搂着眯子的腰走在夜色下宽阔的马路上回家,街灯恍惚地亮起来时,他又感到无聊,无聊透顶了,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兴奋的,除了在飞速地前行着的时候,其他时候他都感到无聊,恋爱也是无聊的,一些机械的哄女孩子开心的话,一些告别吻或是时常有机会的抚摩,或者那些事情。
和眯子分手的时候,眯子说:“明天你来我家吗?”
“明天再说吧。”
拥抱的时候他听到遥远的地方有群鸟蜂鸣的声音,那么刺耳,那么遥远。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一种三五式座钟的滴答声在底下母亲的房间里响着,有时丁城城并不太明白母亲一个人睡在空旷的房间里,伴着这个座钟度过的夜晚是什么样子的。
母亲已经把他换下来的牛仔裤洗了,半包牡丹牌香烟被从裤子口袋里面掏了出来,现在就摆在台灯下,里面剩下的几根香烟已经全部被扭断了。
丁城城把电脑连上了网,胡乱地去几个常去的网站兜了一圈,看看MSN上的在线好友名单是空的,所有的人都显示着away状态,烟都没有了,他有点难受,习惯性地连上收藏夹里的色情网站,随便荡了一些小片段下来,把喇叭里面的声音关掉,慢慢地重复地播放着,看着里面模糊的女人的身体,他开始打飞机,打飞机的时候他静悄悄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从老虎窗看着外面沉闷的天空,这时候实在是太安静了,可以听得到窗外樟树和女贞细小的叶子在风里面晃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美好得不得了,他好像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又到了那里,风清云淡,后来他就睡着了,睡到凌晨四五点的时候突然醒过来,爬到晒台上的水龙头边上去洗内裤,哗啦啦的水声里看到路灯慢慢地熄灭了,天色渐亮,扫街的人把夜晚凋落的树叶和花朵扫进了垃圾车里,对过人家的老太太出来刷牙,发出咕噜咕噜的漱口声音。丁城城把内裤晾在晒台的铁丝上,光着屁股重新爬进被窝里面去,一努力就睡着了,甚至开始做梦了。
之后整整一个礼拜丁城城都没有去过眯子的家,白天眯子发短消息给丁城城他也不回,他常常希望自己是消失的,谁都看不到他,变成一个隐身人。他厌恶在家里面,妈妈总是没收他的香烟和打火机,所以他把香烟藏在屋檐上的瓦片下。这会儿下雨了,他好不容易狠下心来买的一包红盒万宝路已经全部被淋湿了。丁城城的心情很差,他没有办法出去玩滑板,也看不进去书。雨水落在地上,弄堂的石头路就好像是翻着白肚皮的鱼一样死气沉沉,弄堂里所有的人到了雨天都好像是隐遁了。从对过的某房间里传出断断续续的钢琴声,电风扇也在单调地旋转着。天已经变得黑沉沉的,这是他所熟悉的无数个春天的模样,沉闷和无限漫长,总有一些过去的事情随着和煦的风一起吹进屋子里面,想抓却又徒劳地抓不着。
丁城城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听着屋檐下两只躲雨的鸽子发出的咕噜的声音。这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肯定是眯子的,他懒得接,可是铃声执著地响了三下以后,他听到楼下妈妈窸窸窣窣地爬起来穿拖鞋的声音,才一把抓起了电话,听到眯子的声音,他终于还是变不成一个隐身人。
“干吗这几天一直这样躲着我?”眯子有点委屈。
“没有,最近挺忙的,这是真的。”丁城城再次躺回床上去。
“来我这里吧。”眯子再次说出这句话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外面的雨很大啊。”丁城城迟疑着。
可最后他还是去了,他拎着鞋子摸索着走下楼梯,轻轻掩了一下门就出去了,路上湿漉漉的倒映着人的影子。眯子不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她在一年前就已经退了学,和两个女孩子一道在地铁商城里租了个小店面卖外销的衣服和各种首饰。
半个小时以后丁城城就按响了门铃,眯子穿着娃娃头拖鞋来开门,脸上白天化的浓妆已经卸掉了,露出鼻梁上面一点点的细小雀斑和睡衣里两条纤细的胳膊。她沉默着给丁城城开了门,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碗冰冻的糖番茄来摆在茶几上看他一口口吃掉,就如同坐在台阶上捧着矿泉水瓶子等他过来一样专注。然后俩人都不知该干点什么,眯子用手指甲不停地画着茶几上的木头纹路,嚓嚓的。丁城城舒展着双腿坐在地上,紧紧闭着嘴巴,一种可怕的沉默在俩人之间蔓延。
最后丁城城觉得该做点什么,他移动到眯子的身边,开始如同往日般地抚摩她的背脊,熟悉地亲吻她,解开她睡衣的扣子,循序渐进地进入她的身体,然后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你快来月经了吧?”
“嗯。”眯子突然感到凄凉,她半闭着眼睛,看着丁城城歪斜在一边的脑袋。最后他终于气喘吁吁地躺在眯子身边的地毯上,注视着窗外缓慢流动的暗色里的云朵。
“你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算是什么?”眯子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我现在算是你的女朋友吗,还是只是你的多夜情?”
“啊?”丁城城假装没有听清楚她在说什么。其实他已经懒得说话,此刻那么安静,他只想躺着,看着窗户外面的云朵。而眯子却开始说个不停:“你这样算什么?你两个星期没有打过我电话,我发消息你也从来不回我,你还不愿意碰我了,你不喜欢我了你就说啊,我也不会死缠着你的,可是你这样算什么?你说话呀。”见丁城城依然不说话,她把肩膀缩成一小团开始哭了,一开始哭的声音很小,后来忍不住剧烈地抽泣起来,身体也蜷缩起来。丁城城不能再装作没有听见,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从背后抱住她。
“你不要乱想了,不要乱想了。”他是害怕女孩子哭的,最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