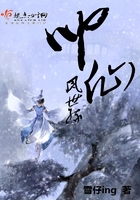次日,有风,天上阴霾,怕要下这场年末雨,路上行人匆匆忙,只见那灯笼对联窗花,当真红火闹腾气。
张随风见了骆宾武,只见得一花白头发老头子,亡了师,一夜白了不知多少发。陈不知眼红,昨夜未睡,熬了通亮。见了张随风,还不知那恩人仙去,闻了骆贤人悲天泪,才明了这回事。陈不知一夜拍头数十次,“陈不知啊陈不知,你枉读了几十载无用书,早该想到了,你可当真不知。”
张随风上前扶了骆宾武,见得心酸,道,“师兄啊师兄,你这一夜白头,我可就真不该来你这书院,倒是害你这般悲苦。”
骆宾武摆手,神色凄凉,勉强挤出一丝欣喜,道,“走吧,见师父去。”
云山,江南道西去五十里,张随风脚力行了三日,坐了马车,只消半日光阴。这元宵近了,赏林的少了,今年未下雪,光了山林子,也没啥可赏不可赏。上云古道,弯弯曲曲去那云山头,上去千米,也就到了峰顶。
池塘,茅屋,竹林,待张随风等人到了云山头,已是下起毛毛雨,江南本如此,如那深闺的妇人,多愁善感得紧。骆宾武随行的两个仆从,急忙递来油纸伞。张随风不接,陈不知不要,骆宾武不理,那两人只得撑了伞,遮自家主子,却也遮不了多少。
一座土坟头,一坛老药酒,碑上几个大字:半仙,笔万机之墓。孤零零立这云山头。
骆宾武自那仆从背的箱中抱了两坛杏花酒,不够,又抱两坛,来回三四次,衣服已然打湿。
张随风上前,自那仆从手里取了一把油纸伞,招呼两人离去。张随风撑伞,遮那骆宾武。陈不知立边上,玉人扇不摇,八字胡不摸,盯了那碑上名字,入神了。
“师父呐。”骆宾武磕头,也不数多少,头沾了污泥,不管,衣物打湿了水,不管。陈不知欲上前扶那骆贤人,见得张随风摇头,只得心里叹息。
自家人知自家事。张随风听着骆宾武头碰在地上,见着泥水溅得飞起,要说心里滋味,不知比陈不知苦了几倍。然张随风不拉,不敢拉,不忍拉。师父,徒弟,看着这已然名动东阳王朝半百年岁的骆宾武,在老头子坟前这般如那几岁童,试问一句,谁人见了不落泪。
张随风撑伞,却是无用,骆宾武身上哪里还有一处干净。足足过了一刻,骆宾武额头冒了血,张随风见是到了时候,丢了伞就扑去,拉住那骆宾武,大喊道,“师兄,够了,够了,老头子听到了,看到了。”张随风沙哑了声,虽说男儿不落泪,却是哪有不动情。
陈不知抬手,要去擦那眼角的东西,却拍了额头,这才想起,这天,有雨。
待得张随风扶上骆宾武,陈不知再前,拜去,嘴里直念,“恩人,不知这来给你送行。晚是晚了,还当喝那离别酒,只当不知孝敬你了。”这文弱书生,也不晓得哪里来的英雄气,提了一坛酒,就往肚中灌。
张随风见了,也是上前,取了两坛酒,一坛丢那骆宾武,一坛自己高举,大口喝,大口灌。待得坛空了,张随风往那地上一摔,然后跪了去,“老头子,你可就乐了,这师兄来了,你予他恩情的不知来了,这杏花酒,可是你来这江南道,最爱的,十坛多了,活了十七年,今儿个,我当好好与你醉一场。”
话音未落,只听得那边骆宾武,咳个不停,如此文人,未进江湖,哪里见过这场面。骆宾武抱了坛子,酒自那山羊胡上下,老泪自那雨水两颊流,“喝,师父,喝,我随你十三年,你骂我十二年,只当我喝不了酒,不配这男儿二字,今儿个,咱们就不醉不归了。”
张随风,骆宾武,陈不知,一个年轻习武郎,一个文斗骆贤人,一个江湖知情客。十坛杏花酒,一场更年雨,云山头上坐,一醉千愁消。
雨住,人醉,虽不知几时,已然夜半。上云古道下,马车之中,两个仆从,早早睡了去。云山头,孤坟前,醉了三人,碎了七坛酒。鸦啼起,那云散了,出落一月,透了月华,落这竹林外。
问这沉浮大地,世人只知,有那么一老人,名笔万机,一代大儒贤,来这江南道,登了云山顶,寻仙访道去。然谁又得见,云山顶上一土坟,自是他的埋骨处。
这夜,见了三人,醉了三人。
张随风梦,嘴角落笑。
骆宾武梦,伸手摸头,咧嘴笑了。
陈不知梦,嘴里糊涂话,“恩人,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