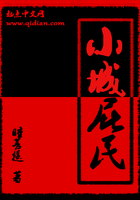张随风离去,天不作美下起了霏霏细雨把这一齐乐宫罩在迷蒙当中。对竹轩里,雨打竹叶落池塘,叮咚叮咚煞是好听。
张随风自也没那兴致去倒上两杯小酒自个翘了二郎腿赏雨吟小曲,金宁在了,这下雨时节本就低迷但也没那么多忙事要做。那赵王府里赵苏婷自个有那些个随身丫鬟伺候着,也劳烦不到这齐乐宫里打杂弟子,不然一张那樱桃小嘴别说齐乐宫里弟子就是从那汪南省城青凤岭跑一些个官赏世家子弟也是不会稀奇。但这就不该是张随风在意的事了,人虽美当赏则赏足了,招惹多了是非红尘恩怨情仇自不好,更何况自家门前雪都未扫干净,怎管得了他人瓦上是霜还是叶。
“张师兄,有话还请说了,静怕打雷,这雨下得好是好了,来了闪电恐怕静一个人待院里要害怕,我该早些回去,”金宁说话始终是那大人口吻,也顾不得与那张嫩白脸儿合衬不合衬,提了金静,嘴里却也带了丝丝笑。
“他怕打雷啊!”张随风望一眼竹窗外,还好雨虽霏霏春雷还没炸响,又望金静,道,“那你怕什么?”
金宁喝茶,这等无聊之谈他不在意,也没那心思,茶水苦金宁也吞了,不像那平常人家几岁娃吵着要吃糖,张随风看得直觉得心里没了滋味。若说金静苦,他吵吵闹闹哭哭笑笑自也正常,若说这金宁苦,成天卑躬屈膝左右逢迎心比身老,张随风说不出一句反驳话。
张随风不卖关子,道,“我今儿个明白了事,这才知了为何我言要带你们出这齐乐宫你没正眼看我,不是你不信,是你太老成了,有些时候我跟你坐一起喝茶如同面对一个长辈一般。”金宁不说话,张随风接着道,“我带不走金静,你知道,齐龙天,齐秋书,他两个模样,你也知道,你有这般心智自个也该多少明了那两个宫主表面带待你们不薄实际如何,你清楚了?”
金宁摆手,“不用说,我都知道,我和静就跟两枚果子一样,瓜熟蒂落也就这般简单。我言报仇你都不信,谁人相信,真个看着那齐家两兄弟老死在这山上?那等至少入了先天的人,我多少从书里看过些许,或许比我和静还能活,这不稀奇。”说完望一眼张随风,从那眼睛也望不出一丝恶意,唯有一阵这少年童子的叹息,“你是好人对我与金静而言,这一天两天看不出来,而今看出来了,我也不骗你,实话认真跟你说道说道。”
张随风提茶壶,倒茶,等这心里装了无数事的少年人今儿个掏一掏心窝子,平常同辈交不分那长幼。
金宁开口,声音清脆却是低沉,这是他本来音色,一个七岁孩童的音色,“宫里那两人暂且不说,先给你讲一讲师兄师弟些。你以为龙榜仅仅那二十人?错了,三年争夺一次龙榜,取一百人,齐乐宫去年收徒一百,前年两百,今年五十。为什么?江湖那些个怕了,怕上了山下不去,但人少自也不能有弱根不然才吃饭无用,所以一个月前那山门外面才有那一出杀人夜。那剩下的去哪里?我不说别说你就是宫里那些个待了五六年的弟子都恐怕不晓得。”金宁说到这里,却是不出声,而是用那小版宫袍里面穿了灰布鞋的小脚往着地下用力踩了踩,小手互相比划了几下,张随风顿时明了。
“你是说他们……”张随风开口。金宁摇头,接着道,“这只是一处,齐秋书这些年来所为之事,我一次悄悄跟去,也管不得他发没发现,我未满十虚岁他自不杀我,半吊子药效和宝药之间多少差距他比我明白。至于齐龙天,他待我和静亲,我却不愿与他打交道,齐秋书狡猾但至少理智,齐龙天?杀人不过头点地,听说宫里那些个他族亲去了,也不过叹了一句齐秋书不是个东西。他要和你装老成,装无辜,你自最好别信,他疯起来恐怕这山门里面没人拦得住。”金宁说,张随风听,但这巴掌大的脑袋里,装得东西却超出了张随风以为的太多太多。
“那你上次让我带金静走?让我赶快了是为何?”张随风想不明白,自然要问,也不觉得在这七岁孩童面前丢了见面。
“水中三色莲,两柱活灵药,赵家二百甲!”金静不多说,只道这三个东西,张随风不聪明自也一点就通,道,“要打架了?”
金静点头,道,“这算一个,另一个,你带静离去,你有免死金牌,静更是不会死,被抓也就被抓了,还在这山上,但却能给我拖延时间。那传道殿内两株数百年老松树,齐秋书没沾染那地下,那地下属于我,一条鼠道,已听得到暗河涛涛。”
“那现在可否行得通了?”张随风听得这里,问上一句,自个离去或许轻松,但这两娃人家锅里肉自不会让到嘴的飞了,早知道能帮早就冒死做戏给人看了。
金宁摇头,“赵家来了,这回是个府主女儿,下回是个什么,什么时候到,说不准,但也快了。平常天黑夜深能去,如今不行,那齐家两兄弟盯得紧了。”
“我当如何,金静,我亲弟!”张随风认真道。金宁黑眼珠子转,隔了半晌抬手,“赴耳过来!”
雨隐人行声,却隐不去那恩怨江湖多少事,云遮天下事,却遮不住这苦命孩童七岁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