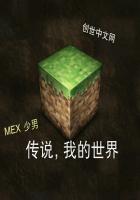十六年正月十五
有唐伯虎的诗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这宫里头怎可落了后,处处是张罗着挂满了各色的宫灯。东西六宫上至妃嫔,下至常在答应皆是一赌诗文,列了灯谜,悬于御花园里头。上头书画了赏钱,宫名,若是猜得准了,便去各路标注的公公那儿领赏钱。宫人们虽不能这般,倒也有他们的趣味儿,剪纸糊花,装点屋子。这元夕过的竟是几分像除夕了。
因是进来皇太后就着兰烨回宫一时暗地里头助着不少,才使得安亲王,简郡王未多几分闲话。福临心下也明白的紧。与孝庄也是亲近起来,故而也好生听得孝庄剖析的更姓一事,再听其言,这兰烨虽是抚顺之女,可到底是鄂硕一手栽培,切不可忘恩负义了。何况那会儿可不就说个门第出身,如此一来,兰烨的门第也就不觉间高了,福临听着在理,遂也依了。
前些日子福临谕礼部要册封其为妃,这消息才不过放出了声儿,福临正是寻思着该要如何热热闹闹的大赦天下,普天同庆。得,镇国公来了,吴克善亲王也到了,配上安亲王,简郡王,如今又添一个佟妃之父,既是他们出面,后头自然又是紧紧随着些趋炎附势之辈。尽管是各怀鬼胎,矛头却是直直指着一处。
福临龙颜大怒,从前受得这般钳制,险些酿成不可悔过之误,如今旧事重提,这些官员还要阻挠,这说到底不过是皇帝纳一个妃子,后宫佳丽三千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何时轮的着官员来讨论他该是不该了?可就是是因着册封的人不同,竟是这样错综起来。
还又赶上了郑成功来犯……
孝庄只怕在兰烨心中落了芥蒂,三番四次促膝而谈,兰烨自然知晓,想来福临年少气盛,措辞话语,行动举止间都不免心浮气躁了一些,好在兰烨并非争权夺利之士,原本不在意这些虚名,如今能在他左右得一安寝之地,早已心满意足。何况这些臣子又都是大清国济济的人才,更是想着法儿处处宽慰着福临。
既而,这一搁,就又搁下了。
早晨兰烨饮了汤药,照旧是提着皇后和佟妃送来的食点去了乌云珠那处一道用膳,回房时,各宫的赏赐也都已经到了。福临今日与大臣在乾清宫商讨进取云南之事,着实是挑不出时辰过来了,可赏赐仍旧是少不了的,宫人们列队搬进来,大道桌椅板凳,小到珠玉发簪,旁人也都瞧花了眼。
“兰主儿,这东西都齐全了,您瞧瞧,可漏了什么没有?”顺儿这会儿子可是见风使舵,对着兰烨殷勤不已。可从前收了乌云珠那么多些好处,再说乌云珠自打荣登了皇贵妃,也没少待他好的,他心里头还是记着的。“若是全了,奴才这还得去皇贵妃那儿呢。”
“这些东西可是人人都重样儿?”
“那哪儿成那,这些都是万岁爷挑了给娘子您的,单单就兰主儿您一个人有,这是多大的福分。”顺儿低头哈腰,简直要把头磕到地上去了。
兰烨瞧了一圈,指了指几件儿顶精巧的摆设,“你们把这些照着原样收起来,一会儿送去了与皇贵妃,但说是皇上赐的,不可言及与我。明白么?”回身嘱咐了绿翘数语,却是见得她进去取了个匣子出来。“顺公公,您知道皇上他秉性纯良,想什么便就做什么了,您也寻常帮着兜罗着。皇上政务繁忙,没顾着的事儿自然也是有的。我这儿是皇上原先赐的一些小玩意儿,都不曾使得。你拿了去,若是瞧见那个贵人常在的分例少了,便添置些。只说是皇上赏的,好歹别让她们见着别人多的眼红,心里头不快活。到时候闹起来,也不好听。”
“是,奴才都记下了。”顺儿说着谄媚之语,面上的肉都揉成了一团。“奴才告退了。”
顺儿前脚刚走,兰烨便急急收拾了些典当,命了宫女过来,“你把这些东西送了去给唐妃,前阵儿我去探视,她的精神气儿也不好,告诉她六阿哥好得很,叫她别记挂着,皇上前朝的事儿多,一时脱不开身,得了空就去看她。月子里头顶重要的,让她好生养着。”
“让人家养着,你自个儿呢?”乌云珠含笑着进来,发髻上戴着的便是方时福临赐下的翠玉蝴蝶簪。宫女做了揖退了下去。
兰烨赶紧是起身过来扶了乌云珠做了上头,“翘儿,沏茶。”
“你啊,方才落了东西在我那处也是不知,听得底下的人说你告了皇太后今日要出宫去?”乌云珠笑着把一方绣帕递与了兰烨。
兰烨将帕子收入袖中,顺手拈了一旁开的正好的杜鹃花,斜斜插了乌云珠的鬓端,“配上这娇艳欲滴的鲜花,姐姐是更国色天香了。活生生一出蝶恋花了,想来皇上也正是此意才赠此簪子与姐姐呢,虽是忙碌,皇上到底是把姐姐放在心坎儿里头了。”乌云珠的眼中滑过一丝诡异,旋即嬉笑怒骂。“好啊,吃了我的饭,得了气力反过来取笑我了。”两人玩闹了一阵,却是听得外头人来传,说是皇太后困乏,找乌云珠过去说话儿。
两个又是忙活了一阵,一同到了门前,各奔“前程”去了。
过了太和门,出了紫禁城,兰烨下了轿子,吩咐着小路子在这儿候着,自个儿令找了辆马车,只让绿翘随着,扬长而去。
过了东大门,上了东长安街,原来这京城里头也是氛围浓重。绿翘在宫里头憋了几个月了,如今放了出来,探着脑袋到处瞧。
“也不是头一遭出来,怎么今儿这样乐?”兰烨着实忍不住,笑出了声。
绿翘嘟囔着嘴,像是满腹委屈,“主子,从前奴婢在承乾宫里那可是呼风唤雨,如今说话做事还得小心谨慎,可不把人给憋死。”兰烨无奈的摇了摇头,“瞧你说的,不过是添了姐姐而已,那个吴尔库尼,你不去惹她便就是了,那不就还是如常啊。”
“主子,您是不知道她那一肚子坏水,成日里净想着如何教唆人兴风作浪。皇贵妃再留着她,早晚留出祸害!”绿翘合上了窗棂子,“好歹现在出来了,说话儿倒也不必顾忌了,主子,原也不是奴婢瞧不惯她便在您跟前数落她的不是,只是您没瞧见她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奴婢知道您和皇贵妃情深,您能原谅她过去的种种作为,奴婢要再说,反倒像是挑拨离间了。近墨者黑啊!虽说你们情深,主子,您还是防着她些的好。”兰烨微微动容,她知道绿翘斗胆此言也皆是为她所想,在宫中能得此忠心之士,也不枉了。“主子,咱们不是上月老庙还愿去么,怎么上东长安街来了?”绿翘一吐为快之后,放算是撂下了心事,这会儿才想起来,竟是走错了道?
“打这儿过去也成。在宫里谨言慎行,现在出来了倒也不瞒你说,在那老宅子里头成日与山水为伍,事事不知。这会儿回了宫,却总觉着怪异,太妃娘娘分明搬入了襄亲王府,可如今又回了麟趾宫。襄亲王喜好游山玩水不假,如今成了家,平日里更是见不着一面儿,这也说得过去。可今儿个元夕,他也没个踪迹。宫里头的谣传我也不是充耳不闻,若让人知晓我打听襄亲王的事儿,指不定又得闹出什么来。”正说着,马车缓缓停了下来,车门微启,绿翘先行下来,方是回身布起小梯子,让兰烨步行而下。
时光荏苒,王府依旧是从前的模样,便是西墙旁那株黄梅,都如从前一般花开绚烂,无非多了几分苍老之感,兰烨有些踟蹰,间或仰头瞧了一瞧,冷不丁是一个哆嗦,但见匾额之上烫金的四个大字:温郡王府。
“哎哎哎。”绿翘喝住了车夫,“怎么回事儿?襄亲王府呢?”
“您们二位这是说玩笑话儿呢,这儿两年前就是温郡王府了。”车夫鼓囔着,伸出了手。绿翘抛给他一锭银子,那车夫凑近了些,“您们是打哪儿来啊?要是投奔襄亲王那可就没指望了。襄亲王啊,早在两年前就悬梁自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