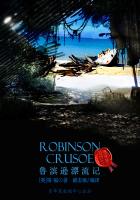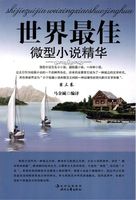县里有个曲艺队,人不多,统共只有十来个,可个个都有把刷子,有个叫张天辈的说书人在里面挑班唱头牌。
张天辈高个儿,腰板儿倍儿直,瘦白脸儿,留一缕花白山羊胡,书说得好,不说十里八乡了,就是在附近几个县都有名气。他人也傲气,整日手里捧个锃亮锃亮的白铜凤冠雕花水烟袋,抽起烟来,咕嘟咕嘟响。那时候抽水烟儿的人不多,可张天辈是角儿,角儿有角儿的气派是不?他就是和别人不同,无名指留有半寸长的指甲,平时修剪得很整齐,爱翘着个小指头用留有指甲的无名指当梳子整理他花白的大背头。别看他整天耷蒙着眼儿,一上台,神采奕奕,俩眼儿炯炯有神,一人千面。那鼓一敲,砰砰作响,极有韵味,让人心痒难耐。鼓声停歇,张天辈嘴一张,字正腔圆,沧桑厚实,台下乱哄哄的场面即刻鸦雀无声,观众跟着他时悲时喜。
这一阵儿他跟前儿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与他形影不离,不知情的以为是他孙女。其实那女子先是迷上他说的书,继而迷上他的人,走哪儿跟哪儿,家里人看出不对劲,也劝了,也骂了,也打了,还是跳窗翻墙跟着张老先生跑了。
张天辈却跟别人说那女子是他干闺女。
县曲艺队和豫剧团的宿舍同在一院,有的是爱管闲事儿说小话儿的人,其中“小贱妃”最有能耐。
“小贱妃”名叫马花。马花在《秦香莲》中扮演皇姑。论说剧中皇姑是有着皇家气派的公主,金枝玉叶万尊之体。可马花就是对皇姑这个角色理解不到位,老是雍容跋扈不足,风骚轻佻有余。压根儿不管自己是身穿日月龙凤衫的公主千岁,出场后往台口侧身一站,冲观众就频频地丢媚眼儿,毫无大家风范。勾得台下那些浪荡子们扯起破锣嗓子叫好,马花得意地一拨儿媚眼儿接着一拨儿媚眼儿地丢,拽都拽不回来。从此,便落下了“小贱妃”的绰号。
这时,“小贱妃”正满脸跑眉毛跟平时演宫女丫鬟的秋菱发布她的最新消息:那女子哪是张天辈的干闺女啊,夜夜黑儿睡一块儿呢!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剧团里本来就是块儿是非之地,这下整得跟鳖翻滩似的再也不安生了。
闲话传到海椒那儿了。曲艺队队长姓海名椒,以前唱花脸儿后来倒嗓改行当了队长。人如其名,性格和花脸儿的行当相配,行事有点儿鲁莽,话辣还冲,剃一光瓢,动不动拉开架势,哇呀呀呀呀一阵叫板,吓得剧团大院儿里的一帮半大孩子四下逃窜,他倒是得意地拍着光头咧着嘴嘿嘿嘿地开心之极。可眼下,他听了“小贱妃”广播后,抽着冷气牙疼似的在当院里转来转去想门儿。
那个年月男女问题是雷区无人敢蹬。虽说曲艺队和剧团里不时有些花花草草的事儿,可那是逢场作戏跟刮风一样,过去就过去了。张天辈这事儿非同小可,人家是个人物是角儿啊。
张天辈三十岁丧妻,这么多年干熬,如今奔六十的人了,莫非晚节不保?
想来想去,得给张天辈提个醒儿,可这事儿没按住就无法开口,情急当中,拉上豫剧团的支书、他师兄、小生行当的洛成一起与张先生摊牌。
张天辈住在靠西边把头儿的那排平房里,海椒和洛成进门儿时他正坐在冲门口儿的那把罗圈椅上咕嘟咕嘟地吸水烟儿。见他俩进来,眉毛一扬中气十足地喊声“坐,上茶”算是招呼过了。俩人落座后,环视屋内,见摆设俭朴,迎面挂一画轴,细瞧却是黄胄的《群驴图》,虽说画已发黄,但这么随意地挂在家里,就知道不是真迹是赝品。这时,只见里屋门帘儿一撩,一花布衫儿大辫子闺女手里端两杯茶就出来了,低着头盈盈含笑将茶放在海椒洛成跟前儿,也不言语就快步出去了。
海椒干咳几声与师兄绕黑山避白水比葫芦说瓢终于把意思表达出来了。俩人擦擦汗忙呷口茶水润嗓,只等得茶喝完了,还举着空杯张嘴瞪眼儿庙里木鱼儿似的紧盯着张天辈看。
半晌,张天辈阴着个瘦白脸儿把手中的水烟袋重重往桌上一顿,山羊胡子一撅一撅地说:碍谁事儿?俺找个暖脚的中不中?明儿找您开证儿去!海椒和洛成面面相觑,既然话已说到这份儿,忙知趣地起身告辞。脚还没迈出门槛儿,就听后面说声:走好,不送!花脸儿和小生对视苦笑,好像怀里被人猛地塞块儿冰只凉到后脑勺脚后跟儿。
两天后,剧团大院忽然噼噼啪啪爆竹声声,惊得猫也跳狗也咬的。大院里的人们慌忙起身看个究竟,却见一脑后盘髻斜插朵红绒花的女子,搀着手捧个锃亮白铜凤冠雕花水烟袋的张老爷子踩着一地落英,喜眉笑眼儿地说着走着……
是个男人都说:这张天辈艳福不浅!
“小贱妃”说:嘿!老牛真的吃住嫩草了。
张天辈照样在曲艺队里唱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