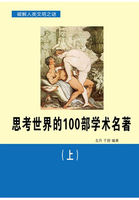其次,信息模式符合媒介组织各层级的需要。对于试图增加读者份额以及获得随之而来的广告收入的发行人来说,报纸以公正的面目出现是重要的,这可以最大程度地赢得读者。在莫特看来,报纸成为“大规模的事业”的另一个后果是报纸为了支持与稳定组织而产生了追求利润的保守主义倾向(Mott,1962:547)。《纽约晚邮报》的阿戈登(Rollo Agden)就认为报纸的稳定似乎是依靠庞大的资本与高度的赢利(Mott,1962:548)来维系的。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经济领域出现了公司企业兼并的浪潮,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风潮也波及到新闻业。弗兰克·芒西(Frank Munsey)大量兼并报纸,在他眼中,新闻业与工业、运输业、贸易、商业或银行业并无二致,这些重要事业的经营法则同样适用于新闻业,小的组织不再具有竞争力(Mott,1962:637)。在逐利而动的报纸看来,信息模式客观的呈现手法意味着可以规避政治、经济风险。通过大量使用直接引语与权威性材料而平稳地叙述事实,可以避免法律纠纷和引起非议。例如,美联社即要求记者严格遵循交代消息来源的报道原则,主编会告诫记者切记交代信息来源不是为了报道的准确性而是为了将责任转嫁给消息来源,假如结果证明信息是不准确的,报纸不必对此负责,要对此负责的是消息来源(Mencher,2003:45、47)。
对于编辑而言,他每天都是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的。他很少能亲自去现场看看他每天处理的这些新闻报道的情况。但他知道他必须要吸引读者,因为有众多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夺走读者。他往往要在几分钟之内对一篇新闻报道做出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报纸版面是基本固定的,截稿时间是雷打不动的,再加上销路不稳定、诽谤法以及其他可能有的无穷无尽的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新闻写作与编辑遵循一定的惯例和程式,才能节约时间和精力,保证编辑工作不致失败(李普曼,1989:233)。
对于凡人记者来说,他没有一个水晶球可以任意地观察世界。虽然从理论上讲,记者可以报道的事件很多。而实际上,他们只了解这些事件中很小的一部分,并且他们也必须要面对截稿时间和版面有限的压力。这样,他们每天只能在纷纭事件中选择极小的一部分加以报道。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赫伯特·甘斯发现记者时时处于“效率”的重压之下,而他认为这一压力主要来自于截稿时间(Gans,1979:283)。所以,如果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日常工作模式,记者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报道这么广泛的题材,他们不可能每天都采用新的标准去选择事实。门彻亦指出,不论是报道一场大学篮球赛、撰写一篇讣闻,还有报道总统的国情咨文,新闻记者都要遵循同样的基本程序:体育记者、娱乐记者、一个有25000人口小镇的综合新闻记者与美联社的驻白宫记者全部共用一种思维方式与一套类似的、指导新闻记者多年的技巧,而不管技术发生了何种变化(Mencher,2003:xxii)。
由此看来,信息模式的确是媒介建构专业权威的需要,因为信息模式提供了“一个结构而使得报纸能严肃对待自己的作品并说服其读者和批评者同样严肃地对待它们”(Schudson,1978:151);它亦是报纸组织生产降低成本、规避风险的需要;它还是读者的需求,否则新闻无法成为商品。正因为信息模式契合了社会和报纸组织多方面的需求才使得报纸将其作为了新闻生产的常规形式。3对报纸组织特征的廓清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后来那么多其他的报道方式,诸如“新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乃至“解读模式”都未能取代信息模式,而只是作为对其的修正或补充而存在着。而这也是信息模式一方面饱受非议和质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另一方面,对其批驳的力度愈大,对其坚守的决心也就愈强的原因。
三信息模式的遭遇:对信息模式的破与立
(一)对报纸独立地位的质疑
既能满足社会需求,又契合媒介组织特性的信息模式似乎可以让报纸一劳永逸了,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处于20世纪复杂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媒介的实际运作状况令人担忧。
1917年4月,美国宣战后一星期,威尔逊总统就任命成立了公共资讯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布有关战争的消息,并协调政府的宣传工作,负责政府与报纸之间的联络。它制订了一套以自愿为基础的新闻检查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家报纸的主编都必须避免刊登可能会对敌人有帮助的材料,关于一般的交战、伤亡和部队番号的消息,只有在官方公报已经提到的情况下才能发表。1917年,国会通过《间谍法》,1918年通过《煽动法》。借战争期间的特殊需要,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多年后,一位研究公共资讯委员会所发布新闻准确性的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公共资讯委员会所发布的6000多条消息几乎没有一条曾在事实方面引起过质疑,没有哪一个大国在发布官方战争新闻时能与之相比,但是,公共资讯委员会的失职之处在于它犯了“省略”的错误,虽然没有协约国的做法那么严重,但是公共资讯委员会和军方对消息的掩盖程度已经超过了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要求。公共资讯委员会的负责人、报纸主编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将该委员会的工作直接等同于纯粹的宣传机构,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和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4:320)。一战期间政府的信息控制和战争宣传使得人们对“事实”充满了怀疑。
此时兴起的公关行业使得新闻报道中“事实”的可信度进一步下降。英国学者J.A.R.平洛特(J.A.R.Pimlot)这样评价公关行业在美国的兴盛:“公共关系并非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但是它在哪里也没有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别的国家的这种活动不会如此普遍、如此赚钱、如此招摇、如此体面而又声名狼藉、如此广受怀疑和如此被吹捧得天花乱坠”(埃默里等,2004:481)。公关行业的兴起对新闻生产造成了很大冲击,它使得新闻越来越少地报道世上的事件,而是更多地复制能够雇用得起公关顾问的特殊利益者眼中的事实。公关先驱埃韦·李(Ivy Lee)在给洛克菲勒的一封信中就媒体大量报道后者捐款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事发表评论,他认为,这不是一条真正的新闻,报纸那么注意它,看来似乎是因为此消息经过“包装”之后更适合报纸的需要(Schudson,1978:138)。李普曼即认为,公关行业的发展表明现代生活的事实并不是自发地被认作是新闻,这些事实必须由某些人提供;由于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不能把事实报道出来,由于情报组织没有兴趣,于是就有必要由有兴趣的一伙人提供新闻。公关宣传员就是干这项工作的,他为记者提供清楚的情况,这当然减少了记者的不少麻烦。但是,宣传员给记者提供的情况却是他希望公众知道的。他是审查者或宣传者,仅仅对他的老板负责,全部事实只是服务于老板所谓的自己的利益(李普曼,1989,228)。根据斯拉斯·本特(Silas Bent)的统计,1926年12月29日《纽约时报》的255条新闻中至少有147条来自于媒介代理,1926年1月14日《纽约太阳报》的162条新闻中的75条是来自于媒介代理人(转引自Schudson,1978:144)。在一战之前不久,纽约的报纸统计了固定受雇用和固定委派的报刊宣传员的数目,大约有1200名。因此,“新闻的许多直接渠道已关闭,公布的消息都是首先通过报刊宣传员传播的。大企业、银行、铁路、所有商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组织都有报刊宣传员,他们是一种传播新闻的媒介。甚至连政治家也有报刊宣传员”(转引自李普曼,1989:227-228)。
媒体由来已久的商业性传统使得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其经营的不二法则。广告在报纸上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评论和广告的比例从70∶30发展到50∶50,甚至更低。在19世纪80年代广告占报纸总收入的44%,到了1900年就成了55%(Schudson,1978:93),1905年为56.6%,1910年则增加为60%(Park,1922:364)。大多数报纸为广告提供的版面从25%扩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与新闻版平分秋色。当时的都市日报的发行人认为,只要发行收入可以支付新闻纸和发行的费用,自己的生意就稳当了,而在50年以前,报刊还主要靠发行费过活(Park,1922:364、363)。某些新闻工作者对于报纸对利润的重视亦心存不满。在报纸成为“大规模事业”的时候,阿瑟·布里斯班就径直道出媒体“心随财动”的特征:“报业的成功带来了金钱。编辑已经成为商人”。著名的揭丑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更是认为:“报业财政运作金额的庞大已使得新闻业本末倒置”(Mott,1962:489,547)。
报纸也是兼并浪潮中的一部分,当时美国两个最大的报团——赫斯特报团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展开大规模的兼并活动。前者通过从1918年到1928年的集中购买,扼杀了16家报纸,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也造成1923年到1942年期间15家报纸倒闭。在1900年,8家报纸连锁控制了27家报纸,占全国日报总数的10%;在1935年,全国63家报纸连锁控制了328家报纸,占全国总数的41%(Sloan,1991:213)。并购造成了全国范围内报纸数量的减少。1892年,芝加哥有人口110万,英文晨报6份,而到了1918年,通过并购,只剩下2份:《芝加哥论坛》和《先驱观察家》(Herald and Examiner);尽管到了1925年,芝加哥人口已经达到300万,但只有4份晚报。很多大城市只剩下1份晚报。底特律在1925年人口100万,但10年以来,只有1份晨报:《自由报》。在圣路易斯、圣保罗、安纳波利底斯、亚特兰大、新奥尔良都是如此(Mott,1962:637)。报纸数量的减少以及报纸的集中垄断造成的后果就是“意见市场”的多样性声音的减少,而这是有悖于民主理念的。
商业力量的渗透使得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备受争议。报业本身存在的内幕也成了揭丑报道的题材。1905年,《柯里文》杂志发表了一篇匿名报道,题为《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卖药阴谋》。该篇报道揭露了马萨诸塞当地报纸为何回避报道1904年在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众议院展开的一场关于专卖药辩论的内幕。这场辩论围绕这样一项议案,即在该州出售的每一瓶专卖药上应该附有标签,以说明瓶中药品的成分。但是,这场“既妙趣横生又意义重大的辩论”并没有得到当地报纸头条的青睐(斯蒂芬斯,2000:206)。记者对此十分好奇:
为什么这个题材遭到如此忌讳?为什么第二天的各家报纸上对立法活动的日常报道被压缩为平时冗长篇幅的一小部分,删去了所有触及那天下午关于专卖药辩论的内容?为什么那场辩论的发言者们无法在第二天的报纸中找到他们的发言?为什么报道立法活动的记者看不到他们的作品见报?为什么漫画家们被禁止利用这个未被利用过且极具诱惑力的机会来展示他们的才能——马萨诸塞州州议会的成员们神情肃穆地啜饮一口佩鲁纳,然后把药瓶递给下一位。这种实践认知能否成为立法行为的基础呢?
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报纸的沉默源于一种协议(斯蒂芬斯,2000:209):
阅读以下协议书,品味一下马萨诸塞州举足轻重的沉默吧!此协议是胡德—艾尔与穆尼恩公司在与全美上千份报纸所立协约时的惯用模式。
……
协议最后附有两个重要条件:
一、双方一致同意,一旦任何有损于J.C.艾尔公司利益的法律或法规确立,自立法之日起,此协议失效。已刊之广告按协议价格按比例支付费用。
二、一旦报纸刊登的其他药品广告欲代替本药品或含有其他不良动机,或者,任何有损于J.C.艾尔公司利益的内容出现在阅读栏或报纸的其他版面,J.C.艾尔公司可以撕毁此协议。
这样的协议在专卖药行业并不少见。在美国,专卖药产业在经济上占有极大比重,在美国人民每年为专卖药支付的这1亿美元中,有整整4000万流入报界的腰包。美国至少有5种专卖药每年向报界支出的广告费用高于100万美元。波士顿的格林公司破产时,它拖欠报界的广告债务高达535,000美元。药品制造商们手挥经济利益这只大棒对报纸颐指气使,《柯里文》因为对于专卖药发表了某些评论,一年就损失了80,000美元。这些制造商们甚至会联合起来制裁某些报纸对专卖药的不利报道(斯蒂芬斯,200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