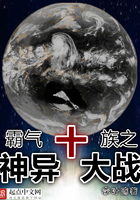霸权概念把文化领域描述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产品以隐蔽的方式向社会传播,并通过这种方式施展本阶层的霸权力量;不同社会处境的观众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文化产品进行解读,从而解读出不同的文本意义。因此,文本意义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协商、抵制和斗争的过程,即统治阶层和不同社会阶层的观众通过协商、抵制和斗争产生意义的过程。在斗争过程中,如果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完全占据优势地位,或者受众赖以解读文本结构的社会背景与文本结构得以形成的环境相近,双方就暂时取得了一致的立场,从而统治阶层的目的得以实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统治阶层在文化斗争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局面鲜有出现。
由于不同的利益目的,统治阶层和从属阶层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然而在文化这个特殊的斗争场所,统治阶层不可能通过武力手段粗暴地压制从属阶层的文化,因此他们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主动吸纳从属阶层的文化因素,并通过对文化的整合,传播有利于统治阶层的文化,以达到维持霸权统治的地位。正如托尼·本内特所言:
统治阶级建构大众文化领域,企图赢得霸权,同时又以反对这一企图的形式出现。因此,它不仅仅是包含了自上而下,同统治阶级步调一致的群众文化,而更像是两者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期间主导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以大众文化形态各异的特定类式,“混合”在不同的队列里了。从霸权主义视角研究大众文化,彰显了统治阶层利用大众传媒维护霸权地位的事实以及大众传媒对各种文化形式的包容,肯定了大众传媒在维持受众“意识形态式的赞同”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为霍尔倾向性解读的受众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信息传播的倾向性
倾向性解读(Preferred Reading)指的是一个文本虽然向若干潜在的解读开放,但是通常倾向于某一种或几种解读方式。通过分析文本的内在结构可以识别出这种倾向性。符号学家艾科也曾经就文本的开放性和封闭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一个封闭的文本往往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其倾向性非常明显;而一个开放的文本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艾科明确了解码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反对过度强调解码者的权利,从而为倾向性解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符号学家的观点,一旦信息通过不同的符号形式被编码,由于符号的任意性特征,文本就具备了意义的开放性;同时,由于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因此符号的意义必须停留在双方能够形成共识的范围之内。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一方面承认编码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编码文本的开放性特征。但是,在霍尔看来,经过编码的文本始终是偏爱某种解读方式的。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内,霍尔利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相关理论,着重研究了媒介如何通过话语结构对文本进行编码,并使得“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得以展现的方式。
霍尔认为,媒体不是把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故事复制出来,而是将真实的故事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加工,从而“制造出”一个媒介中的“现实”:“现实不能再被简单地认定为只是一套被给定的事实,而是一种构建事实的某种特别方式的结果”。霍尔通过上述表述指出,媒介中的现实并非事件的本来面貌,而是媒介构建出来充当事实的东西。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霍尔用“表征”(representation)和“反映”(reflection)两个词来表示:媒体的反映功能指的是媒体把事件的原貌原原本本表现出来;而表征不仅仅是一个传输的过程,在“表征”这个过程中,媒介通过“选择、表达、构建和塑造”等过程积极主动的行为为事件重新赋予意义。这种区别就体现在复制现实和定义现实之间添加了一个主动创造的过程:
媒体信息……从根本上表征一种对世界的独特看法和建构被以如此方式加以组织。这些信息通常被用主导性或协商性符码来处理。它们可能会在细节方面而不是整体上受到挑战。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对世界的霸权性的理解和表征,它有利于有权势的群体,并且作为常识的一种形式,被大多数人所共享。霍尔把媒体的实践和生产称为“象征行为”,把媒体称作“象征的代言人”:这种象征行为主要通过符号的意指过程,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制造“舆论”和“共识”。在对文本进行编码之前,媒体已经有“一套占有优先权的价值、信仰、礼节、制度上的程序(游戏规则)”,因此在媒体播出的节目中,这些具有优先权的规则已经先入为主地为文本符码赋予一定的意义。而且,“这种倾向性的解读与电视、其他媒体以及整个社会上表现出的强大有力的且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并行不悖”。霍尔认为,“‘倾向性含义’的范围用一套意义、惯例和信仰来体现整个社会秩序,其中包括对社会结构、‘在该文化中事情如何服务于一切实际目标’、权与利的等级划分以及合法权限和制裁构成的常识性了解”。因此,文本中意义的倾向性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的构成形态。媒体对整个意识形态环境进行了塑造:一个表征事物秩序的方法,这个秩序以自然或神圣的必然性,赋予它们以限制的观点,使它们与“现实”本身广泛、自然而连接地出现。这个运动——朝着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胜利,朝着在自以为是的“现实”中特定构建的地基——确实是“意识形态”的描述和定义机制。安吉拉·麦克罗比曾经指出霍尔理论中表达的电视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和倾向性:
霍尔等人的出发点是,认为电视“从不只传达一个意义”……而是提供意义的范围——尽管这里有一个推荐的意义引导或指导观众。要把电视节目做好,其成功的基准就是要传递这样一个推荐意义,但要产生这种推荐性阅读结果,节目制作者需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那么,大众媒体如何保证统治阶层在传播过程中发挥话语权的作用,并使受众的解读产生一定的倾向性?霍尔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媒介可以选择播出哪些内容、放弃哪些内容,即媒介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例如,有人预测1984年底至1985年埃塞俄比亚会发生大饥荒,因而一些记者和救援人员竭力唤起人们关注灾民,然而西方媒体并未对这一事件进行及时报道,因此这一事件没有及时得到世界的关注。其次,媒介可以对故事进行重新建构,编辑一定的价值观念,以此引导受众价值观的形成。电视新闻记者总是带着“一组设想或框架”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组织和筛选,例如,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中就存在着“冷战思维”的框架,在这一框架的指导下,“正义”一方的美国与“非正义”一方的苏联之间的较量成为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符合这一指导思想的新闻就可能被报道,反之则不可能播出。此外,媒介还可以通过广播人员与画面语言相结合的方式,造成某种特殊的效果。
媒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节目的选材、制作、编辑、播出等过程加以控制,从而展现了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
霍尔列举了产业纠纷的案例来说明意识形态话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有关产业纠纷的报道中,媒介可以把产业纠纷对国家经济的威胁报道为对“国家利益”的反对。这种含义的建构标志着媒介倾向于维持现行的经济政策,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一方。如果推翻现行的经济政策,将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于“国家利益”。因此,媒介所采取的话语策略暗含了这样的意义:如果罢工工人一方获胜,将威胁到的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利益。显然,媒介采用了偷换概念的方法,使其倾向于资产阶级一方。这样,本该公正的大众媒体在报道中偏向了产业纠纷中的一方,使媒介的报道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功能。媒体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表征了一个“有偏见的、其运作有利于统治群体的世界观”。
三、信息传播的隐蔽性
电视新闻为了达到客观性的目的,借用了写实的传统手法。通过这种手法,事情“似乎是原汁原味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而“制作者的手”并没有在节目中表露出来。同时,媒体必须宣称自己的报道是真实的、公正的。电视节目也试图以“自然的”方式为观众灌输思想,界定共识,然而,共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怀疑、有抵制、有反抗,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批判标准和判断模式。共识的形成过程就是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作用的过程。在意识形态的运作下,媒体不断将人们“型塑为符合优势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优势阶级以媒介文化产品赢得弱势阶级的认同,使后者的隶属地位更加确立”。因此进行文本分析时应该首先考虑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结构,关注意识形态是如何制造共识、体现共识的,还应该看到这些共识是如何按照统治阶层的利益塑造弱势群体的。霍尔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同样借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规则和秩序,而言语是符号具体的表现形式。霍尔借鉴了这种区分形式,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引入媒介分析中。霍尔把媒介文本看成具体的言语,即具体的表现形式,把文本中包含的规则看成意识形态。因此在对文本进行编码时,意识形态已被无意识地融入其中。离开了语言,言语就成为没有意义的孤立字体和片段;同样,离开了言语,语言也就无从表达。在霍尔看来,这就是文本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文本中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只能通过文本来表达。二者互相渗透、密不可分。
在这一点上,霍尔把意识形态看成对现实进行编码的系统,而不是一套已确定或已被编码的信息。任何文本在形成过程中都离不开这一系统。没有离开了意识形态系统而独立形成的文本,也没有不依靠文本而表现的意识形态系统。
索绪尔区分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这就为文本的多种解读开放了空间,同时为“意识形态的侵入留有了空地”。罗兰·巴特发展了符号的任意性观点,提出符号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符号的任意性和意义的多样性为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缩小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限制了所指的意义。因此,在文本中存在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张力。意识形态是如何将能指和所指连在一起,同时又偏向某一种意义的表达,也就是说,“统治话语如何保证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并且能够持续限制、禁止或者剥夺其他选项或竞争意义……大众媒体——如何能够成功地维持一个在统治传播系统中的有偏向的或已界定的意义范围”,霍尔对此进行了分析。
媒体机构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生产文化产品,在对文化产品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使用意指的谋略,把文本的意义限制在某一框架之内,因此“集体的社会理解才创造出来……一些特殊结果的共识也能够有效动员起来”。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权利,一种表达“现实”的权利,更是一个竞技场。在这个战场上,纠纷的各方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这样,意识形态就和政治连在一起。然而,不论是媒体人员还是受众都不会意识到意识形态在文化产品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意识形态以“合乎语法”的面貌出现。
霍尔以电视为例阐释了这一过程的形成。人们把电视称为能够展现世界的真实面目“一扇世界之窗”,因此相信电视语言使用“自然主义话语”叙述事实,描绘真相。然而霍尔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以自然为基础,而是把自然生产出来,作为其真实性的保障”。霍尔提出“制造共识”的概念从而强调了上述观点。媒体不是“反映舆论”的机构,而是“生产舆论”和“制造共识”的机构。这种信息传播中的“自然化”方式使媒体“生产舆论”和“制造共识”的过程取得成功,尤其是在新闻节目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在英国举行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电视作为报道国内、国际大事的信息源在完整、准确、公正、快速和清楚方面堪称之最。霍尔认为,通过“自然化”的过程,媒体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生产出有人为烙印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得这种文化产品必然会偏向某种意义的表达,进而造成受众解读过程中出现的倾向性。霍尔提出了解码的多种可能性,但是在他看来,“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本始终是决定的主要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