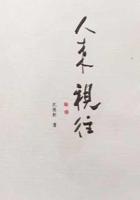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先驱者达拉斯·斯迈思前往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之所以决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科技哲学”,是因为他“有一种直觉……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问题”(Guback,1994:228)。他在报告中写道,尽管自然科学家和广播官员们认识到科技及其产品有政治本性,但他在中国的学术和政策部门遇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却不同意他所说的科技具有的社会建构性。斯迈思发现,这些人认为“工艺和科技是自治的和非政治化的”。更令他不安的是,“他们表现出一种固执,甚至完全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的可能性”(Smythe,1994:238)。
对中国科技哲学的这一探究并非停留在抽象层面,也不仅是一种学术兴趣。相反,斯迈思对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性道路进行探索的可行性提出了最根本的问题。正如他所说的,“尚不清楚中国人是否已正确认识到科技的政治属性,而这在今后一二十年里将对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至关重要”(Smythe,1994:242)。具体来说,斯迈思看到了这样一种不一致:一方面中国说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人有一种“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科技的心态,后者“意味着社会主义科技可以被用以衡量反对资本主义科技的成就”(Smythe,1994:243)。对斯迈思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获得成功,有赖于中国能否拒绝盲目引入西方的科技、消费商品和服务,以及能否拒绝在这个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消费关系”。要想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政治”(proletariat politics)必须在科技革新和经济生产领域获得领导权,特别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某一种消费品和服务的革新”是否“能服务于作为集体或者个人的大众”(Smythe,1994:243)。这里的“无产阶级政治”意指民众对决策的参与,指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社会需求,这也是在斯迈思的想象中“文化大革命”所意味的东西。在斯迈思看来,西方消费品是“资本主义呈现给新的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陷阱,中国的工农兵应该意识到这个陷阱”(Smythe,1994:241)。斯迈思写道,因为“在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中没有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采用资本主义的奢侈品,比如说私家车、家用洗衣机、家用冰箱、单向电视等,也就意味着用这许多教育工具武装起中国家庭,导向资本主义的文化道路”(Smythe,1994:231)。
斯迈思以评判性视角对当时的国际传播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起“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他甚至从冷战年代美国禁止向中国输送技术和苏联从中国撤回技术支持的举动中看到了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自力更生获得科技进步”。他这样写道:结果,中国……牢固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决策的群众路线方式。现在中国已经解决了向民众提供食物、衣服、住房、医疗这些紧迫的问题,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大步迈进共产主义是有可能的。这一步的实现决定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答案应该是公共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个人私下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将创造性人才和资源分配去生产和提供所有人都喜闻乐见并有教育意义的物品和服务,如公园、博物馆、科学、教育、图书馆、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筑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包括双向电视),“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便可以十分有效地直接达成(Smythe,1994:243)。斯迈思在改革初期的1979年再次访问中国,并就所见所思写了一份报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将它作为一份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阵营一名“家庭成员”的友好批评与建议书,提交给了中国政府有关官员。斯迈思生前之所以从未将之发表出版,是因为他觉得“有义务将我的批评局限在大家庭内部”(Guback,1994:230)。
然而中国有关官员从未正面答复斯迈思。相反,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为了回应来自外部的冷战压力和来自社会主义内部的危机,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口号回避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中国追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改革开放”,使消费主义在中国迅速蔓延。中国在大量进口西方的科技和消费品的同时,更将自己变成了“世界加工厂”,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成为主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而这些商品不仅包括鞋子和玩具这样的低端消费品,还包括电子消费产品和其他的高端信息技术产品,例如电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最蓬勃发展的区域”。加上对信息科技这一“资本主义最生气勃勃的产业”的拥抱,中国成了跨国资本主义“两个增长极”交汇中心(Schiller,2005)。
斯迈思注意到,他访谈的中国哲学、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士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误导,错误地相信科技具有中立性。这种观察也许是正确的。不过,他本人很可能也被“文革”时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修辞术误导了。
首先,在他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并非像他认为的那样,已经解决了向大众提供基本必需品的问题。在1978年农村改革之前,“吃饭问题”对中国的大部分人口来说仍然是十分紧迫的问题,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一直是一个挑战(Huang,2005:5)。
其次,斯迈思想当然地以为“无产阶级政治”具有民主的天性,或者说在决策过程中会有“群众路线”这样的民主过程;不仅如此,他还错误地认为,这样一个过程已经多多少少被牢固地确立了。事实上则是,他的两种假设都存在问题。“群众路线”政治传播模式不但有明显的家长制的色彩,而且还很容易从上面或从下面被颠覆(Zhao,1998)。
再次,在政治上,斯迈思虽然接受中国官方的说法,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但他没能充分把握中国的后革命政权不得不应对的冷战环境的严重性,而中国领导人作为一个整体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在高科技战争和核武器威胁中生存。简言之,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斯迈思所观察到的“两条路线斗争”之上,这种由军事引领的科技民族主义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数字革命”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最后,尽管斯迈思关于科技政治的观点在西方批判学术界被普遍接受(比如说Williams,2003;Winner,1997,1986),但他对商品和服务要么服从集体需求、要么服从个体需求的二分法是有局限性的。在某些情况下以及在特定条件下,集体的社会需求和个体的需求并不能截然分开。电脑和手机这样的互动传播科技尤其如此。信息传播商品与服务具有社会本性,而且消费者并非消极的和原子化的,各种社会主体能够将信息与传播技术用于自己的目标。
然而,斯迈思与中国的这番遭遇不应仅仅被视为西方学者因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而试图在别的什么地方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天堂的个案。尽管中国改革时代的发展道路和斯迈思设想的道路相左,但是斯迈思提出的问题还是在中国挥散不去;不仅如此,当中国由信息科技驱动、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引发的经济与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后,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被更准确地修正为“手机之后,是什么?”——便有了新的相关性,并日益重要。尽管斯迈思误读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他用来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框架也不乏局限性,但他确实为我们分析中国在改革时期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整体发展策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斯迈思对经济中的决策过程、科技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占中国最大多数的群体(他本人所称的“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所承担的风险的关切,在中国现行的社会改革和与世界市场体系的整合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国家决策及市场导向的“数字革命”的形成
1958年的“大跃进”,目标是通过自主科技创新与本土工业化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发展目标则是“蛙跃”进入数字时代。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番历史。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领导层对实现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决心。这个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发展规划,明确表现出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对现代化根深蒂固的认识:要将这个国家从过去遭受科技和军事凌辱中拯救出来,唯一的方法便是“赶上西方”。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施“863计划”这一高科技发展项目。这个启动于1986年3月的计划是一项大规模的军事和工业研究发展计划,是对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的回应,将包含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在内的七项新的“战略”技术领域视为优先研发的对象。在1992年的海湾战争中,中国惊叹地目睹了一场“信息传播战”,看到了实际战场上控制、指挥、传播、情报的战略重要性(Mattelart,1994:117-121),这进一步加强了中国领导层将信息与传播技术视为战略领域的信念和对它的重视。
中国通过获取西方发达科技和将之本土化,以及进一步与全球市场体系融合,来追求现代化,并将“信息化”提升到现代化之母的高度(Zhao and Schiller,2001)。正如前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所言,“没有信息化,就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Zhao and Schiller,2001)。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部署,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信息化,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方面。电信网络得到爆炸性扩展,各类“金字头工程”(Feigenbaum,2003:199),如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成为国家对“数字革命”所进行的主要投入。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信息社会理论的重要特征是将社会从政治化的文化批评领域剥离出来。在这一理论范式里,社会不再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外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领域,而是一个超越了社会制度区分和政治冲突的经济主义领域(Schiller,1996;1997;2007),而这正是“政治的终结”论的体现(Mosco,2004)。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受够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说教的改革初期的中国来说,“信息范式”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吸引力。人们欢迎这种看起来既客观又科学的“信息”,这在1980年代早期至中期的新闻改革的话语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场改革试图重新定义新闻,突出其具有“信息”的特性,并推动信息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化宣传功能分离(Zhao,1998)。
此外,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的需要以及民用的需求,共同驱动了改革时期的科技发展,因此信息与传播技术很快就变成中国高科技发展中最流行和最商业化的领域。到2001年,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明确了通过信息化推动工业化的策略,以此利用最新的发展成果,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蛙跳式的跨越,大步跨入“十五”计划(2001-2005)。2001年中国还史无前例地成为第一个官方确定全国信息指标(全国信息化评估中心,2001)的国家,这个指标包含如下统计指数:
电脑、电视机、互联网接入家庭覆盖率
千人广播时数
人均宽带数
长途电话线长度
卫星地面站数
电子商务的规模
每百人大学毕业生数
研发投资率(R&;D)
IT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
2002年11月,信息与传播技术应用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上被定位为日趋发展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逻辑选择”,这进一步确立了信息科技的重要地位。正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要坚持通过发展信息化来推动工业化进程,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并在各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使用信息技术(Jiang,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