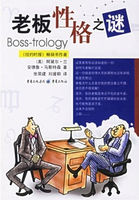一、国王和民族利益的兴起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论述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归宿,神国必然战胜俗国。因此,他推论神国应该高于俗国,世俗政权必须服从神权。这个推论成为中世纪西欧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基本准则。
中世纪初期,盖拉西教皇发表了“两剑论”,对奥古斯丁的“两国论”作了补充和发展。他宣称,上帝将代表教权的剑和代表政权的剑分别授予教主和人主,要他们互相提携,互不僭越。直至11世纪,盖拉西的理论都被认为是教会的基本教义。按照这种教义,任何人都不能兼有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力。
实际上,整个中世纪教会之剑和人主之剑经常发生碰撞,有时甚至火星遍地。不过总的来看,在9世纪以前,人主之剑的光芒更盛。而在9世纪以后,直到16世纪,教会之剑则居于统治地位。
在查理大帝统治时期(768—814),法兰克王国对基督教会活动的控制最严格。国王亲自主持宗教会议,宗教会议的决议由国王的《通令》予以颁布。各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按照所辖教区和修道院的规模,为法兰克王国的军队出人出钱。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和重要的宗教仪式规范,一律由国王决定。
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封他为法兰克皇帝。这个事件是国王的权力从强盛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从表面来看,国王变成了皇帝,世俗权力格外强大,但世俗权力从此打上了教会批准的印记。为了使这个印记更为深刻,大约在公元850年前后,教皇档案馆出示了被称为《君士坦丁的赠礼》的著名伪件。据这份“文件”称,由于教皇西尔维斯特的祷告,君士坦丁大帝才治愈了麻风病。为了表示感谢,他将帝国王冠及对罗马、意大利以及整个西欧的政权,赠送给教皇,教皇退还了王冠,但保留了统治权力。教皇引用这份“文件”,声称世俗君主只是以教皇代表身份为罗马教会行使职权。教会之剑隐隐地指向人主之剑。
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他的帝国迅速衰落,他的子孙既抵挡不住外族的进攻,又不能对教会给予更多的保护。苦难导致人们产生厌世思想,因而使禁欲主义的理想强劲复苏。公元910年,虔诚者威廉在德国东部的克吕尼建造了一座隐修院。克吕尼隐修院在处理它本身的事务和选择它的领袖时享有完全的自主;它只服从教皇,而不服从任何世俗权威。遍及西欧的“克吕尼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教皇权威的上升。
教会要求权力的愿望还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到10世纪前后,教会和教士就已经是大地主了。以当时不算很富的德国圣里奎尔修道院为例,这个修道院拥有2500处庄园,在市镇上还有2500幢房屋。要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光有上帝的关怀是不够的,教会和教皇还必须掌握世俗权力。
1075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发布《教皇敕令》公开宣称:一切君主应亲吻教皇的脚,教皇有权废黜皇帝,罗马教会从未犯过错误,也永远不会犯错误。敕令揭开了罗马教会向世俗君主夺权的序幕。到了13世纪,教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在德国,教皇把皇帝的废立看做是自己的家务事。在法国,教皇迫使国王同他废黜的王后复婚。在英国,教皇宣布不服管教的英王失去王位,并对他进行讨伐。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这时的基督教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是基督教对国家的否定”。
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对教皇的权力作了理论的说明。他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因此是由于人的理性的需要而自然产生的。当然,这种理性是由上帝赋予的。一个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某种治理规则和控制机构,这就是世俗国家。这样,理性的根源是上帝,国家的根源是理性,而教会是上帝的代表,于是教权高于俗权就是合理合法的。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从14世纪起开始瓦解。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教会本身的腐败。由于教会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一些神职人员就利用这些权力搜刮财富,他们酗酒、经商、放高利贷、污人妻女、霸人财富,甚至使女修道院也成为贵族、神职人员的妓院。正如黑格尔说:“由于人与神圣生活的联系是存在于尘世上的,神圣生活就被人的各种欲望搞得世俗化了。”2 其次,由于教会的横征暴敛,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反抗。12世纪和13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新兴的市民阶级经常起来造反,14世纪以反对封建神权统治的农民起义在整个欧洲此起彼伏,极大地动摇了罗马教会的统治。再次,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教会分裂,使教会的力量大大衰弱。从1378年到1409年,在罗马和阿维农同时存在两个教皇,两人都自称正统。当时西欧任何地方神职出缺,两个教皇同时派人出任。并且,两个教皇都同时向西欧所有基督教国家征收赋税。德国、意大利等国支持罗马,而英国、法国等国则支持阿维农,形成基督教历史上“西方大分裂”。最后,中世纪晚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沉重打击了原来依靠土地收入的教会的经济势力。市民阶级为了切身利益与封建君主联合,要求建立廉洁的教会,取消教会的苛捐杂税,而封建国家为拒绝纳贡和争夺神职任命权,也需要走向中央集权,抵消教会的各种干预。这些斗争进一步削弱了教会的权力。
封建国家争取权力的斗争在理论上首先表现为宗教异端。“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的时代(1265—1321)一个重大主题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罗马教皇争夺对北意大利的统治权。在这场争夺中,但丁坚定地站在世俗政权一边。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不顾教会的高压统治,大胆而详尽地驳斥了君主的权力来自教皇的种种论点。他指出人生在世,有其双重的目的:一是永生的幸福,它体现为能够看到上帝;一是尘世的幸福,它可以尘世的乐园为象征。达到第一个目标非人力所能及,只有通过神启来实现。达到第二个目标则靠人的理性、伦理去实现。“但是,人类的贪欲仍然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人类就像脱缰之马,不得不用缰绳和嚼子勒住它,使它走上正道。”而人类的缰绳将由一对骑手来把握:国王和教皇。教皇用神启引导人类走向永生的幸福,国王则用哲理引导人类走向尘世的幸福。国王和教皇的权力来自同一源泉——上帝。而教皇仅仅看守着天国的大门,没有统治世俗帝国的权力。但丁的“双骑论”为政教平等、政教分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立即被教廷列为禁书,直到1908年才开禁。
1324年,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写了一本小册子《和平的保卫者》。这本书第一次用鲜明的笔调指出世俗权力的来源不是教会,而是“人民”。 马西利乌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有关论述,指出国家的起源来自许多家庭的联合,而促成这种联合的是由于每个家庭都不能自给自足,因此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神的意志,而是对美好世俗生活的渴望。为了满足这种渴望,人民,或者是由公民构成的整体,或者是这个整体中最为强势的部分选出立法者,而世俗的立法者应该具有不受制约不受控制做任何事情的权威。
1328年,被称为“最后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威廉·奥康就提出教皇只有宗教上的权力,在世俗问题上应当服从世俗君主的观点。1376年,英国国王的神学顾问威克里夫(1328—1384)发表了《论世俗统治权》的演讲。他指出教会的唯一法律是《圣经》,教会的唯一首领是基督。一切职务,不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是上帝赐给的。教皇不一定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他只知攫取世俗权力,热衷于征税发财,那他不仅不是上帝的选民,而且还是基督的敌人。威克里夫的观点传到了波希米西,引起了约翰·胡斯(1373—1415)的共鸣。这位布拉格大学的校长积极宣传威克里夫的观点,他要求取消教会的土地占有制,取消教士养尊处优的豪华生活,他生动地比喻:把狗群中的骨头夺掉,狗群就不会再咬;把教会的财产没收,教堂里就找不到神甫。5 这种说法在当时的西欧和中欧家喻户晓。
胡斯的观点使教会感到恐惧,1415年7月6日他被控异端遭处火刑。他的死成为15世纪欧洲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导火线。1440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1405—1457)经过认真研究,揭穿了“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份伪造的文件,从而动摇了教会权力的最重要的神圣支柱。
1295年,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为了应付德国与英格兰的战争,开始向神职人员征税,这件事引起了教会的不满。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于1296年发布《教俗通谕》,规定凡不经教皇允许不得对教会财产征税。国王于是以禁止德国钱币出境作为报复,这对教皇的财政收入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意大利银行家所施加的压力下,教皇不得不在1297年重新发布国王有权向本国神职人员征税的指令。1300年,教皇卜尼法斯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再次谴责菲利普四世。1301年,菲利普四世下令逮捕法国大主教,以叛国罪加以审讯。教皇下令释放大主教,并传讯菲利普四世到罗马受审。对此,菲利普四世针锋相对,于1302年召开法国首次三级会议,会议支持国王与教皇对抗。教皇则发表著名的《一圣通谕》作为回答,并宣称,基督将两把剑都授予了教会,神圣之剑供教会使用,世俗之剑也供教会使用。教会的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最高的神权即教皇的权威不容置疑和动摇。菲利普四世对此的反应就是派人用武力攻进教皇的寓所,将卜尼法斯凌辱并殴打一顿。一个月以后,教皇卜尼法斯死于气病交加。这个事件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此,在教会步步后退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步履日益持重而坚定。
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政治思想家也不甘寂寞,为自己的国家奔走呼号。法国的让·波丹(1530—1596)在他的代表作《国家论·六卷集》(1576)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我想以这本书来巩固因内乱而动摇的法国王权的基础,来实现有关国家的理想。波丹认为,国家是由家庭产生的,因而带有家庭的一些特点:第一,在家庭中,成员之间是不平等的,父权是最高的权利。在国家中,阶级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君臣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君权高于一切。第二,家庭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而国家因私有财产而繁荣,不承认私有财产,国家就无法维持。第三,家庭有了家长的权威才可能安定和睦,国家也必须有无上的权威,即“主权”,“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利”。这种权利只向上帝负责并受制于自然法则,它本身是永恒的,不因政府的更替而变更;它具有无限性,既不受法令的限制,也不受其他社会集团的约束,它本身就是法律的来源。
拥有主权的君主首要的特征性权力就是为全体臣民制定普适性的法律和专门适用于个别的特别法令。但是这还是不充分的,我们还必须加上“制定法律不必经过其他人的同意,不论这些其他人的地位是比制定者高,与之平等还是较之卑下”。
荷兰的格老秀斯(1583—1645)发展了波丹的理论,在《战争与和平法》(1625)这本著作中,他用自然法来解释国家的产生。他认为自然法就是正确理性的命令,而理性是人性本身的所有物,在某种意义上,理性独立于上帝。在他看来,国家的产生不是出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出于人的理性,在人所独具的特性中有一种要求社交的强烈愿望,亦即要求过社会生活的愿望。 因而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每个人放弃他所享有的自然权利,把它交给少数人或某个人,使之管理社会之权,于是国家就产生了。
国家是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谋求他们共同的利益而结合起来的一个完美的联合体。
这种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以法律为社会契约,以追逐世俗福利的国家形象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论相去甚远了。
二、 海洋与贸易精神
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是国王的时代,朕即国家。城市经济的发展,庄园制度的衰落,十字军的东征,黑死病和连绵不绝的战争削弱了贵族的地位。宗教改革破坏了基督教会的团结,教皇对世俗领袖的封建统治权被废除,从而扶持了各国的民族主义。正如熊彼特所说:
这些事实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民族的”,就力图摆脱超国家的控制;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坚持而且不得不坚持拥有绝对主权;……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些新的主权国家是好战的。它们是偶然出现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彼此拥有所需要的东西。而且它们很快就被新世界所包围,诱使它们竞相去征服和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