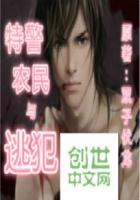误会和蔑视,是人天生随之的特性。——剑追雪
入了‘路过桥’,过了片刻后,马灯熄灭,日光打在马头上,是到了,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马车没驾马人,马车的马晃晃头,见了步贤和步茶下了车,晃晃马腿,转转便回了这夜中,马灯依旧亮着,渐渐远了;
再看身后,却是没了那座桥,再看眼前,是一片沧海,眼前沧海畔是个港,却也不算个港;
一条木船停着靠岸边,岸边,立了几棵白银树叶的树,叶小如松针,却是银白之色;
三两棵这样的树立在一座木屋前,木屋的木是偏淡色的,木屋前,一个半人约高的石桌,和个藤椅;
藤椅微斜,上面躺着个人,面上扣着个草帽,双手合着扣在身前,一腿放于另的腿上,一身的深色的短衣短衫;
步茶躲在步贤的身后,拉着他的手,步贤走着,走到这人的面前;
躺着的人只是去晃晃手,指了指湖上那孤零的木舟,步贤便不再说什么,上了木舟;
木舟之上无船桨,脚踏木舟,坐于木舟之座上,木舟自渡于湖上,远处依稀见得是个水乡小镇,渐行渐近;
抬头望,云起云聚,夕阳之色,记得之前来时是夜色了,这日色,是倒退了么;
步茶心有好奇,伸手触了触水,水于手上,其温不凉不热,抬头再望,却是已至这水乡小镇;
楼台水上,这些楼台却是不高的,建筑说来风格,算是慵懒,亭台楼阁,砖瓦执剑不见紧凑,不见严密,楼台之间并无什么绝美雕样;
砖瓦之色,白黑灰之间,小宅小屋如同孤岛,每每小屋前,常有几棵树,或老或幼,或高或低,皆是有的;
小宅小屋之间,石桥相连,拱桥板桥,有的桥,还是断掉了,透着清水看到湖底,有些石块;
穿水行桥下,行于石屋小宅之间,水乡小镇不大,约小憩片刻的时间,这条木船出了小镇,再回首,小镇渐远;
残阳日色,光自残云穿过,道道,或注或撒在这水乡小镇之上,或是砖瓦之上,或是片片玻璃之上,反光而;
残光入水,落于湖底,残光映起,其色之美,步茶竟是不看前方,半蹲在船头,望渐远这小镇之色,迟迟不回身;
水乡小镇渐远,天色渐变,由残阳之色,渐渐日落西山,再望天色,却已不知何时变作深夜之色,星辰,撒部天际;
眼前,是个山,环山,聚顶为尖,单一个山峰,环山之色,毫无半棵树立着,环山,却是一道裂缝,木船不偏倚的进了环山之中;
进环山,却又是换了个景色,再望天,却是无群星挂垂,天空之色,一望无际,万里皆清,天色之清,朝阳之色;
朝阳色,透光,天色之间,一片希冀之情,眼前,终于靠了岸;
岸边,青石上,坐着个身着一身白袍之人,一头短发,身后是个小木屋,这少年手上把着个小茶壶,见步贤来,做个请的动作,向着这条青石路,通向通幽之处;
两边林茂盛,不多时,走到了尽头,一处悬崖之上,自悬崖向下看去,白云层层,云雾缭绕,不见悬崖之底;
悬崖边,是十几人坐着;于崖边,有些坐着微闭双目似是睡去,有些捧本书看着,有些望这云色,有些,竟是执个竹竿挂鱼线,远处,垂下,于悬空,鱼线垂入山间渺茫之云色间;
一位垂竹竿,钓云的人自座起身,到两人的面前;
“二位,这边请。”
于悬崖边,寻到了个石梯,长约三人上下的宽,那人于前,步茶紧紧贴在步贤的身后,这石梯无任何的扶处;
不消片刻,山壁之上,竟是起了间住舍,这住舍竟也不小,竹所筑,开几窗,前面那人领两人进了这竹舍;
竹舍中,两人住间,一间书屋,一间茶坊,书屋开出个露天台于峭壁之边,峭壁之边,一桌两椅;
步茶坐于自己那住间,步贤和那人,到了这露天台;
“步贤先生,于今晚始,您二位衣食住行不必担忧,自有保障,还有的,请将那位小姐还叫做步茶,南宫那姓名太招摇,但望步贤先生继续照料那位小姐,羣宗,自有厚报。”
“这山间有许多这样的房舍吧。”
“这并非您所需知道的,做好本分之内,但望有一日您可活着走出这山。”
慕雪在元门内,休憩到了第二日,第二日清晨,他打听到了,安唯之是再也未被找到了;
未被寻到,未得思量,慕雪便被再派出去了;
夜色阑珊,这次,还是要他救人,所要救的,是位薛家的大人物,薛景崇;
要动这位大人的人,太多了,同僚,亦或是敌国,而慕雪也只是元门所派往的其一而已;
上路前,他收到了另个消息,来自赵一的信:沈漫雨并未有什么事情,只是那位薛少爷,将自己的命扔到了澜沧府;
而做这件事情的,是黄说遥;
“怎么样,吐得可好?”田逸群调侃着,而程子璇则是递给黄说遥一碗汤剂;
“多谢。”将汤剂灌入肚中,抹抹嘴角,咳了两声“我,从不坐船,今天,算是破例了,额咳咳咳。”
“不过,我不懂你为什么回来的有点晚。”田说着,她所说的,是黄说遥到云江畔的时辰,晚一些;“上面人交代的事不该这么长。”
“咳咳,我去杀了个人。”黄说遥说着,不再咳嗽;
“哪一位如此深仇大恨?”
“那个薛少爷。”他说着,又喝下点残余的汤剂,“他身上有我要的,所以我不想留这个人。”
接着,他竖起手掌,冲着田“别再问这件事,找我有什么求的,说就好了。”
“我看你的气息,你到底,做没做手脚?”所指的,是黄说遥的字迹,近乎无色,却看的清楚;
“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黄说遥说罢,却止住下一句的话;
“你便说吧,田她真是有事急求。”说话的,是程子璇;
黄说遥他一翘起嘴角,眨眨眼点点头“听说过,天生绝脉吧。”
不等田说,黄说遥则是继续了“在下便是天生绝脉。”
“可在下的修为,仅从练气之说,不加吹嘘,当世而今,出我之右的人,不过三人至多。”他伸手抹了抹鼻头,却又笑着,“但,所谓练气化道,修行层次之说,太过荒谬了,我这本领,尚不及田。”
“不对,天生绝脉之人,无任何可能修行,任何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
黄说遥耸耸肩,“常有言,功大欺理,却未有人常言,身随心转,虽不知道你们修行冥想时,见到的是什么,我见到的,是虚无。”
“哼,吹牛。”说话的,是程皓皓;
“是么?”
话说出,抬眼间,周遭皆变,身竟处繁星浩海之中,周遭星见,深邃之色,再见星息之间,这一瞬息之间,不知所在;
醒来时,只见到黄说遥捧着本书,嘴边,咬着个草标;
“浩海星辰,几位,还是第一次踏入吧。”
说话这语气,带着些许的傲气;
“这是,为什么?”说话的人,是田;十几柄剑,立于黄说遥的周围,剑锋所指,是要命的,“而你,又是为什么?”
“澈流庄什么时候做这样的事情了?”
“少有人可达如此境界,而逃命在外的,想必只有一位,南宫!”
“田!”程子璇,却是挡住了田逸群的下一手,“他肯定不是南宫,安心,安心。”
南宫,
一位以杀承道的修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