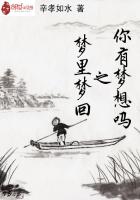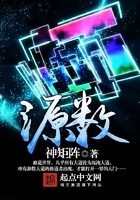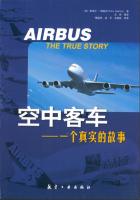说到爱国,中国更为突出。在世界上众国之林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宣传不爱国的。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必须对爱国主义加以分析,不能一见爱国主义,就认为是好东西。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爱国主义,一真一假;一善一恶。被压迫、被侵略、被剥削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真爱国主义,是善的正义的爱国主义。而压迫人、侵略人、剥削人的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邪恶的,非正义的,假爱国主义,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害国主义”。
1.随感录三十八鲁迅
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 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
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 Bon 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 Bon 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活,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2.论救国道德
冯友兰
我们以为凡道德都是救国道德,凡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凡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
在抗战的时候,一般人都觉得不拘什么东西,都必须与救国有关,才有价值。有些人似乎以为,即道德亦必须与救国有关,才有价值,或才有特别价值,于是有人讨论,什么是救国道德。好像是我们可于道德中,特别提出一部分,说这是救国道德,好像是现在我们所应该特别提倡的道德。
这种看法,我们以为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对于国家社会,是有害的。我们以为凡道德都是救国道德,凡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凡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
欲说明此点,我们须先说明道德的性质。一个社会组织,如欲存在,其分子必须遵守某些规律。如一个社会组织的分子,皆守此规律,则此社会组织,即是一个健全社会的组织,如皆不守此规律,则此社会组织即“土崩瓦解”,不能存在,这些规律,即是所谓道德。道德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所必需的。
国家亦是一个社会组织。它若果要存在,组成它的分子,必须遵守上所说的规律。这就是说,一切国民,都必须守道德。所谓救国者,无非欲使国家存在,国民守道德,都是所以使国家存在,所以凡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反之,凡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
例如商人做生意,要公平交易,这是商人的道德,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与救国无关。但商人若贪图厚利,囤积居奇,任意提高物价,使物价高涨,则必影响到后方整个的经济,后方的经济,一有扰乱,前方即要受到影响,这是我们现在所亲身经验到的事实。
又例如节约用费,不可乱用钱,这是个人的俭德,似乎亦与救国无关,但如大家都有钱乱用,则市面上钱多货少,亦能影响到物价,使物价高涨,因而影响到后方整个的经济。政府现在正提倡人民节约。可见节约也是与救国有关系的。
还有些人,做所谓公德私德的分别,这种分别,亦是不能通的。凡可称为道德者,都是与社会有关系的。例如上所说的公平交易及节约等,照这些人的说法,似乎应该是私德了。但照上所说的,我们可见其与国家关系是重大的。凡纯粹个人的事,与社会无关者,是不属于道德的范围的。例如一个人好喝酒,这或者不是一个好习惯,但我们不说这是不道德的事。一个人不好喝酒,这或者是一个好习惯,但我们不说这是道德的事。一个人好穿红白衣服,我们不能说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如于“跑警报”时,仍穿红白衣服,不顾大家的安全,这行为就是不道德的了。这是因其与别人有关系的缘故。凡人的行为,必与别人有关系,才发生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问题。
说道德有公私的分别,是错误的,说特别有救国道德,亦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对于国家社会是有害的,因为什么呢?
以为道德有公私分别的人,大都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属于所谓私德方面者,大家不能或不必求全责备。我们不承认有所谓公德私德的分别,即令有之,而在实际行为中,所谓公私的分别,往往亦很难分清,有些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别人要责备他,他说:这是我的私德,与你无干。好像从前皇帝,于废皇后、废太子的时候,如大臣谏阻,他说:“此朕家事。”其实他的家事,就是国事,二者之间,很难有清楚的界限。
特别指出某一部分的道德,说这是救国道德,其害更有甚焉。因为如此,可以使一般人以为,除此以外,别的道德的事,都与救国无关,都是承平时候的事,在抗战时候,则可以做可以不做。做官吏的,可以敷衍因循。做商人的,可以贪图厚利,发国难财。做教员的可以不用心教书,做学生的可以不用心求学,以为这些都与救国没有关系。其实这些事都是与救国有关系的。提倡特别有救国道德者,当然不一定特别指明,说这些事是与救国无关。但其对于所谓救国道德,特别提倡,难免予人以如此所说的错误印象。这种错误印象,对于国家,是有害的。
我们须知,所有的道德,都是救国的道德,所有道德的事,都是救国的事,所有不道德的事,都是祸国的事。所以我们主张不必特别提倡所谓救国道德。
3.爱国诗
朱自清
“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正是我们人人心里的一句话,现实的,也是理想的。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游)临终《示儿》的诗,直到现在还传诵着。读过法国都德的《柏林之围》的人,会想到陆放翁和那朱屋大佐分享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可是他们也分享着同样爱国的热诚。我说“同样”,是有特殊意义的。原来我们的爱国诗并不算少,汪静之先生的《爱国诗选》便是明证;但我们读了那些诗,大概不会想到朱屋大佐身上去。这些诗大概不外乎三个项目。一是忠于一朝,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其次是对异族的同仇。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第二项可能只是一姓的忠良,也可能是“执于戈以卫社稷”的“国殇”。
说“社稷”便是民重君轻,跟效忠一姓的不一样。《楚辞》的《国殇》所以特别教人注意,至少一半为了这个道理。第三项以民族为立场,范围便更广大。现在的选家选录爱国诗,特别注意这一种,所谓民族诗。社稷和民族两个意念凑合起来,多少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但“理想的完整性”还不足;若说是“爱国”,“理想的完美性”更不足。顾亭林第一个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警句,提示了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确是他的伟大处。放翁还不能有这样明白的意念,但他的许多诗,尤其这首《示儿》诗里,确已多少表现了“国家至上”的理想;所以我们才会想到具有近代国家意念的朱屋大佐身上去。
放翁虽做过官,他的爱国热诚却不仅为了赵家一姓。他曾在西北从军,加强了他的敌忾;为了民族,为了社稷,他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这种壮志常常表现在他的梦里;他用诗来描画这些梦。这些梦有些也许只是昼梦,睁着眼做梦,但可见他念兹在兹,可见他怎样将满腔的爱国热诚理想化。《示儿》诗是临终之作,不说到别的,只说“北定中原”,正是他的专一处。这种诗只是对儿子说话,不是什么遗疏遗表的,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尽可以说些别的体己的话;可是他只说这个,他正以为这是最体己的话。诗里说“元知万事空”,万事都搁得下,“但悲不见九州同”,只这一件搁不下。他虽说“死去”,虽然“‘不见’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师”终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嘱他儿子“家祭无忘告乃翁”!教儿子“无忘”,正见自己的念念不“忘”。这是他的爱国热诚的理想化,这理想便是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至上”的信念的雏形,在这情形下,放翁和朱屋大佐可以说是“同样”的。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配称为爱国诗人。
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