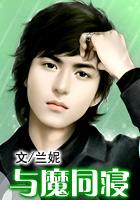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蒙泰尼里主教大人抵达佛罗伦萨,一时间全城为之轰动。他是一位有名的传道士,也是革新教廷的代表人物。人们热切地期盼他会阐释“新教义”,传布博爱、和解等救治意大利苦难的福音。吉齐红衣主教已被提名担任罗马圣院的书记长,以代替千夫所指的拉姆布鲁斯契尼。这一措施早已将公众的热情推向高潮。而蒙泰尼里正是保持这种狂热的最佳人选。他那无可挑剔的严肃生活作风,在罗马教会的显赫人物中实属罕见,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习惯于把敲诈、贪污和为人不齿的私通当作高级教士职业之永恒不变的附属品。何况作为一名传道士,他的才能的确了不起。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凭他优美的声音和磁石般吸引人的品行而卓尔不群。
如同往常一样,格拉西尼处心积虑地想把这位新来的名流请到他家里做客,可是蒙泰尼里可不是那么容易上钩的。对于所有的邀请,他都以礼貌而坚定的言辞断然谢绝。他借口身体不舒服,腾不出时间,既无精力也无余暇从事社交活动。
一个晴朗而凛冽的星期天早上,玛梯尼和琼玛穿过西格诺里亚广场。“格拉西尼夫妇真是欲壑难填啊!”他讨厌地对她说道,“你观察到在红衣主教的马车开过时,格拉西尼鞠躬的姿势吗?生平还没见过如此巴结社会名流的人呢。八月份捧的是牛虻,现在是蒙泰尼里。我希望受到如此瞩目的主教大人会感到受宠若惊。最可气的是,竟然有那么多宝贝货色趋炎附势。”
他们刚从人满为患的大教堂出来,蒙泰尼里正在那里布道。玛梯尼唯恐琼玛那恼人的头疼病复发,不等做完弥撒就劝她出来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早上,之前下了一个星期的雨,所以他邀请琼玛到圣尼科罗山上的花园散散步。
“不,”她答道,“你要是有时间,我倒愿意散散步,但是不要到山上去。我们就沿着阿诺河的堤岸走走吧。蒙泰尼里从教堂出来一定会路过这里,我跟格拉西尼一样,想看一看这位名人。”
“你刚刚不是已经看见他了吗?”“大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离得太远了,况且在马车经过时,他背对着我们。假如我们站在桥的旁边,肯定能清楚地看到他-他就住在阿诺河边上。”
“可是你怎么会突发奇想,非要看一看蒙泰尼里不可呢?从前你对有名望的传教士并不会特别留意啊。”
“我并不在意传教士,我在意的是他那个人。我想看看从我上次见过他以后,他的变化有多大。”
“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亚瑟淹死后两天。”
玛梯尼不安地瞥了她一眼。这时他们已经走上阿诺河的堤岸,她茫然凝视河水,脸上的那副神情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琼玛,亲爱的。”过了一会儿他说,“难道你要让那件痛苦的往事纠缠你一辈子吗?我们大家在十七岁的时候都犯过错误呀。”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十七岁的时候都杀死过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她惆怅地答道。她把胳膊撑在小桥的石栏杆上,俯瞰河水。玛梯尼沉默不语,每当她陷入这种情绪时,他几乎有些不敢跟她说话。
“每当我俯视河水的时候,我老是会想起这段往事。”她慢慢地仰起了头,凝视着他的眼睛,接着她神经质地颤抖了一下,“我们再走一会儿吧,西萨尔,站着不动有点儿冷。”
他们默默地过了桥,然后沿着河边往前走去。又过了几分钟,她才开口说话:
“那人的嗓音多美!我相信,他之所以有那样大的感染力,一半的秘密在于他的嗓音。”
“他的确有一副好嗓子。”玛梯尼表示赞同,他总算捕捉到了一个或许可以把她从痛苦的回忆中引开的话题,“而且,除了嗓子好之外,他还是我所知的最优秀的传教士。但我相信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还有更深的秘密,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与其他的高级教士不一样。在整个意大利教会里-教皇本人除外-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得出另外一个显赫人物享有他那样清白无瑕的声誉。去年我在罗玛亚的时候曾路过他的教区,亲眼见到剽悍的山民冒着大雨在路边恭候他,仅仅为了看他一眼,或摸一摸他的衣角。那边的人简直把他当作圣人来顶礼膜拜了,这种情况发生在罗玛亚人身上,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他们一向憎恨穿法衣的人。我曾经和罗玛亚的一位老农民-一个典型的走私贩子-交谈过,他说:‘我们并不崇拜主教,他们都是骗子。但是我们喜爱蒙泰尼里大人。没人见他说过一句谎话,或者做过一件不公正的事情。’”
琼玛自言自语地说:“我很怀疑他是否清楚人们对他的这种看法。”“他怎么就不清楚呢?莫非你认为这名不副实?”“我认为名不副实。”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告诉你的?蒙泰尼里?琼玛,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她把额前的头发向后拂去,随后转身对着他。他们仍默默地站着,他斜倚着栏杆,她则用雨伞的顶端在人行道上缓慢地画着弧线。“西萨尔,我跟你有多年的交情了,可我从没把亚瑟的真实情况告诉你。”
“用不着跟我说了,亲爱的,”他连忙打断她的话,“我全都知道了。”“乔万尼告诉你的?”“是的,他临终前的一个夜晚,我守在他的病榻旁,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琼玛,既然你提起这事,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他说你总是沉湎于这件痛苦的往事,他求我对你真诚相待,并设法让你不再想起这件事。
亲爱的,我已经尽力了,虽然我或许没有成功-我确实尽力了。”“我知道你尽力了。”她低声地答道,抬起眼睛看了一会儿,“如果没有你的友情,我的日子会很难过。不过……乔万尼并没有跟你说起蒙泰尼里大人,对吗?”
“没有,我并不清楚蒙泰尼里与这事有什么关系。他说的只是有关那个密探的事情,还有……”
“还有我怎样打了亚瑟一记耳光,他怎样投水自溺身亡。好吧,我就给你讲一讲蒙泰尼里的事吧。”
他们转身走向主教的马车将会路过的小桥,琼玛失神地看着河的对岸。“那时蒙泰尼里还只是一个神父,他是比萨神学院的院长。亚瑟进入萨宾查大学以后,蒙泰尼里经常给亚瑟讲授哲学课程,并跟他一起读书。他们之间情深意笃,相互爱护的程度远甚于师生关系,简直像一对恋人。亚瑟对蒙泰尼里心悦诚服,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假如他失去他的‘神父’-他老是这样称呼蒙泰尼里-他就会投河自尽。随后就发生了密探那事。第二天,我父亲和勃尔顿一家-亚瑟的同父异母兄弟-花了一天时间在达森纳港湾打捞他的尸体,我独自一人坐在我的房间里,回想我所做的蠢事……”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讲了下去:“天黑后我父亲走进我的房间说:‘琼玛,孩子,下楼去吧,我想让你见个人。’我们走下楼去,看到那个团体里的一个学生,他坐在接待室里,脸色发白,浑身哆嗦。他告诉我们乔万尼从狱中送出了第二封信,信上说他们从狱卒那里听到卡尔狄的情况,知道亚瑟是在忏悔的时候落入他的圈套。我还记得那位学生对我说:‘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清白的,至少这是一个慰藉吧。’我的父亲握住我的手,试图安慰我,他并不清楚我打了他。然后我回到了房间,独自坐了一晚。我的父亲在早上又出了门,陪同勃尔顿一家到港口去打探打捞的情况。他们对在那儿找到尸体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什么也没找到?”“没有,一定是被冲到海上去了,可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它。
我独自待在我的房间里,女仆告诉我有一位神父来访。神父打听到我的父亲去了码头,然后他就走了。我想他一定是蒙泰尼里,于是从后门跑出去,在花园门口追上他。当我说我想跟他说句话的时候,他停住脚步,一声不响地等着我开口。西萨尔,你真应该看看当时他的脸-随后的几个月里,它始终环绕在我的心头!我说:‘我是沃伦医生的女儿,我来告诉你是我杀死了亚瑟。’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他站在那里听着,仿佛是一个石头人。等我说完后,他说:‘让你的心安静下来吧,我的孩子,杀人的凶手是我,不是你。我欺骗了他,被他发觉了。’说完他转过身去,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大门。”
“后来呢?”“我不清楚他后来的情况,只听说当天晚上他昏倒在街上,被人抬到码头附近的一户人家。我只知道这些。我的父亲为我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我把情况告诉他以后,他就歇业了,立刻带我回到英国,这样我就听不到一点儿可能引起我回忆的事情了。他担心我也会跳河自尽,有一次我差一点儿就那么做了。后来我父亲身患癌症,我不得不理智些了,因为除了我,再没有人服侍他了。他死了以后,我要照顾家中的小弟小妹,直到我的哥哥成了家,能够安顿他们。后来乔万尼到了英国,他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莫及-他不该在监狱里写出那封倒霉的信。不过我相信,正是我们共同的痛苦把我们结合到一起的。”
玛梯尼略微一笑,摇了摇头。“你可以这么说,”他说,“不过乔万尼从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起,就打定了主意。我记得他第一次从里窝那回到米兰,就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谈论你,弄得我一听到英国姑娘琼玛的名字就腻味儿。我当时觉得,我真该恨你。啊!马车过来了!”
马车通过了小桥,停在阿诺河河边的一座宅院前。蒙泰尼里靠在垫子上,神色枯槁,似乎无力顾及聚集在门口等待一睹他风采的狂热人群。他在大教堂里露出的那种动人神情已经不复存在,阳光照出他疲惫的皱纹。他下了车,迈着无精打采的步子,颤颤巍巍地走进房子。琼玛转过身,慢慢地向桥头走去。
“我常常感到纳闷儿。”过了一会儿,琼玛开口说道,“他所说的欺骗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时我想……”
“想什么?”“说起来非常奇怪,那两个人的相貌惊人地相似。”“哪两个人?”
“亚瑟和蒙泰尼里,不止我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呢。而且那一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儿神秘莫测。亚瑟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温柔的一个人。和亚瑟一样,她的脸上有一种纯洁的表情,不过她总是显得有点儿恐惧,就像一个怕被人找到的罪犯。而勃尔顿先生前妻所生的儿子的老婆,对待这个继母的态度十分恶劣。还有,亚瑟和勃尔顿家那些粗俗的人真有天壤之别。当然了,人小的时候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回头想想,我常常怀疑亚瑟是否真是勃尔顿家的人。”
“也许他发现了他母亲的什么秘密-这很有可能是他自杀的原因,跟卡尔狄的事毫不相干。”玛梯尼插嘴道。此时此刻他只能用这句话安慰她。
琼玛摇了摇头:“西萨尔,假如你看见他被打之后脸上的神情,你就不会这样想了。蒙泰尼里的事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对他的伤害却永远无法弥补了。”
他们又走了一会儿,彼此沉默不语。“亲爱的琼玛,”玛梯尼终于说道,“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从前做过的事一笔勾销,那么往日的错误还值得我们苦思苦想。但事已至此,人死不能复生。这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至少那个不幸的小伙子已经解脱了,比起那些活下来的人-那些流亡和坐监狱的人-倒是更幸福了。你和我都得为那些人着想,我们没有权利为死者过度悲伤。要记住雪莱说过的话:‘过去是死亡的,未来才属于自己。’抓住未来,趁它还属于你的时候。你要关注的不是那些使你伤心痛悔的往事,而是你所能做的有益于别人的事。”
他在情急之下握住了她的手,忽听背后响起一个柔和、冷漠而又慢吞吞的声音,他连忙松开那只手,并向后缩回身体。
“蒙泰尼……尼……尼里大人,”那个懒散的声音喃喃地说道,“毫无疑问与你所说的完全一样,我亲爱的医生。他实在太好了,这个世界都容不下他的好了,应该恭而敬之地护送他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确信他在那里也会引起轰动的。那里的许多老鬼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新奇的东西,一个‘诚实的主教’。鬼最喜欢新奇的东西……”
“你是怎么知道的?”列卡陀医生的声音响起,那语调中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恼怒。
“我是从《圣经》上看到的,我亲爱的先生。如若相信福音书,即使最体面的魔鬼也喜欢奇奇怪怪的大杂烩。这不,诚实与主教的组合就是一个令人难受的大杂烩,正如虾子和甘草一样。啊,玛梯尼先生,波拉夫人!雨后的天气好极啦,不是吗?你们也去听当代的萨伏纳罗拉[1]布道啦?”
玛梯尼突然转过身来,只见牛虻嘴里叼着雪茄,纽扣里插着新买的鲜花,此时正向他伸出一只瘦削的、用手套裹得严严实实的手。阳光从他那锃亮的靴子反射出去,又从水上照到他那笑吟吟的脸上。所以在玛梯尼看来,他不仅没有往常瘸得厉害,反而显得更神气了。他们握手,一个热情洋溢,一个悻悻含怒。就在这时候,列卡陀急促地喊道:
“估计波拉夫人有点儿不舒服!”
[1]萨伏纳罗拉(一四五二-一四九八),佛罗伦萨传教士。他常常揭露教会与当局的腐败行为,因此遭受迫害,一四九八年因邪教罪被判处死刑。
她的脸色苍白,帽檐下面的阴影差不多呈青灰色。由于呼吸急促,系在喉部的帽带有些发抖。
“我要回家。”她无力地说道。玛梯尼叫来了一辆马车,护送琼玛回去。牛虻弯下腰为琼玛整理被车轮挂住的斗篷时,突然抬起头看了看她的脸。这时玛梯尼发觉她有些回避,脸上带着一种惊恐的神色。
“琼玛,你没事吧?”他们坐上马车离去之后,玛梯尼用英语问道,“那个恶棍跟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西萨尔,这不怪他。是我……我吃了一惊……”“吃了一惊?”“对,我仿佛看见了……”她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玛梯尼默默等待她恢复自控能力。随后,她的脸渐渐有了血色。“你说得没错。”她转过身来,像往常那样平静地说道,“回忆痛苦的往事不仅没用反而更糟,这只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产生幻觉。西萨尔,我们再也不要谈论这个话题了,否则我会觉得我见到的每个人都像亚瑟。这是一种幻觉,就像青天白日里的噩梦。就在刚才,那个讨厌的家伙走过来的时候,我把他当作亚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