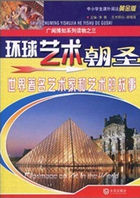在1893年5月9日那天,他参加一个19岁的学生拉赫马尼诺夫所写的歌剧《阿莱科》的首演。柴可夫斯基对这位不出名青年的作品有很深刻的印象,从许多方面看来,他注定要成为柴可夫斯基的正统继承人。
柴可夫斯基在5月底前往伦敦,因为那时伦敦音乐协会正准备举行两场音乐会,许多外国作曲家都要出席,接受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而且他们的作品也一一地被演奏。这一年对柴可夫斯基来说并不坏,但他却在抵达伦敦时又犯了忧郁症及思乡病。他在写给达维多夫的信中说:
我自愿受这折磨,你说是不是很奇怪?难道我是被鬼迷住了?我昨天在旅行途中,有好几次想不顾一切,掉头回去。但没有好的理由就一走了之,而且那是多么失礼!
昨天晚上我难过得失眠,那真是少有的事。我不但受尽了难以形容的痛苦(我新编的《第六交响曲》似乎足以表达),而且也为自己不喜欢陌生人和莫名的、不断的恐惧感难过,至于怕的是什么,那只有天知道!
他在信中进一步抱怨他的内心的痛苦及两腿无力,发誓说除非是为了“大把的钞票”,否则将不再出国旅行。6月1日他指挥自己的《第四交响曲》的演出,伦敦的听众很表欢迎。他在两天后骄傲地告诉莫杰斯特,说他的第一场音乐会“非常成功”,又说大家一致同意柴可夫斯基获得了实际的胜利,连在他后面演奏的圣桑都为之失色。
纵然这次成功是暂时性的,显然它也确实使柴可夫斯基的不愉快暂时消除,因为他说过他对伦敦的第一印象受恶劣气候影响最大:“因此我不知道它的乡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天知道,巴黎比起伦敦来只不过是个村落而已!走在这里的摄政街或海德公园时,看到的是那么多的华丽车马,那可真会把人给弄得眼花缭乱。”
但是,一星期后,他的旧病复发了,我们发现他抱怨他所必须忍受的痛苦生活,没有片刻的安静,以及永不停止的烦躁、惧怕、思乡与疲乏。他只好自我安慰,不断告诫自己,解脱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6月12日剑桥大学开始举行颁奖典礼,那一天可以说是让柴可夫斯基解脱痛苦的一天,和他一起出席的有圣桑、布鲁赫。柴可夫斯基发现布鲁赫却是个没有同情心及极为骄傲的人。格里格虽也是受奖人之一,但他因病而未能出席。圣桑是柴可夫斯基的老朋友,同时,还有位名人也和他相处得很好。
那天晚上的音乐会,是由每位作曲家指挥他自己的一首乐曲。柴可夫斯基选择了他的交响乐诗《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结果圣桑对他的“伟大天才及超特的技巧”表示由衷的敬佩。
第二天早晨,这四位作曲家都戴着有金穗子的黑天鹅绒四方帽,穿着红白色的丝长袍去接受他们的荣誉学位。柴可夫斯基对剑桥大学所保留的中世纪奇特习俗,以及它那种像修道院般的古老建筑留下极深的印象。同时,他也非常惊奇于他自己对此地的亲切感。
次日,他离开英国,前往巴黎。柴可夫斯基写信告诉康德拉契耶夫,说现在一切都已过去,回想起在英国每个地方访问时,他们对他那么亲切,确实令人欣慰。但由于他的脾气古怪,因此他在那里时并不开心。
柴可夫斯基回到莫斯科时听到了阿里布列赫特和席洛夫斯基都已去世的坏消息,同时,他的朋友阿布赫金也生命垂危。莫杰斯特回忆他哥哥当时的异常反应时,曾这么说:“早几年前遇到这样的伤心事时,难过的程度比现今要严重得多。现在,他似乎对于死亡的看法不那么迷惘和惧怕了。究竟是他现在的感觉较为迟钝,还是近年来的痛苦遭遇使他了解到死亡经常是一种解脱呢?我真是说不出来。我只想强调一件事实,从他自英国回来以后,直到他死亡时为止,虽然坏消息一再传来,他却始终保持像往常一样的愉快、平静。”
当他安全地回到克林时,随即就开始编写《第六交响曲》。尽管他在管弦乐曲方面经常遭遇困难,仍旧在八月底将它完成了。他高兴地写信给尤尔根松:“当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一件好的作品时,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有感觉如此自满,如此骄傲,及如此快乐。”
但在给达维多夫的信中,他却表示有关音乐界对他新作品的反应如何,他比较没有信心:“如果这新交响曲首先遇到的是毁诋或无人欣赏,我认为那是很自然的事,一点也不值得惊讶。不过,我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我爱它的程度比爱我以前任何一首乐曲都深。”
他在听到阿布赫金死去的消息时,依然处之泰然;但在同时期写给尤尔根松的信中,他却明白表示梅克夫人的事仍旧困扰着他。他说:“人们如果也看过这些信件的话,我相信他们会认为火变成水也许比她停止对我的补助来得可能。当她准备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我时,人们一定奇怪,我怎么能满足于那样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数目。但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更重要的是,我居然还真正相信她已经破产。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一个女人的多变而已。这事真让人恼火,但是我并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