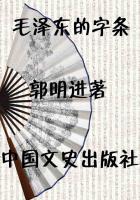他最急迫的工作是把《胡桃夹子》的各部分乐曲集编成组曲,以便在3月7日圣彼得堡的音乐会中演奏。结果,这组曲很受人欣赏,6个乐章中有5个演奏过两次。两星期后全部芭蕾舞曲完成时,柴可夫斯基前往莫斯科去为三个乐曲的指挥工作履行前约。那是古诺的《浮士德》,鲁宾斯坦的《魔鬼》。
他和歌剧界的关系非常好,因此5月17日离去时,所有交响乐团中的每一个团员和歌手全都到火车站去为他送行。他前往索伏朗诺夫在克林乡下为他准备的新屋,那地方虽只有一个小花园,景色也极平常,但最大的优点是房间非常大,就一般俄国乡村房舍而言,真是颇不多见。
那里是柴可夫斯基最后的住处。索伏朗诺夫在柴可夫斯基死后将它买下,1897年交给了莫杰斯特和达维多夫。后来,那地方成为柴可夫斯基博物馆,最后俄国政府取得它的所有权,1941年曾受德军掠夺,后由俄政府出面将之收回。
柴可夫斯基在克林乡下定居以后,开始起草编写新交响曲,但随即因日益烦躁及患了胃病,而由达维多夫陪伴去西欧治疗。7月底回到克林以后,他又拾起以降E调编写新交响曲的工作,同时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作品新版的编校上面。
但交响曲谱写工作没有什么进展,他写信告诉尤尔根松说是“没有时间”。他很希望在维也纳的音乐及戏剧展览会中担任音乐指挥。他说:“维也纳一直对我很不友善,我极想去克服那种敌意。”但他9月18日抵达维也纳时才发现他所要指挥的,竟然是在一处不比“酒吧”大的地方演奏的小交响乐队。他惊恐地和莎菲曼特及萨伯尔尼可夫跑到她在泰洛尔的城堡中去,因为那里“宁静而且没人打扰”。
他在回国旅途中,参加《黑桃皇后》在布拉格的首演,轰动一时。抵达莫斯科后,由于公务缠身,而且必须出席音乐会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一百次演出,他感觉越来越厌烦。他虽成为俄国的一流作曲家,可是内心并不愉快。
《Yolanta》和《胡桃夹子》已经开始排演了,柴可夫斯基在11月初去圣彼得堡进行督导。在12月17日首演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它们推崇备至,然而这两者都不能算是成功,因为评论普遍不佳,柴可夫斯基12月22日写信告诉阿纳托里说他“情绪坏透了”,又说“舞台布置虽然不错,但芭蕾舞曲却令人生厌”。
以后,人们依然不重视他的这两部作品。即使今天《Yolanta》也一直未能再抬头。在双重的失败下,柴可夫斯基再次逃避到西欧去。莫杰斯特说:“好像有一些无名的力量在迫使他东奔西跑……他不能长久在一处停留,但这主要是由于他常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比我们所住的处所要好……”
如果柴可夫斯基想在西欧寻找安逸与解脱,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他在12月28日从柏林写信给达维多夫,说他有意放弃新交响曲的编写工作。几天后他又写信告诉莫杰斯特说:“除了难过以外,别无其他消息。”而且还说第二天要去探望40年前的女家庭教师劳妮,因为最近听说她仍健在。
此一番会面,使他“充满恐惧,好像是要进到死人的世界一般”。及至看到劳妮几乎没有怎么改变,而且不像是70高龄的人时,他才放下了心:“我流下泪来,但她迎接我时却很亲切而且高兴,好像我们只有一年没见面似的……过去的一切都清楚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呼吸到了沃特金斯克的空气,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柴可夫斯基与劳妮郑重道别后,1月14日前往巴黎及布鲁塞尔。10天以后他又到奥德萨督导《黑桃皇后》的排演及指挥全部都是他自己乐曲的音乐会。他也腾出时间,坐下来让库兹涅佐夫为他画那幅有名的画像。
关于那事,莫杰斯特曾表示了他的看法:“那个艺术家虽然不知道柴可夫斯基内心的情感,但却把他当时身心的悲凄情景全都揣摸及描绘得非常成功……没有任何一幅柴可夫斯基的画像比那幅更为真实和生动。”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奔走,柴可夫斯基在1893年2月初回到克林,突然感觉到自己再也没有前途可言了。2月9日他写信给莫杰斯特,说他所需要的是对自己的信心。由于他对自己的信念已经动摇,所以他认为自己担任的角色已经告终了。
他在一个星期后开始编写一首新交响曲。这项工作证明了他所担任的角色绝对没有结束。对全世界来说,那是他所有乐曲中的杰作。